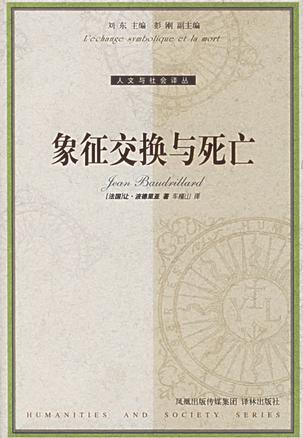这对我们而言是如此“自然”,我们甚至不再思考我们对话语的滥用,然而这正是我们与所有其他文化的区别。我们不受礼仪、宗教或诗歌的任何限制,完全“自由地”使用和滥用词语、音素、能指,对我们随意“生产”出来的大量材料不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每个人都以自我“表达”的名义,无休止地自由使用和汲取声音材料,只考虑自己要说什么。这种话语“自由”,这种掌握话语、使用话语,却从不归还话语、从不为话语负责、从不牺牲话语的哪怕任何一小部分的可能性(而以前人们则要牺牲原始财富的一小部分,以保证原始财富的再生产),这种把语言当做一个无所不能、取之不尽的媒介的语言观念(语言仿佛是已经实现了“各取所需”这种政治经济学空想的地方——幻想一种闻所未闻的储备,幻想一些甚至不需要经过原始积累就随着人们的使用而神奇般地被再生产出来的原材料,即幻想一种奇妙的挥霍浪费的自由),这种性质,即我们的话语交流的性质,这种疯狂地自由使用能指材料的性质,只有在一个整体配置中才能被设想,在这个整体配置中,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人类本身的再生产受到同样原则的支配。一种同时发生的变化使以前的社会构成过渡到了我们的“现代”社会构成。在以前的社会构成中,财富、个体的数量以及言说行为,都在一个象征循环的内部以比较严格的方式受到限额的规定,受到限制和控制。而我们的现代社会构成的特点则是经济、语言、人口等方面的无限生产性——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上涨:物质积累的上涨、语言表达的上涨、人类繁殖的上涨 ① 。 这种生产性模式——指数曲线的上升、急剧增长的人口、无限的话语性,应该在各处同时得到分析。仅就此处涉及的语言问题而言,很清楚,这种为了表达的目的而使用无限数量的音素的疯狂自由(却不经过相反的过程:抵消、赎罪、吸收、摧毁——此处用什么词并不重要),是与索绪尔所阐明的那条简单法则根本对立的。根据那条法则,诗歌中任何一个元音,任何一个辅音,任何一个音节,如果不被叠加,也可以说如果不被驱除,如果不在抵消它的那种重复中完成,它就不应该被说出。 这样一来,就不可能有一种无限使用了。诗歌同象征交换一样,调动起一个受到严格限制的素材库,它的任务是把素材全部用尽,而我们的话语经济学所调动的却是一个无限的素材库,它不考虑消解问题。 在我们的话语系统中,词语、音素变成了什么?不要以为它们一经使用就乖乖地消失了,或者像排铸机字模中的活字那样返回某个位置,等待再次使用。这仍然属于我们的理想主义的语言观。任何词语、任何音素,只要不被重复,不被归还,不被诗的叠音所蒸发,不被当做词项和价值(与它“想说”的意思等值)来消除,都会残留下来。这是一种废料,它将汇入一堆由残渣、不透明的话语材料构成的难以置信的沉淀中(人们开始发现,生产性文明的主要问题可能就是它的废料问题,而废料问题不是别的,正是生产性文明的死亡问题:被自己的残渣压垮)。但工业废料与语言废料相比算不了什么:我们的文化本身被这个石化了的庞大废料机构所纠缠和围困,它试图通过一种生产过剩来化解这个废料机构:它试图通过语言的竞价来阻止“交流”率下降的趋势,但是无济于事。任何商品,即任何在价值规律和等价法则影响下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阻断社会关系的无法分解的废料,同样,任何被生产出来的、未受到象征摧毁的音素、词语,都会作为被压制的东西积累下来,以死亡语言的全部抽象力量压在我们身上。 统治我们语言的是一种丰富和浪费的经济学——是富裕的乌托邦。就物质经济而言,“丰富”和浪费是一个新特征,是一个历史特征,但就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而言,它们却像是一个已经给定的自然维度。这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应有尽有的乌托邦,是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语言的无限资本的乌托邦。为了表达意义,每个人都进行能指的积累和积累性的交换,而能指的真理则在别处,在能指与能指想说的意思之间的等价关系中(这个意思可以用更少的词汇说出——简练是一种道德品质,但这永远只是一种手段经济学)。匮乏的幽灵从来不会在这种话语“消费”上盘旋。这种话语消费,这种由丰富的想像所支撑的浪费操纵,最终成为一种惊人的通胀,它和我们所处的这种增长失控的社会一样,也留下了一堆同样惊人的废料,一堆无法降解的能指废料,这些能指虽然被消费,但从未被耗尽。因为,被使用过的词语不会自行蒸发,它们作为废料积累下来——这种符号污染和工业污染一样惊人,并且和工业污染同时发生。ˇ 语言学重新抓住的仅仅是这个废料阶段,是一种功能语言的阶段。它把这个阶段普遍化,当做一切语言的自然状态。它想像不出任何别的东西:“罗马人和伊特鲁立亚人用一些生硬的数学线条划分天空,然后在一个像庙宇一样有限的空间里向神祈祷;同样,每个民族的上方都有这样一块分布着数学概念的天空,从此,在真理的要求下,他们不准备到别处,只准备在这块天空的范围内寻找概念之神。”(尼采《哲学家之书》)语言学也是如此:它把语言逼进一个按照它自己的样子来自律的范围内——它假装“客观地”找到了语言,其实是它发明了语言,它使语言彻头彻尾地合理化了。语言学没有能力想像语言的另一种状态,只能想像语言是代码(语言系统)的抽象组合再加上言语的无限运用,换句话说,语言是建立在一般等价关系和自由流通基础上的投机(取“投机”和“思辨”的双重含义)——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地使用词语,并根据代码的规则进行词语交换。 然而,让我们假设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语言符号被有意地限额分配:限制发行,没有明文规定的生产“自由”,也没有明文规定的流通和使用自由,或者更应该假设一种双重流通:一个是“解放的”词语的流通,词语可以被任意使用,作为交换价值进入流通——这是意义“交易”的领域,类似经济交换中的金瓦利(gimwali)圈。 一个是“未解放的”区域中的流通,这个区域受到控制,其物资只限于象征使用,在这里,词语没有使用价值,也没有交换价值,既不能增加,也不能被任意说出——类似对贵重财产而言的库拉(kula)圈。在这个区域中,一般等价原则完全不起作用,因此符号—语言“科学”研究的符号逻辑理性结构也不起作用。 诗歌在语言方面重新创造了原始社会的这种情况:一些数量有限的物品在交换/馈赠中不断地流通,产生出一种取之不尽的财富,一个交换的节日。根据总量或价值来估算的原始资料,其最终的结余几乎是一种绝对的匮乏。它们在节日和交换中不断地被消耗,“用它们最小的容量和数量”描绘出尼采所说的“符号的最大能量”或萨林斯所说的第一个、惟一一个真正的富裕社会。在这里,词语与物品、资料的性质相同:它们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任意使用的,这里没有语言的“富裕”。在巫术和仪式用语中,一切都受到限制,只有这种限制才能维护符号的象征效能。萨满和先知对一些音素或一些被编码、被限制、被计算的仪式用语施加影响,在一种最大限度的意义组织中把它们耗尽。仪式用语按照字面形式和节奏被准确地念诵出来,通过它自身控制未来——而不是通过它所表达的意义 ① 。
象征交换与死亡——作为价值毁灭的诗歌 2
书名: 象征交换与死亡
作者: [法] 让·波德里亚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原作名: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译者: 车槿山
出版年: 2006-4
页数: 359
定价: 22.5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00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