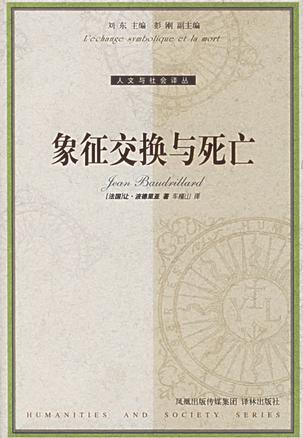任何身体或身体部位都可以在功能上以相同的方式运作,只要它服从相同的色情戒律即可:它必须是而且也只需是尽可能地闭合,尽可能地光滑,没有断裂,没有洞口,没有“缺陷”,一切性感差异都被指称(并且设计)这个身体的结构障碍所消除,这种障碍在服装、首饰、脂粉中可见,在完全的裸体中不可见,但永远在场,因为此时它像第二层皮肤一样包裹身体。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无所不在的广告话语十分典型,例如“近似裸体”、“裸而不见,仿佛你在从前”、在紧身袜中“你比自然更裸”: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调和“直接”感受身体的自然主义理想和剩余价值的商业需求。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了。最有趣的地方是真正的裸体在这里发现了自己作为次级裸体的定义:紧身袜X或Y的裸体,透明纱衣的裸体:“以致这种透明将你变为你自身。”另外,这种裸体还经常被镜子替代——无论如何,女人正是在重叠中束缚“她梦寐以求的身体:她自己的身体”。至少这一次,广告神话是绝对有道理的:惟一的裸体就是在符号中自我重叠的裸体,就是在被表现的真相中自我包裹的裸体,这种裸体像镜子一样再现了身体在色情方面的基本规则,即为了以菲勒斯方式得到赞美而变成自豪的、无性的身体,变成半透明的、光滑的、脱毛的实体。 这方面的完美例子是电影《金手指》(邦德[J.Bond])中那个涂成金色的女人:所有洞口都被堵住了,这是彻底的化妆,这使她的身体成为完美无缺的菲勒斯(它是金色的,这只是强调了与政治经济学的同构),这当然也就等同于死亡。这个涂金的裸体花花公主将因为体现色情幻想直至荒诞极限而死去。但在功能美学中,在身体的大众文化中,任何皮肤都是这样的。紧身袜、紧身裤、袜子、手套、“贴身的”长裙和上衣,更不用说晒黑的皮肤了:永远都是“第二层皮肤”这一主题,永远都是这种使身体变成玻璃的透明薄膜。 皮肤本身并不能被定义为“裸体”,只能被定义为性感区:接触与交换的肉体中介,吸收与排泄的代谢。身体并不终止于这种多孔的、有洞的、开口的皮肤,皮肤只是被形而上学设定为身体的分界线,它为了第二层皮肤的利益而遭到否定,第二层皮肤没有毛孔,没有渗出,没有排泄 ① ,不冷也不热(它是“凉爽的”,“温暖的”:优化的空调),没有斑点,也不粗糙(它是“细嫩的”,“柔软的”),没有一定的厚度(“透明的肤色”),尤其是没有裂口(它是“光滑的”)。它被功能化,成为玻璃纸保护层。所有这些品质(凉爽、柔软、透明、光滑)都是封闭的品质——即一种零度,它来源于对两个极端的否定。皮肤的“青春”也是一样的:年轻/年老这一范式在仿真的不朽青春中被中和了。 这种裸体玻璃化可以与那种给物体加防护层的强迫症相比较:涂蜡、包塑等,还有刷洗、擦拭等劳动,目的都是让物体不断地重新进入清洁的、完美抽象的状态——这也是为了阻止它们分泌(变色、氧化、灰尘),预防它们崩溃,使它们维持在抽象的不朽中。这是“被指称”的裸体,它不暗示自己所编织的符号网络下的任何东西,尤其是不暗示身体:既不暗示劳动的身体,也不暗示享乐的身体;既不暗示性感的身体,也不暗示被撕裂的身体——它在安定的身体仿象中从形式上超越了这一切,仿佛是芭比娃娃:“她之所以美,是因为她精确地填满了自己的裙子”——这是没有未知数的函数方程式。与人体模型的皮肤(下面有颤动的肌肉)相比,现代身体更像充气娃娃,吕伊(Lui)曾用一个幽默节目表现过这个主题。人们在节目中看见一个脱衣舞女,她结束脱衣时,做了最后一个动作:她拔掉了自己的肚脐,于是她当下就泄气了——舞台上只剩下一小堆皮肤。 这是裸体的乌托邦,是在自己的真相中出场的身体的乌托邦。一个印第安人说(我不记得是谁了):“裸体是一个无表情的面具,它掩盖了每人真正的天性。”他在这里的意思是:身体只在被铭文标记、覆盖时才有意义。阿莱(A.Allais)在节目中以相反的方式表达了上面的意思:一个狂热爱好真理的印度贵族不满足于寺院舞女的脱衣,于是让人活剥了舞女的皮。 身体在任何地方都不是这种存在的表面,不是这种没有痕迹的处女海滩,不是这种自然。身体只是在压抑中才获得这种“原初”的价值,根据自然主义幻想让身体作为原貌得到解放,就是让它作为压抑得到解放。此时裸体必将反戈一击,不可避免地给身体戴上空中审查的光环:第二层皮肤。因为皮肤像任何获得符号力量的符号一样,在意指过程中自我重叠:它从来都已经是第二层皮肤了。这并不是最后的皮肤,但永远是惟一的皮肤。在这种致力于把身体建构为整合化幻想的多余的裸体符号中,我们重新发现了意识主体通过自己的镜像进行的无限思辨——在重叠中从形式上捕获并消除自身不可还原的分裂。这些题写在身体上的、紧挨着死亡冲动的符号,从来都只是在肉体材料上重复意识主体的这种形而上学操作。这正如阿尔托所说:“人们通过皮肤使形而上学进入精神。” 这是镜子的围墙,也是标记的菲勒斯的重叠:在这两种情形中,主体都在自我诱惑。它诱惑自身的欲望,并且在被符号重叠的自身消除这一欲望。在符号交换的后面,在像菲勒斯堡垒一样的代码作用的后面,主体可以躲藏起来恢复镇定:避开他人的欲望(避开自己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自)视而不被见。符号的逻辑和反常的逻辑在这里吻合了。 这里有必要彻底区分身体层面上的题写与标记的劳动在原始社会中和我们的当代系统中的不同之处。人们非常容易在“象征表达”这个普遍范畴中混淆它们,仿佛身体过去就一直是它现在的样子,仿佛古代文身具有和现代化妆一样的意义,仿佛存在着一种超越了历次生产方式革命、从远古时代直到政治经济学领域都没有变化的意指方式。在我们的社会中,符号在一般等价物的制度下相互交换,它们在主体的菲勒斯抽象和虚构性饱和的系统中获得交换价值。与此相反,在古代社会中,身体标记和面具活动的功能是即时实现象征交换,与诸神的交换/馈赠,或在群体中的交换/馈赠——这种交换不是在面具或符号操纵下的主体对自身同一性的转让,而且正相反,在这种交换中,主体耗尽自身同一性,成为占有/剥夺的主体进入冒险——整个身体就像财产和女人一样成为象征交换的材料——或者可以干脆说,在这种交换中,标准的意指模式还没有出现(就像货币的抽象概念还没有出现一样),我们那超验的“能指”/“所指”,以及统治着我们那整个身体政治经济学的“菲勒斯”/“主体性”都还没有出现。一个印第安人(也许还是前面那个人)在回答白人关于裸体的提问时说:“我全身都是脸。”他的意思是说,他的整个身体(而且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身体从来都不是赤裸的)都托付给了象征交换,而这种交换在我们这里却经常局限于惟一的脸和目光。在印第安人那里,所有身体都在相互注视,相互交换各自的全部符号,这些符号在永无休止的关系中耗尽自身,它们既不参照一种超验的价值规律,也不参照一种主体的私人占有。在我们这里,身体困住自己的符号,通过计算在主体的等价法则和再生产法则下交换的符号而得到增值。主体不再消解于交换中:主体在思辨。正是这个主体,而不是野蛮人,完全处在拜物教中:通过身体这个配角,主体被价值规律偶像化了。
象征交换与死亡——次级裸体
书名: 象征交换与死亡
作者: [法] 让·波德里亚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原作名: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译者: 车槿山
出版年: 2006-4
页数: 359
定价: 22.5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00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