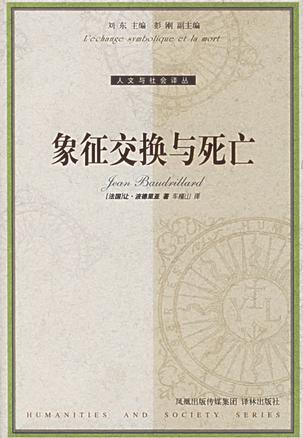这些名字要求的并不是一种同一性,一种人格,而是这个宗派、团伙、群体、种族或年龄段的根本专有权,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种专有权正在成为名字的归属,正在成为对这个名字、这个图腾名称的绝对忠诚,尽管这一专有权直接来自地下连环漫画。这种象征性名称的形式是我们的社会结构所否认的,这种结构强加给每人一个专名和一个私有的个性,以抽象而普遍的城市社会性的名义粉碎了一切关联性。相反,这些名字,这些部落名称负有一种真正的象征责任:它们的出现就是为了在匿名中无限地相互给予、相互交换、相互传递、相互接替,不过这是一种集体匿名,在这种匿名中,这些名字就像从一人到另一人的秘传词语,如此完美地相互交换,以至就像语言一样,不是任何人的财产。 这就是象征仪式的真正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涂鸦与所有传媒符号、广告符号截然相反,这些符号有可能在我们的城市墙面上造成相同咒语的错觉。人们曾谈到过关于广告的节日:没有广告,城市环境将很沉闷。但事实上,广告只是冷漠的活跃,它是召唤和热情的仿象,它不向任何人示意,它不能被一种自主或集体的阅读重新接纳,它不创造象征网络。广告大于承载它的墙面,它本身就是一堵墙,一堵功能符号墙,这些符号就是为了被破译才出现的,因此符号效果也随着破译而枯竭。 所有传媒符号都来自这种没有品质的空间,来自这个像一堵墙般竖立在符号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登录界面。德勒兹也许会说这是没有器官的城市身体,这个身体上交织着运河般的脉络。涂鸦运动则处于领地的范围。它把已经解码的城市空间变为领地:某条街、某堵墙、某个城区通过涂鸦而获得生命,重新成为集体的领地。它没有把自己限制在贫民窟,它把贫民窟输往城市的所有交通要道,它侵入白人城市,并表明这个白人城市才是西方世界的真正贫民窟。 随着这场涂鸦运动,语言贫民窟闯入城市,这是一种符号动乱。在城市的信号系统中,涂鸦至今为止一直意味着社会的底层——色情、淫秽的底层,意味着公共厕所里和空地上那些涉及性器官的、压抑的图文。只有政治宣传标语才以进攻方式占领墙面,但对这些标语而言,墙面仍然是载体,语言仍然是传统中介。这些标语针对的不是墙面本身,也不是符号功能性本身。大概只有这里的涂鸦和法国1968年5月的那些招贴才以另外的方式涌现,它们攻击载体本身,让墙面恢复一种野蛮的变动性,一种图文的突发性,这等于把墙面废除了。农泰尔市的那些图文正是这种反传媒行动,正是这种挪用:把墙面当做空间恐怖主义功能分区的能指。证据就在于行政当局相当灵巧,没有抹去这些图文,也没有重涂墙面:这项工作由群众的政治标语和招贴完成了。没有必要镇压:传媒自身,极左派传媒自身,让墙面恢复了盲目功能。此后人们知道了斯德哥尔摩的争议墙:某些墙面有争议的自由,旁边却禁止涂写。 曾经也有过挪用广告而展开的短暂攻击。它虽然受到自身载体的限制,但已经走上传媒自身开辟的道路了:地铁、车站、招贴。还有鲁宾(J.Rubin)和电视上的美国反文化展开的攻击。这是仅在内容层面上改变大众传媒的政治尝试,没有改变中介本身。由于纽约的涂鸦运动,城市运输和移动载体第一次得到了如此大规模的应用,第一次具有了如此多的进攻自由。但尤其是传媒第一次在自己的形式本身中受到攻击,即在自己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中受到攻击。这恰恰是因为涂鸦没有内容,没有信息。这种虚无就是力量。对形式的全面攻击伴随着内容的衰退,这并非偶然。这来自某种革命直觉——即深层意识形态不是在政治所指层面上运作,而是在能指层面上运作,正是在这里,系统最容易受伤,最容易被摧毁。 涂鸦运动的政治意义就这样显露出来了。这个运动诞生在对贫民窟动乱的镇压中。在这种镇压下,造反分裂为两派:一派是纯洁、强硬、教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组织,另一派就是这种没有目标、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内容的符号层面上的野蛮文化过程。有人在前一派中看到了真正的革命实践,指责涂鸦是民间创作。但正相反:1970年的失败造成了传统的政治行动主义的衰落,同时也迫使造反在真正的战略场所变得激进,即在完全操纵代码和意义的场所变得激进。因此,这根本不是在符号中的躲避,相反,这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极大进步——在这里,理论和实践再也不能分离了。 起义,闯入市区,而市区是再生产和代码的场所——在这个层面上,重要的不再是力量关系,因为符号依赖的不是力量,而是差异,所以应该用差异来进攻——用不可编码的绝对差异来拆毁代码的网络,拆毁被编码的差异的网络,系统遇到这种绝对差异就会崩溃。这个目的既不需要组织起来的群众,也不需要清晰的政治觉悟。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只要?标记笔和喷墨罐武装起来,就可以干扰城市信号系统,就可以打乱符号秩序。涂鸦遮盖了纽约的整个地铁图,如同捷克人改变布拉格的街道名来迷惑俄国人:这是相同的游击战。ˇ 尽管表面相似,但那些“城墙”,即墙绘,与涂鸦毫无关系。这些墙绘是上层发起的改造并活跃城市的事业,依靠市政府津贴实施。城墙公司成立于1969年,“目的是促进墙绘计划与技术”。支付预算的是纽约市文化事务局和各种各样的基金会,其中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个公司的艺术思想是:“建筑物与纪念性绘画之间的自然结合。”它的目标是:“把艺术献给纽约市民。”或者还可以提到洛杉矶的艺术广告牌计划:“此计划的实施是为了促进城市环境中使用广告牌作为中介的艺术表现。福斯特(Foster)和克莱瑟(Kleiser)这两大广告社的合作使广告空间成为洛杉矶画家的艺术橱窗。它们创造了一种充满活力的中介,使艺术走出了画廊和博物馆的狭窄范围。” 当然,这些操作都交给了专业人员,交给了那些在纽约聚成共同体的艺术家。没有任何歧义:这里涉及一种环境政治,即大规模的都市工业设计——在这里,城市赢了,艺术也赢了。因为艺术闯进“露天”、走上街头时,城市没有爆炸,艺术接触城市时,自己也没有爆炸。整个城市变成了艺术陈列室,艺术在城市中重新发现了演习场。两者都没有改变结构,它们只是交换了各自的特权。 “把艺术献给纽约市民!”只要把这句话与“超酷”说的话比较一下就够了:“哥们儿,有的家伙不喜欢这玩意儿,管他喜欢不喜欢,反正是我们搞出了最带劲儿的艺术运动狂扁纽约市。” 全部的差异就在于此。有些墙绘很美,但这并不重要。这些墙绘将在艺术史上留名,因为它们巧妙地用线条和色彩在光秃秃的墙面上创造出了空间——最美的画总是那些错视画,它们创造了距离和景深的错觉,按照其中一个艺术家的说法,它们“用想像扩展了建筑”。但这也正是它们的局限。它们让建筑游戏,却没有破坏游戏规则。它们在想像中回收了建筑,却保留了建筑的圣体(从建筑的技术载体到纪念性结构,到阶级社会面貌,因为这样的“城墙”大部分都在城市的白人文明区)。
象征交换与死亡——冷酷的杀手或符号的起义 2
书名: 象征交换与死亡
作者: [法] 让·波德里亚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原作名: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译者: 车槿山
出版年: 2006-4
页数: 359
定价: 22.5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00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