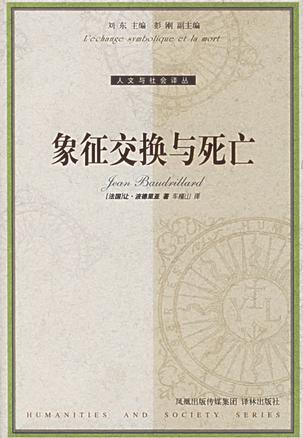这不再是生产的危机,而是再生产的危机(所以不可能确定这种危机中真相和仿象的状况)。生态学,这就是生产在短缺的幽灵中重新找到源泉,生产重新发现自然必要性,重新锻造价值规律。但生态学太慢了。一次突发的危机,比如石油危机,将成为更有效的治疗。石油越少,人们越能意识到生产的存在。当原材料再次占据突出位置时,劳动力也将再次占据自己的位置,整个生产机制也将重新变得可以理解。这将是另一圈的重新开始。 因此无需恐慌。当劳动力的密集调动和劳动力的伦理都有瓦解的危险时,物质能源的危机将及时赶来阻止生产目的性真正灾难性的毁灭,把这种毁灭变成一种简单的内在矛盾(我们知道,这个系统正是依靠自己的矛盾生存的)。ˇ 还有一种幻觉需要加以考虑:资本系统在达到扩大再生产的某个临界点时,将不可逆转地从一种短缺策略过渡到一种富裕策略。当前的危机证明这种策略是可以逆转的。这一幻觉仍然来源于对短缺现实或富裕现实的天真信仰,即来源于这两个词项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对立这种幻觉。然而,这两项只不过是交替,而且新资本主义的策略定义不是过渡到富裕阶段(消费阶段、压抑性非升华阶段、性解放阶段,等等),而是过渡到两者之间系统性交替的阶段:短缺和富裕——因为两者都不再有参照,即不再有对抗性现实,所以系统可以不加区分地利用前者和后者。这一切代表的是再生产的完成阶段。在政治领域,当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切对抗都被中和、权力的行使可以交替利用前者和后者的时候,上述这个阶段就达到了。 正是词项的这种不确定性,辩证对立成为简单而纯粹的结构交替这种中和,带来了危机现实不确定的特有效果。这种难以忍受的仿象效果——任何来自代码系统化运转的东西都有这一特征——所有人都在尽力用阴谋论清除它。危机可能是“大资本”策划的:这一假设给人安全感,因为它恢复了一种真实的政治经济体制,恢复了一个(隐匿的)危机主体的在场,也就是一个历史真理的在场。仿象的恐怖消除了:一切都更好了——宁愿要资本无所不在的政治经济命定性,只要资本有一个清晰的真理:利润、剥削,宁愿要资本的这种经济暴行,也不愿承认我们所处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中,一切都通过代码的效果来决定和撤消。不了解这个统治世界的“真理”——假如确有真理,这与第一次全面展现这个真理的危机本身是相称的。 因为1929年危机仍然是一次按照再投资率、剩余价值率、利润率来衡量的资本的危机,是一次按照消费的社会目的性来衡量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正是需求调节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无目的的目的性交换中解决了这次危机。从此(最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生产和消费不再是对立而且可能是矛盾的两极。这样一来,整个经济学领域和危机的可能性本身一起丧失了任何内在确定性。从此经济学领域只是作为经济仿真的过程,残留在一种完全吸收它的再生产过程的边缘 ① 。 但是,曾经有过真实的短缺吗?即有过经济原则的现实吗?否则人们今天怎么可以说这种短缺消失了,从此它只是作为神话在起作用,也就是作为富裕神话的交替性神话?从历史角度看,曾经有过短缺的使用价值吗?即有过不可简约的经济目的性吗?否则人们今天怎么可以说这种使用价值在再生产的循环中消失了,被惟一的代码霸权,代码调节的霸权所替代,这一霸权是真正的生死宣判?我们认为:经济学为了自我生产(它从来都只是生产自身),需要短缺与富裕之间的这种辩证张力——但是系统为了自我再生产,今天则只需要经济学神话操作。ˇ 因为全部经济学领域都拆除了引信,所以一切都可以用政治经济学和生产的术语表达。经济学成为整个社会的明确话语,一切分析的通俗版本,而且最好是采用它的马克思主义版本。今天,所有观念学者都在政治经济学中找到了自己的母语。所有社会学家、人文科学家等都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以此作为参照话语。这甚至包括基督教徒,当然尤其应该包括基督教徒。神圣新左派全都站起来了。通过相同的、不分场所的整合操作,一切都成为“政治”,也成为“意识形态”。社会杂闻是政治,体育是政治,艺术就更不用说了:到处都是阶级斗争的论证。资本的全部潜在话语都变得一目了然,人们在各处都可以注意到这种“真理”升天中明显表现出来的狂喜。 1968年5月标志着这种政治经济学引进中的关键阶段。因为1968年5月的冲击波从象征构造的底部动摇了系统,使“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道德、文化等等)向经济基础本身的意识形态化的过渡变得紧迫,变得生死攸关了。资本将证实针对自己的异议话语,通过这种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合法化增加自己的权力。正是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填补了1968年的断层,如同正是各个工会和左派党?就地“协商”解决了这次危机。因此,只是为了挽救灾难性形势,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隐匿参照才被挖掘出来,而它在今天之所以继续得到传播和普及,被拼命地再生产,这是因为1968年5月开启的灾难性形势还没有结束。如果我们胆大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经济学及其批判都只是上层建筑——但我们不敢这样说,因为这只可能是把这个古老的问题像手套一样翻个面而已。如果这样说,那么经济基础之类的东西在哪里呢?那么这就可能让经济学有一天按照跷跷板的方式重新出现,而这种方式本身也是代码效果。人们经常用经济基础的假象欺骗我们,我们应该把这副面具扔回去。系统自己终结了这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确定性。它在今天假装把经济学当成基础,这是因为马克思曾经天才地向它提示过这种备用策略,但事实上资本从来没有真正根据这种想像的区分运转:资本并非如此幼稚。它的力量恰恰就在于它在各个层面上同时发展,就在于它归根结底从来没有考虑过各种体制的确定性、狡诈的区分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就在于它其实并没有把自己与生产混淆,而马克思和其后的所有革命者却都混淆了,只有这些革命者曾经相信并且仍然相信生产,他们在生产中掺进了自己的幻想和最疯狂的希望。资本却满足于通过惟一的运动扩展自己的法则,无情地占领全部生活空间,不论先后次序。资本把人投入劳动,但它同样也把人投入文化,把人投入需求,把人投入语言和各种功能性方言,把人投入信息和交流,把人投入法律、自由、性关系,把人投入生本能和死本能——它在各处都同时根据敌对神话和冷漠神话来训练人。这就是它惟一的法则:随意性。需要使各种体制等级化吗?这种游戏太危险了,有可能转而损害资本自身。不:平等化、中立化、非差异化,这就是资本会做的,这就是它按照法则所做的。但它同时还要在政治经济学的“决定性”面具下掩盖这一根本过程。 在目前这种作为多形大机器的资本中,象征(馈赠与反馈赠、互惠与复归、耗费与牺牲)不再有任何重要性,自然(本原与实体的大参照、主观/客观的辩证法)不再有任何重要性,政治经济学本身也只是在脑死昏迷状态中苟延残喘,但所有这些幽灵仍在价值的操作领域里徘徊。这里也许放大并重现了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的现象:每个事件首先作为历史存在而出现,然后以戏拟的形式复活。不过对我们而言,这两个阶段相互渗透,因为古老的唯物主义历史本身也成为一种仿真过程,它甚至不能提供一种滑稽戏拟的可能性:今天,恐怖是直接表现出来的,它建立在那些被掏空了实体的事物上,各种仿象立即就在所有确定性中侵吞我们的生活。
象征交换与死亡——作为仿真模式的政治经济学 2
书名: 象征交换与死亡
作者: [法] 让·波德里亚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原作名: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译者: 车槿山
出版年: 2006-4
页数: 359
定价: 22.5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00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