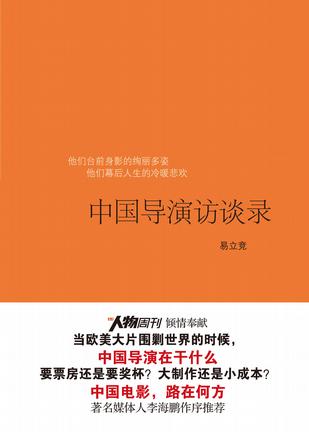易立竞:从拍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到《三峡好人》,你的电影之路走了10年,这10年里,在经济和精神上,付出和回报让你觉得平衡吗?有委屈吗? 贾樟柯:我觉得生活对我很慷慨,非常慷慨。你想拍电影,哎,真的当了导演了,当了导演还能接着一部两部,一年半一部的速度拍下去,我现在有5个故事片,3个纪录片,等于8部影片这样一个连续的产量。从第二部《站台》开始,所有影片都能够在戛纳等电影节做竞赛片,《站台》是2000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任逍遥》是2002年戛纳,《世界》是2004年威尼斯,然后到《三峡好人》拿到金狮奖,我觉得生活对我很慷慨了,还要怎么样?所以觉得没什么委屈,挺好的。 易立竞:2005年前的电影不能在国内公映的时候什么感受? 贾樟柯:那会儿的感受也不是委屈,那时候感受是有个事要解决掉它,有个山要把它翻过去。 易立竞:压抑吗? 贾樟柯:会有,有时候会难受,但是它会被创作的乐趣冲淡。比如《站台》拍完了,走了那么多电影节,得了那么多奖,然后特别想在国内放。那个时代,我觉得它有共性,大伙(年轻导演)都经历过,特别想进入到这个文化环境里去工作,但是你进不了,会很难受。可是,哎,马上又去拍《任逍遥》了,拍《公共场所》了,就会冲淡这种感受。从个人感受来说,那个东西并不会成为一个一直笼罩着导演的一个阴影。 易立竞:为了让你的电影能在国内公映,你作过妥协吗? 贾樟柯:没有作过妥协,但作过努力。 易立竞:回看自己的电影时,对当年的表现满意吗? 贾樟柯:有遗憾吧,就好像一个人看日记一样。有时候看日记,你会毛骨悚然,比如看初中时候写得那种日记,哎,怎么我当时会这么想,那是一个年龄段的认识,到今天我再看那些日记的时候,这都很可爱。 易立竞:现在回看你的电影,也都很可爱? 贾樟柯:对,我也经过毛骨悚然的阶段,再回头看,怎么会那样,但是等你工作再往下进行,你会觉得所有的天真,所有的幼稚,所有的不成熟,所有当时的遗憾,它是一种自然的状况,不可避免会有这些东西。比如说今天反省起来,如果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站台》是我最心痛的。《站台》当时如果能够公开拍的话,我相信比现在好多了。那个原剧本里头我写得特别有意思,非常多的人生活在很多公共行为里面。比如说,我原来开头不是演出,是春天,在一个山坡上,许多机关干部在种树,接下来是卡车在黄昏的时候,一卡车一卡车把人拉回来,这些场景你最起码要组织10卡车的干部,怎么组织那么多的机关干部?比如要拍一个夜晚游行的戏,你要动员一街的人,怎么封街?它都需要调动公共资源,没有公共资源帮助你,我那时候根本没办法。这个电影如果有这些东西,它会显得更强,不贫血,这种遗憾每部电影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