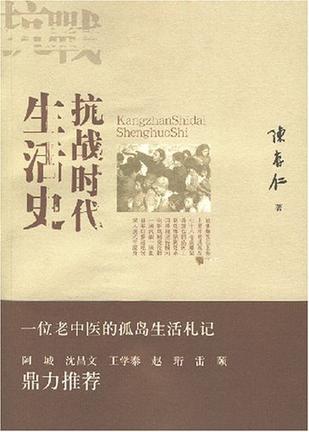陈群在三马路“米家船”楼上的居处,布置相当雅致,中央挂着一个小匾额,叫做“双宋楼”,我常常上去和他闲聊。我说:“清朝浙江归安陆心源有一个‘宋楼’,藏了两百部宋版书,著有《宋楼藏书志》,现在你这个‘双宋楼’的意思,是不是也藏着两件宋代的古物或是两部宋版书?”陈群轻轻地摇着折扇说:“看你年纪不大,肚皮里倒有些货色,竟被你一语道破,我的确藏有两部宋版书。” 当时我就讲出:“从前藏二百部宋版书的宋楼的那位主人,照书目看来,实际上只得一百二十部书,后来主人逝世,全被日人买去。现在中国人藏有一部宋版书的人已极稀少,而你竟藏到两部,真是难得!”接着我又讲出上海虽有几位收藏家,据我所知只有南浔刘家有一部宋版《史记》。哈同花园曾经藏过一本宋版《孝经》。袁寒云有过一部宋版诗集,卖给丁福保。张菊生的“涵芬楼”也藏有宋版书几种,后来编印成为《百衲本二十四史》,是由几个藏家凑集完成的,但是这件事情已成为学术界空前盛举。现在宋版书已成稀世之珍,民国二十年(1931年),北平琉璃厂富晋书铺曾经搜集到一部散佚的宋版《大观本草》,因为残缺不全,铺主人把它拆开来卖给人家,每一张的代价,是银币十元。丁福保曾经买到一张,把它裱成册页,作为医室的装饰品。陈群听我如数家珍地讲了一大篇,点头含笑,极为高兴。我又说:“同样是宋版书,也分为几种,一种是南宋版,一种是北宋版,一种是南宋版而是元代重印的,有一种是南宋版而在元代复刻的,所以版本大有区别。你所藏的两部,可能是复刻的,而不是真正的南宋版。”我这句话一出口,他瞪着两眼说:“你怎么知道这样多?”我就说:“日本人印过两种书,一种叫做‘宋版书影’,另一种叫做‘支那宋版书研究’,他们把全国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宋版书,都摄了书影加以评述,北平的中央图书馆也藏有许多宋版书,是根据日本这两种书作为参考鉴定的。”陈群听我讲完,就说三天之后,准定把他藏的两部宋版书拿出来给我看。 后来我看到他的两部宋版书,书名极冷僻,都是南宋的刻本。我告诉他北宋本比南宋本价值高得多,陈群就问我北宋本究竟是怎样的,我立刻就走到隔壁来青阁书店,借了一部恽铁樵影印的“宋版内经”给他看,是北宋的本子。陈群看了之后,呆了些时,因为北宋本的字体粗壮,版口宽阔,鱼尾美观,他自己的南宋版本书,就差得远了。接着他问恽铁樵的北宋版内经是哪里来的,我说:“讲穿了一文不值,恽铁樵根本就没有这部书,只是把日本人的影印本复印而已。”后来他又问南北宋版书的纸张怎样辨别,我说:“南北宋版本用的纸多数都带些黄色,纯白色的极为稀见,有些即使原来是白色,久藏之后,也渐渐地变成浅黄色了。”陈群高兴起来说:“我想看看丁福保医室中的那张北宋版册页。”我说:“那很容易,每逢星期五丁氏有一个‘粥会’,到时我来陪你同去参加。”(按:粥会,最初是丁福保所发起,因为无锡人晚上都喜欢吃粥,后来吴稚晖也加入了这个会,因此声名大震,第一次参加的,一定要有一个老会员介绍,随到随吃,并且大家都随带一些书画古玩,互相观摩,至今这个粥会在台湾仍继续举行。)陈群由我介绍参加“粥会”之后,对书籍版本之学的兴趣大为提高。 自从维新政府成立之后,陈群就到南京去了,我和他便没有见面的机会,不过听说维新政府的各部部长,多数是庸碌无能,对江浙两省的情况,知道得不多,唯有陈群头角峥嵘,是这群人中的智囊。 大约相别了七八个月之后,陈群回到上海,又在“双宋楼”出现,打电话找我去看书。我应约而往,只见楼上已经堆了大批旧书,看来琳琅满目,都是善本。我首先看到的是一部陶渊明集初刻本,其版本之佳、纸张之美,已是爱不释手。陈群还在招待别的客人,他说:“老弟,你不要光看这本书,在书桌上面有二十多部书,请你观摩一下,这批书是什么版本。”我就不客气地坐在书桌旁,仔细地看了一个多钟头。因为我对日本影印的“宋版书影”印象深刻,就看出这二十多部书的鱼尾,都是宋版,但是我又怀疑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宋版书集中在一处,后来我忽然有一个灵感,其中有几部书,书的第一页好像见到过,想了半天才想出来,就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几巨册伦敦古物展览画册图片中见到过,再一想,就想到了这批书可能就是南京“朝天宫”中的东西,被陈群据为私有了。但是我又不便说穿他,所以只是看而不说一句话。 陈群周旋在许多客人中,一忽儿已经排定筵席,筵席是由小有天闽菜馆送来的。陈群招呼我入席,对我说:“你看了这批书有何意见?”要我用耳语方式轻轻地告诉他是真还是假。我心想这些书真到不能再真,明明是“朝天宫”中北京故宫旧藏的珍品,但是说穿了有所不便,我只能说这是“国宝”而已。 我在回家途中想,原来维新政府的内政部部长,已把“朝天宫”中的珍本古书,都化公为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