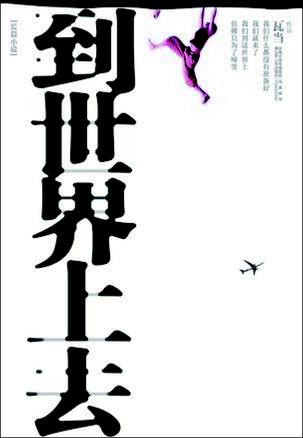“他们都叫我小玲玲。”她笑起来很调皮。 “小玲玲?”我的头一下子大了。那个传说中梳着一百零八个小辫,能打一百零八个旋子的小玲玲? “刘小威,你多大?” “十二。” “我十一。”她咯咯地笑了。 我们结伴而行,我正好经过她家门口。 “明天见!”她冲我摆摆手。 “明天见!”我一路小跑跑回家,兴奋得睡不着觉,真希望幸子永远不死,电视能演上一百集、一千集、一万集…… 小玲玲和我做同班同学是升初中以后的事情,读小学时,我和王小勇、郑成都在三班,小玲玲在一班。我们认识不久,就到了“六一”少年儿童节,学校文艺大汇演。小玲玲唱《达坂城的姑娘》,跳新疆舞,辫子飞舞,裙子旋转,金光闪闪,脖子扳来扳去,引得全场掌声雷动。 那时她刚刚从新疆转学过来不久,便立刻红遍了全校,一举成为所有男生心中的偶像。紧接着,我和王小勇登台献艺,表演唱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的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我像根电线竿子似的戳在那里清唱,王小勇在表演自创的武术,时而“雄鹰展翅”,时而“鹞子翻身”,一个不留神从台上栽了下去。台子只有一米来高,人虽然没事,台下的观众却笑开了锅。我赶紧不唱了,飞身跳下舞台,扶起一瘸一拐的王小勇,两个人在众人的哄笑中慌里慌张地跑出了大礼堂。 我和王小勇的此举,成为多少年的笑柄,一对艺苑新星就此淡出舞台。 话说小玲玲家门口有一棵巨大的桑树,一个人抱不过来,至少有五六十年的历史,我爷爷说他小时候就常在树下乘凉。每年五月几场春雨过后,树上桑葚累累,红得透紫。这时候,全城的孩子们都爬到树上摘桑葚。最多的一次,我数了数,足足有五十多个。站在树上,可以清楚地看见小玲玲家院子里的情景。她家院子里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有一次我有幸观赏到她洗澡的情景。她甩掉书包,将裙子从下面往上捋起,兜过头顶脱下来,只穿着一件红色的小裤衩。她端了一盆水,从头到脚浇下去,裤衩紧紧地贴在身上,一对小乳房微微上翘。男孩们吹起口哨,纷纷起哄,有的还摘了桑葚往院里扔。小玲玲扔了脸盆就冲了出来:“哪个王八蛋,有本事,你们给我下来!” “有本事你就上来!” 男孩们耀武扬威。 小玲玲说:“上就上,有什么不敢!”甩甩辫子,就往上攀。 刚才吵得最凶的也是扔桑葚的那个孩子见她真上来,就赶紧往高处爬,小玲玲就在后面追。小玲玲爬得可真快啊,她比松鼠还灵活。 两个人越爬越高,那个男孩慌不择路,一脚踩空,从树缝中掉了下去。 “妈呀,救命啊!” 我们都吓呆了,要知道从他站的那个枝子到地面至少有两丈高,摔下去即使不死也得落个残废。 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小玲玲翻了一个跟头,双脚勾住树枝,身子倒挂在空中,一伸手将那个孩子的脚跟捞住,借着树枝的弹力一使劲,将那个孩子扔回到了树上,那孩子骑在一棵树杈上,惊魂未定,“哇呀哇呀”地大哭起来,尿顺着裤衩往外流。 这一下子,小玲玲把所有的男孩都震住了。大家纷纷鼓起掌来,又摘了桑葚向她献媚,编了枝条帽子戴在她头上。后来,大家开始追逐打闹,比赛看谁爬得高。结果,小玲玲一口气爬到天影里去了,只看见白花花的阳光中一颗红点,像一只红鸟。她清脆的笑声,像百灵一样婉转动听。大家无不服气,一起拜倒,称颂小玲玲是女王。当时,我就站在她脚底下的一根树杈上,一脸崇拜地望着她,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凑上去吻她赤裸的双脚。她贝壳似的指甲上,画着一个个调皮的笑脸。她感到痒,笑着躲开,又用那只画着笑脸的脚趾去踩我的脸。 后来我才知道,小玲玲的妈妈就是爸爸在仓库的同事任红梅。那个女人胖大粗俗,和小玲玲长得一点不像。她们家去年刚从新疆乌鲁木齐迁回内地老家。 “那她爸爸呢?”我问。 “她没爸爸。” “没爸爸?” “没就是死了,”爸爸嘿嘿一笑,“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有个好爸爸?” “你好吗?我怎么一点都没觉得。” “操,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爸爸再不好,总归比没有强吧?”我想说“那可未必”,忍住了。 我和小玲玲渐渐熟悉起来,她便经常来找我玩。她绝不是那种小家子气的女孩,也不是李珍那种放荡无度的女孩,她恰恰是我喜欢的那种女孩,她恰恰是我的小玲玲,这个名字从我的嘴里吐出,就像一只斑鸠扑棱着翅膀眨眼就飞到了高高的树尖上。 有一次,爸妈都上班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小玲玲来了,挺着胸,背着手在房间里巡视了一周:“你一个人在?” “嗯。” “闷死我了,”她问,“你闷吗?” “闷。” “我们玩点什么吧?” “好。”我把积木、手枪、火车、轮船一股脑地搬出来。 “都不好玩了,小孩子的把戏。”她撅起嘴唇。 “那你说什么好玩?” “我们玩绑人游戏吧?”她眼睛亮晶晶。 “绑人游戏?”我头一次听说,“怎么玩?” “比如说,我是警察,你是坏人,我把你绑起来。” “我为什么不绑你?” “也行啊,警察轮着绑。” “有女警察吗?”我问。 “当然有了,少见多怪,”小玲玲又指指自己,“这不就有一个吗?” 可是,我还是不会玩。 “你这个笨蛋,”她说,“你去找根绳子来。” 我去找了根拴石头的缆绳。 “不行,太粗。” 我灵机一动,拿来缝纫机线。 “这叫绳子吗?” 最后,她自己找,把我妈的红毛线找了来:“这个正好。” “你先绑我。” 说着,她把外衣一脱,露出白色的小背心,然后坐在椅子上:“好了。” 我战战兢兢地凑上前,拿着毛线,像武松打虎似的围着她转了一个圈。我生怕捆疼她,可是她不住地说:“太松了,太松了。” 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好不容易捆牢了,结果她三下两下就挣脱了。 “有你这样捆犯人的吗?”她站起来,“看我的。” 她示意我把外衣脱了,我犹豫了一下就脱了,只剩下一条运动短裤。 她满意地点点头,叫我坐下。 她先把毛线放在嘴边吮一下,然后开始动手。毛线湿漉漉的,凉丝丝的,蛇一样游过我的胸前。我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完全被这个游戏吸引了。我的手被倒扣着捆在脑后,一点动弹不得,双膝蜷起在胸前,整个身体只有一点点屁股坐在椅子上,身体的重量被拉成了好几部分。绳子如吐着烈焰的火舌,所到之处,每一处肌肤都焦渴难耐,肌肉一阵阵地痉挛,疼痛伴随着可怕的快感吞噬了我。我挣扎着睁开眼睛,从对面大衣柜镜子里看见自己——像一只包扎紧密的粽子。 “好不好?”小玲玲趴到我面前,脸几乎贴着我的脸问。 “好。”我的声音都变得陌生。它仿佛来自我身体内部从未知晓的地方,一粒种子在体内秘密发芽。 小玲玲满意地欣赏着她的作品。 不知不觉,我的额头渗出汗来。 “放了我吧?”我咬着干裂的嘴唇请求。 “好吧,”她看看表,“五分钟,第一次这样就不错了。” 她松了绑,我的身体长时间还保留着捆绑的形状。我感觉自己像沙漠中出土的一件破碎的瓷器,一点一点地寻找自己身体的碎片,又慢慢地一点点拼回原状,用火焰弥合了身体的伤痕。这期间,小玲玲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手脚嘴巴并用,穿针引线般地把自己如麻袋般绑好,看得我眼花缭乱。 “你真棒!”我情不自禁地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