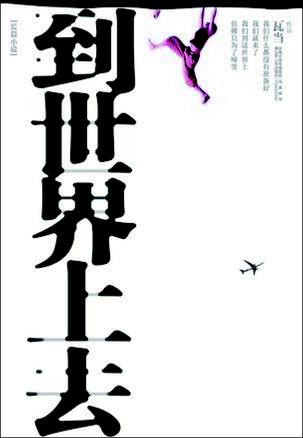“胆小鬼,”赵义武叹了一口气,“可惜我一个人办不了。” 我们三人达成协议,谁也不能把池塘下面有宝贝的事情说出去,不然的话,用赵义武的话来说就是——“不得好死!” 这个毒誓彻底封住了我们的嘴,从那以后,我们三个人之间也不再谈论水底下的事情。 那天,我们上了岸,光着身子坐在水塘南边的闸口上吃西瓜。骄阳把我们的皮肤晒成了古铜色,仿佛是古代英雄的塑像。我们托着红沙瓤的西瓜,边吃边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女人身上。 “女人每个月都会流血。”赵义武说。 “这我知道,”我不懂装懂,“原先我家和对门的四奶奶家共用一个厕所,她每次拉完大便,坑里都一摊血。” 赵义武和王小勇都笑了:“妈的,我说的是那个地方。” 赵义武说着捡起一根木棍,在旁边泥地上画了一个光着屁股的女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大圆圈套一个倒三角形,很像毕加索那种风格。 然后,他把树棍往那个女人两腿间——也就是倒三角中间有力一戳,很流氓地说了一句:“日!” 我和王小勇都笑了,我感觉那根木棍就是我的那玩意儿,它一下子就直了。学了生理卫生课,我知道它是海绵体做的,能伸能缩,就是不能折叠。 赵义武最喜欢的女人是我的语文老师兼级部团支书林丽美。林丽美一米六五的个子,身材健美,喜欢穿一条红裙子,胸前鼓鼓囊囊的两个肉团,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的。 “啧啧,别提多带劲了!” 然后,他又指了指王小勇和我:“你俩,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王小勇喜欢李珍!”我嚷起来。 王小勇捶我一拳:“一边去!” 赵义武赞许地点点头:“嗯,那是个骚货!” 接着,他又问我:“你呢?” 我没有勇气把我的心上人说出来,只能绕着弯说:“我喜欢眼睛大大的,瘦瘦的,爱蹦爱跳的。” 当时,正好有一只蜻蜓落到我的脚尖上。赵义武说:“我知道了,你喜欢蜻蜓。” 王小勇觉着赵义武给他出了气,扯着脖子笑了起来。从那以后,他只要一看见蜻蜓就说:“刘小威,你媳妇来了。” 我倒觉着赵义武说的没错,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就像一只蜻蜓。 吃完了西瓜,赵义武躺在水闸上,由王小勇摁着他的腿,做仰卧起坐。他一口气做了七十个,然后他又给王小勇摁着腿,王小勇只做了二十五个。我在旁边哈哈大笑,把王小勇气火了:“你笑!有本事你也做做,你还不如我呢!” “做就做,你怎么知道我不如你?”我将汗衫一脱,光着膀子躺在太阳晒了一天滚滚发烫的水泥板上。 王小勇使劲摁着我的脚脖子。“别给我摁断了!”我说。他嘿嘿一笑,力道却丝毫不减。我做了二十个就没力气了,可是我想到不能让赵义武看笑话,就咬紧牙齿拼命坚持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王小勇把手一松,我的身体又翻了上来:“二六!” “这个不算!”王小勇说,“这是耍赖皮!” “谁说不算?”我高兴地嚷着,我知道自己不是为战胜了王小勇兴奋,是为战胜了内心里对赵义武无时无刻不有的畏惧。 王小勇起身冲着水里撒尿的空,赵义武把我拉到一边,说要交给我一个任务。我以为要我单独行动,心里顿时很紧张。没想到,他是要我给林丽美捎个信,请她明天晚上看电影。电影演的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票提前都买好了。 我一愣:“你怎么不让王小勇去?” “他干这事不合适。” 我想不出自己怎么就比王小勇合适,但得到赵义武的信任,还是很高兴。加上赵义武连唬带吓,最后欣然接受下来,学着霓虹灯下的哨兵打了一个敬礼:“请首长放心!” 第二天早晨头一节课就是语文课,讲的是臧克家的《有的人》。“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什么乱七八糟, 我都被绕晕了。我耐住性子,一个劲儿地冲林丽美笑,笑得她莫名其妙。下课后,我跟在林丽美屁股后面。她回过头来,一脸狐疑:“你有事吗?” “有,有……”我结结巴巴地说,“林老师,有人让我给你送电影票。” 林丽美一愣,看着我手里的票:“谁?” “他不让我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林丽美鼻子里“哼”了一声:“肯定不是个好东西。你告诉他,有本事亲自来找我,支使个吃屎的孩子算什么能耐?”最后又说:“还有你,从小不学好,长大了还不知道什么样呢!” 我被她训得灰头灰脑,垂头丧气地回去交差。赵义武一听,想了半天,脸上露出了笑容:“哦,她这是考验我有没有这个勇气,我接受考验!” 下午放学时,赵义武在学校门口拦住了林丽美:“请问,您是林丽美老师吧?” 林丽美打量着这个戴墨镜、穿花褂喇叭裤的青年,说话的声音都沙哑了:“我…… 我是林丽美,你是哪位?” 赵义武摘下墨镜,两只胳膊往胸前一抱,微微一笑,接着说:“我是东方铸铁厂的,我的名字叫赵义武,今天晚上想请您看一场电影,电影的名字是……” 没等赵义武说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林丽美立刻想起了上午的事,条件反射般地喊了起来:“我不去!” 她这一喊,把周围人们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 赵义武胸有成竹地说:“就这么说定了,七点不见不散。”说着,他把电影票硬塞到了林丽美的手里。 林丽美像被烫了一下,手一抖,把票扬到了他脸上:“滚!臭流氓!”声音都发颤了。说完,甩着大辫子,扭着屁股跑了。 赵义武一脸尴尬地站在那里,回头看见我和王小勇在那里偷笑,恶狠狠地把眼一瞪:“笑什么笑?” 不光我们两个,周围的人都在笑。众目睽睽之下,赵义武把手里的两张电影票狠狠撕成碎片,冲着林丽美的背影大声说道:“等着吧,我早晚把你给办了!” 林丽美没有回头,但一定是听见了,因为她跑得更快了。当时在场的人们都听见了这句话,大家都很兴奋。这么漂亮的一个大美人,谁不盼着把她给办了? 一个多星期以后的一天,晚上十点多,林丽美下了晚自习,骑着自行车回家,一路嘴里哼着“金梭啊银梭,日夜在穿梭……”经过一片小树林,刚好唱到“看谁织出最美的生活”时,车胎突然放炮了。 她连忙下车,蹲下去看,突然有人从后面抱住了她。她想喊,刚喊了一声,嘴巴就被捂住了。那人抱起她,猿猴一般跳跃而去。到了树林深处一片缓坡上,将她放倒在地。黑暗中,林丽美看不清对方的模样,脑海中却回响起了赵义武的那句威胁:“等着吧,我早晚把你办了!”一阵巨痛过后,她昏迷了过去。 凌晨四点,林丽美在薄雾中冻醒过来,哭泣着,提着先被恶人撕破又被露水打湿的裙角,只穿着一只鞋跑回家去。林丽美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退休工人,膝下只有她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平日里疼爱有加,见到这情景,直吓了一个半死。林丽美只知道哭,问她什么也不说,不喝水也不吃饭。老两口从女儿裙子上的血迹中明白发生了什么,免不了捶胸顿足跳脚大骂。 “谁干的,你倒是说呀!”老头子气急败坏中给了女儿一巴掌,女儿的哭声骤然停止。她两眼直直地盯着面前的墙壁,夫妇俩下意识地回头去看,仿佛上面写着凶手的名字。 这天傍晚,城关派出所就要下班的时候,一对老年夫妇带着一个眼睛红肿的姑娘走了进来。除了出差办案的,当官的和老干警也都已经回家了,只留下一个刚从公安学校毕业的实习生值班。实习生一听“强奸”立刻来了兴致,他知道这是一出大案。在叫受害者填写登记表时,他在一旁不停地问着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问题:“你确定被强奸了吗?强奸可分好几种啊……”要知道,他可是学法律的呀。 林丽美被插入的那天晚上,正好是赵义武的二十岁生日。我们三个人在西关饭店直喝到十点多,然后又去十字街玩了十盘台球。赵义武真是玩啥啥行,下象棋他能让我个车马炮,打台球他能让我和王小勇俩一起上。 那晚的战况势均力敌,我和王小勇还想再玩,赵义武却将手一摆:“不玩了,结账!” 虽然是自己过生日,可赵义武的情绪却不高。他身上有种特别的东西很吸引人,过了多少年,我才明白那其实就是忧郁。他常常陷入忧郁中,这时,我们看他就完全像是一个陌生人。刚才喝酒的时候,他甚至说了这样一句话:“活着真长。”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消瘦又彪悍的年轻人分明是一个忧郁的诗人。如今我年事已高,总结过去,终于理解了忧郁是什么—— 忧郁是青春的美德! 我们走出台球房,邮电局的挂钟刚好敲了十二下。我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第二天黄昏时分,我们三个照旧坐在那座旧水闸上吃西瓜。这时候,一辆警车呼啸着从西侧的土坝上开了过来。我和王小勇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就见赵义武把半拉西瓜往地上一扣,爬起来就跑。警车擦着我们的身边飞驰而过,掀起的灰尘蒙住了我们的眼睛。赵义武一看跑不过去,转身向河畔奔去。警车嘎的一声停住,两个警察动如脱兔地冲了过去。赵义武慌不择路,跳进了干水渠,没跑几步就被芦苇绊倒,两名警察追上去将其摁倒,铐起来带走。 进了派出所,赵义武等明白了怎么回事,不由连喊冤枉。 “不是你干的你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