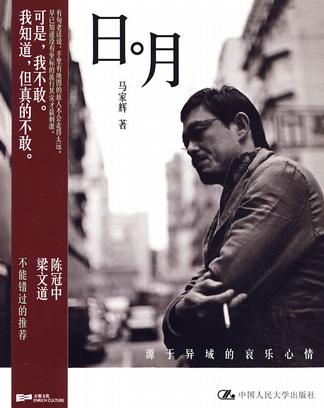时常失眠,失眠时,时常不经意地忆起芝加哥的风风雪雪。 生平第一次和雪打交道,是在芝加哥。 那一夜,在灯下啃读横行霸道的西洋经典,忽一抬头,赫然看见窗外雪粉漫飞,天色是诡异的橘红,折映成淡红的雪粉仿佛带着某种早经安排的韵律在风里旋舞。隔着窗,我真怀疑是否有人故意躲在什么地方播放音乐,遥遥指挥风雪排演一场美丽的旋舞曲,以慰我寒夜诵读之苦。好一场善解人意的雪袭。 第二次雪袭,起于傍晚。步出图书馆,等候学校巴士接载返家。校车久久未至,皎皎白雪却说来就来,一不留神,发上肩上衣上鞋上皆已皑皑。我兴奋得对身旁一位陌生女子说:“这是雪吗?这是雪啊!” 这一场雪之接触,等了二十六年。我觉得雪很温柔,不知皎皎白雪啊对我有何感觉? 芝加哥的雪是千面女郎。 在屋内炉火前独斟或沉思时,窗外的雪亲切得像一位远来访候的老朋友。雪无言,我不语,却两心知。 从超级市场提着两袋沉甸甸的食物涉雪回家时,遮天卷地而至的雪是一头张牙舞爪的猛兽,与我对峙。 夜半失眠,瞥一眼屋外树上车上街道上把一切覆盖复覆盖的厚厚积雪,总难自禁涌起一股过度自怜的凄凉。刹那间,骤觉天地茫茫,一身如寄,八方风雪尽在此。 初到芝加哥,在朋友处借住五天,后在校园附近租到一个小房间,月租两百,算是便宜。 屋主Bob是伯克利大学历史学博士,虽在De Paul大学兼课,正职却是送报员!每天凌晨三点出门送报,风雪无改! 他编写过一本To End War,并出钱出力替一个叫做“World without War”的和平组织做义工二十五年之久。怪人也。好人也。 有室友Nat,亦是怪人,一天讲不到五句话,沉静得可怕。 故我跟独居无异,整天无人可对谈。想讲话,只好上唇对下唇讲,自言自语是也。 屋内有一只黑猫,似也有“种族歧视”,不太理会我,甚少对我“喵喵”叫。我乃常对它大骂英文,以练习英语骂人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