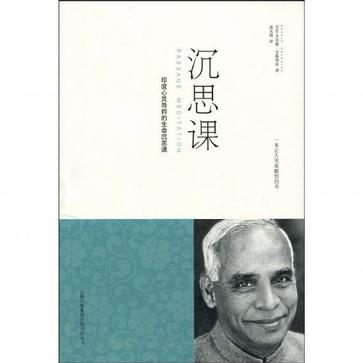我想在两个英国作家之间做个对比,两位都是我在印度当英语文学教授时的最爱:他们是萧伯纳和G.K.切斯特顿。两人的大名都经常在新闻中出现,即便是在印度,我们也对他们的私人生活多有了解。这两个人的差别可真大!萧伯纳是个高挑清瘦的男人,身上没有一磅赘肉。他是个素食主义者,当时的英国对此还不甚了解,文学界因此害怕会永远失去这位前程远大的作者。伦敦的名医也提醒他,说这种新的饮食习惯会缩短他的寿命。当然,萧伯纳活了下来,八十多岁还写了杰出的剧本。朋友们建议他去那些医生那儿展示自己的健康,他回答说:“我很乐意,但事不凑巧,他们都已经不在了。” 而切斯特顿体重则高达三百磅,还对饭桌上的乐趣钟爱有加。诸位可以想象两人相遇时的情景。两位都十分幽默,而且喜欢刻薄对方。据说有一次,切斯特顿打量萧伯纳一番后说:“老萧,见到你,别人还以为英国在闹饥荒呢。”萧伯纳反驳道:“老切,见到你,别人会以为饥荒就是你造成的。”于是问题就来了:你是愿意看起来更像切斯特顿呢,还是更像萧伯纳?这完全由你自己决定。你可以通过乱吃、暴吃让自己体型膨胀;也可以通过适度进餐、健康饮食,让自己显得苗条而精神。 反射的力量 抵御感官欲望的难处来自和我们作对的反射。打个比方,一条大河滚滚涌动,要使它停滞或者扭转流向是何等的困难!我们的多数欲望也是那样,行为的不断重复在心灵中冲出深深的河道,欲望就在里面汩汩流动。然而,就像河流可以改道或者筑坝,稳定的行为模式也能加以改变。河道存在的时间越长,改变所需的工作量也就越大。但只要运用沉思中释放的力量,改变永远是可能的。 感官的多数顽固的好恶都是在生命的早期习得的。一位母亲给尚在学步的孩子一小盘原味酸奶,这时一位已经形成反射的邻居皱起鼻子,厌恶地呻吟道:“原味的酸奶?”只要这样重复几次,孩子的神经系统就会对刺激形成自动化的反应;这就形成了反射。每当这样的反射形成,我们都会失去一点自由和一点选择的能力。这孩子总有一天会对任何健康但带酸味的食物皱起眉头,大叫一声:“不要!”然后把盘子推开,他离这一天已经越来越近了。 我们多数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当然,通常,我们并不记得自己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获得了反射。让我们产生反射的人当时大概也不知道自己正在教授我们如何做出反应,并在我们的意识上套上了限制。我们觉得,令人不快的是食物本身,我们不喜欢端到面前的酸奶是因为它味道不佳——尽管邻座的女士正快乐地享用一大碗同样的东西,没加佐料也没加糖。酸奶是一样的酸奶,两个人的反射却不相同。 不久之前,我在一位想成为足球运动员的年轻朋友身上目睹了这种反射的巨大力量。他讨厌美洲南瓜,我倒觉得这种蔬菜没什么不好。一天我对他说:“如果主跑来对你说,‘每天都吃美洲南瓜,就让你成为美国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你会怎么回答?” 他沉默了,我可以看见在他意识中上演的战斗。最后他说:“我会对他说,‘主啊,我不干。’” 喜好的力量也可以同样强大。我的家乡喀拉拉邦盛产腰果,乡亲们大多对它钟爱有加,我也很喜欢这种果子。但在我离开喀拉拉去印度中部的一所大学任教时,腰果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来美国时,有人把一大罐腰果当做礼物送给了我。我打开罐子,心灵的反应让我惊讶:从前的吸引力一下子涌现出来;我听见心灵在说,“哎哟……腰果!终于能吃了!” 但这一次我已经了解了心灵的脾性,而且我刚好在训练自己的感官。于是我说:“哦,腰果的味道还记得吧?” 心灵说:“少废话啦……我们快去拿来吃吧!” 我答道:“我看你是又忘了谁说了算吧。我知道你喜欢这些个小坚果,我这就和你做笔交易:只要你不再一刻不停地为这些腰果闹腾,我就马上给你几颗尝尝。” 接着,我把打开的腰果罐头放在了身边的桌上,专心做我的学问去了。战斗持续了一阵子。我念着一篇措辞尖锐的散文,是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写的;突然之间,我觉得有什么又小又滑的东西碰到了指尖。原来是我的部分心灵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我的手派遣到了腰果那里。“怎么回事?”我严肃地问道。 “没……没什么,”心灵说,“我们一颗都不会吃的。只想知道它摸起来是什么感觉。” 不用多说什么了。我的手退了回来,心灵也匆匆回到了它本该驻留的《论美国学者》。 心灵终于放弃花招,平息了下去。我望着腰果罐头,看见了它们的本来面目——坚果,生长于印度,我以前居住的地方——这时心灵纹丝不动。“做得好,”我说,“现在你可以吃一些了。”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腰果,因为我是带着自由吃下它们的。 刚开始学习跟自己的好恶较量时,内心可能会充满恼怒。你选择的食物并不好吃,决定不吃的倒可能味道甘美!但过一阵,努力习得的高超技巧会让你觉得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你或许还会像地摊杂志上写的那样:“给朋友和同事送去惊讶。” 我认识一位女性,她在刚开始感官训练时跑去一家冰淇淋店问店主:“你们这儿味道最差的是什么?” “甘草冰淇淋,”男店主答道,“一定就是甘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