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勾沉與出新--《張愛玲譯作選》/單德興
(本文作者為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兼所長)
「作家張愛玲」眾人皆知,但「譯者張愛玲」知者相對較少,至於她在翻譯方面的成就與貢獻則更罕為人知。
其實,名聞遐邇的「張愛玲」一名本身就是翻譯。她在《流言》中的〈必也正名乎〉一文開頭就說:「我自己有一個惡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換一個……」至於自己為什麼「戀戀於我的名字」,卻一直到結尾才道出緣由:
十歲的時候,為了我母親主張送我進學校,我父親一再地大鬧著不依,到底我母親像拐賣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在填寫入學證的時候,她一時躊躇著不知道填什麼名字好。我的小名叫煐,張煐兩個字嗡嗡地不甚響亮。她支著頭想了一會,說:「暫且把英文名字胡亂譯兩個字罷。」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沒有改,到現在,我卻不願意改了。
根據這則作者自道的軼事,她的小名是「煐」,英文名是 “Eileen Chang”,而大名鼎鼎的「張愛玲」卻是十歲臨入學時,母親情急之下「暫且」「胡亂譯」的應景、甚至將就之作。這則出入於中英文之間的童年軼事,似乎也預言/寓言了她未來從事的中英翻譯。
其實,張愛玲很早就步上了翻譯之途。一九四一年,年方二十一歲的她便摘譯了哈而賽的〈謔而虐〉(Margaret Halsey,“With Malice toward Some,” 1938),發表於上海《西書精華》季刊。後來她又中譯了摯友炎櫻(Famita Mohideen)的若干作品,發表於上海的《小天地》、《苦竹》、《天地》、《雜誌》等月刊。有趣的是,她也以中文重新翻譯或改寫自己的英文作品,包括一九四三年發表於上海英文刊物《二十世紀》(The XXth Century)上的一些文章與評論,以及將 “Stale Mates: 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 重寫為〈五四遺事:羅文濤三美團圓〉,“A Return to the Frontier” 重寫為〈重訪邊城〉,The Rouge of the North 重寫為《怨女》,“The Spyring” 改寫為〈色,戒〉等,扮演起「改寫者」、「自譯者」的角色,並且樂此不疲。其中雖有一些為早年的嘗試之作,但連同其他文藝創作,可看出張愛玲左右開弓,中英並進,多元發展,展現了強烈的雄心壯志。
然而,張愛玲的譯者身份與地位主要建立於她的「香港時期」(一九五二─一九五五),雖然只有短短幾年,成績卻相當可觀,不僅對於當時的美國文學中譯貢獻良多(詳見下文),對於個人的文學生涯也有重大的影響,如《秧歌》(The Rice-Sprout Song)與《赤地之戀》(Naked Earth)均分別以中英文撰寫與出版。細究起來,她在翻譯方面的成果還包括了英譯陳紀瀅的長篇反共小說《荻村傳》(Fool in the Reeds,1959)以及英譯自己的小說〈等〉(“Little Finger Up,” 1957)、〈桂花蒸 阿小悲秋〉(“Shame,Amah!” 1962)、〈金鎖記〉(“The Golden Cangue,” 1971);譯注清朝韓邦慶的吳語小說《海上花列傳》為《海上花開:國語海上花列傳一》和《海上花落:國語海上花列傳二》(一九八三),並將此書譯為英文,前兩章發表於《譯叢》(Renditions,1982),全書 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 經孔慧怡(Eva Hung)校訂,二○○五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由此可見張愛玲的譯者身份之繁複多樣,而且與她的文學創作密不可分。此處僅就本書收錄的中文譯作選(全為美國文學)略加說明。
文學與翻譯等文化生產,與時代密切相關。首先就時代環境而言,當時適值冷戰時期,美國在國際上採取圍堵政策,除了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方面與共產主義對抗,防止其擴張之外,在文化方面也採取相同的策略,於是在香港成立文化機構,出版刊物和書籍,前者如《今日世界》(World Today〔一九五二─一九八○〕,原名《今日美國》,先是半月刊,一九七三年起改為月刊),後者最著名的就是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翻譯叢書,總計高達數百種,其中又以美國文學的數量最多、影響極為深遠。今日世界出版社縝密規劃,以優渥的稿酬廣邀港、台著名譯者、作者、學者,可謂當時的「夢幻隊伍」,大規模、有系統地中譯與美國相關的作品,數量之多、品質之精、水準之齊,可說是空前絕後。雖說該出版社成立的初衷有其國際政治的考量,但以後見之明來看,其成果遠遠超越一時的政治,而為中文世界留下了頗具意義的文化資產。筆者這一代許多人在戒嚴時期都由此一翻譯系列獲得啟蒙,至今依然懷念不已,即是明證。
再就張愛玲當時的處境而言,共產主義席捲中國大陸,在上海已有文名的她南來香港,亟需一份穩定的收入。咸信是在上海舊識宋淇(林以亮)的協助下,她開始為今日世界出版社翻譯。一方面,今日世界出版社亟需大批中英文俱佳、且在文藝界或學術界具有知名度的人來從事翻譯;另一方面,就張愛玲而言,與該出版社合作,不只是為稻粱謀(其優渥稿酬是許多人樂於應邀翻譯的重大誘因),更可善用這個良機與管道發揮自己的語文專長與翻譯經驗,甚至藉由出入於中英文之間不斷修訂自己的文學創作,進而嘗試打開通往國際文壇之路。換言之,雖然處於冷戰時期,合作的雙方也各有所圖,但結果卻各蒙其利,並嘉惠廣大的讀者,遠超過一時一地的政治氛圍與現實考量,成為文壇與譯壇難得的佳話。
綜觀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美國文學名著譯叢便會發現,即使其中的譯者高手如林,但產量之豐像張愛玲這樣的並不多見(數量最多的當推晚近謝世的名譯家湯新楣〔湯象〕)。更重要的是,她的翻譯是全方位的,遍及各文類,其中以小說居多,包括海明威的《老人與海》(Ernest Hemingway,The Old Man and the Sea),勞林斯的《小鹿》(Marjorie K. Rawlings,The Yearling,後易名為《鹿苑長春》),歐文的〈無頭騎士〉(Washington Irving,“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後易名為〈睡谷故事〉);詩歌有愛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和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詩作,均見於《美國詩選》(此書由林以亮編選,掛名的四位譯者由張愛玲領銜,其他三位依序為林以亮、余光中、邢光祖,未掛名的譯者尚有梁實秋和夏菁);散文主要見於《愛默森選集》(The Portable Emerson,後易名為《愛默森文選》,內含譯詩);文學評論有〈海明威論〉(Robert Penn Warren,“Hemingway”)和《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Seven Modern American Novelists)的〈序〉(William Van O,Connor,“Introduction”)以及其中的三章--〈辛克萊.路易士〉(Mark Schorer,“Harry Sinclair Lewis”)、〈歐湼斯.海明威〉(Philip Young,“Ernest Hemingway”)、〈湯麥斯.吳爾甫〉(C. Hugh Holman,“Thomas Wolfe”)。至於戲劇則可能是威廉斯的《琉璃集》(Tennessee Williams,The Glass Menagerie),因為今日世界出版社的兩本目錄對此書譯者記載不一:《今日世界譯叢目錄》(一九七六)載為「張愛玲」,但《今日世界出版社圖書目錄,一九八○─一九八一》(一九八○)卻載為「秦張鳳愛」,成為「張學」中的一樁疑案。其中早期的譯作,如《老人與海》和《小鹿》,先前分別由香港的中一出版社與天風出版社印行(前者使用筆名「范思平」),後來納入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美國文學譯叢系列,重行設計與增訂後,更廣為流通。
正如筆者在〈含英吐華:譯者張愛玲--析論張愛玲的美國文學中譯〉一文中所指出的:
張愛玲翻譯的這些美國作家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其中有早期經典作家歐文(Washington Irving),美國文藝復興時期與超越主義大師愛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與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小說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954]),普立茲獎得主勞林斯(Marjorie K. Rawlings [1938]),以及當代美國小說評論。換言之,張愛玲翻譯的範圍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當代文學。她翻譯的《老人與海》早在海明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前兩年便已問世,相當具有先見之明。評論集《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由張愛玲翻譯其序言及七章中的三章,實質上已佔了全書一半。該書於一九六七年出版,距離原著出版僅三年,即使以現今的標準也算頗能掌握時效。由上述可知,譯者張愛玲的興趣廣泛,並有能力處理不同時代、不同作家及不同文類的作品。
張愛玲翻譯的策略與特色也值得一談。套用翻譯研究的術語來說,翻譯策略主要分為兩種:歸化(domestication)主張翻譯成品要像通順流暢的譯入語/標的語言(target language),以方便讀者閱讀;異化(foreignization)主張翻譯成品應盡量維持譯出語/源始語言(source language)的特色,以豐富譯入語的思維與表達方式。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翻譯策略主要為歸化,這種翻譯觀可以曾為該社負責編務的林以亮以及擔任翻譯的思果和余光中的譯論與譯評為代表。這種翻譯策略,配合譯者的知名度,以及出版社的行銷(印刷精美,價格低廉,通路順暢),使得今日世界出版社的譯叢系列順利進入中文世界,尤其在台灣和香港發揮了最大的影響。
至於張愛玲本人的翻譯,基本上依循今日世界出版社的方針,包括在必要時加上原著譯文之外的一些附文本(paratexts),如序言、譯注,以幫助讀者閱讀與理解,進而增加對於美國文學與文化的認識。縱使偶爾出現異化(尤其是譯詩)與誤譯的現象,但整體說來譯筆頗為信實、通達、洗練,充分發揮了雙語者張愛玲身為中、美之間的文學翻譯者與文化溝通者的角色。
可惜的是,由於相關資料欠缺,以往的「張學」甚少觸及「譯者張愛玲」的研究。更遺憾的是,有別於一般的合約,當初美國新聞處是以「採購單」(purchase order)的方式向譯者購買「服務」(service),而非版權,再加上近年來許多譯者相繼謝世,而我國與美國在智慧財產權談判時忽視翻譯,未能要求強制授權,以致在今日世界出版社結束營業後,此一翻譯系列礙於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而難以重新印行,讓前人心血結晶的智慧與文化資產就此湮沒,只能在舊書攤或二手書網站苦苦搜尋,實在令人扼腕。
因此,我們一方面欣喜於《張愛玲譯作選》在有心人努力下得以面世,廣為流傳,另一方面也惋惜其他「張譯」因為版權問題遲遲不能重現於中文世界(據熟悉內情者透露,有些尚須等到二○四○年代才能出版)。至盼張愛玲的所有譯作(包括不同的中英文版本)都能早日勾沉出新,重新流通,讓世人有機會進一步了解張愛玲如何出入於中英文之間,認識她在翻譯方面的成就與貢獻,為原已繁複多樣的張愛玲增添另一番面貌。
二○一○年二月一日
台北南港
附識:本文主要根據筆者《翻譯與脈絡》(台北:書林,二○○九)中的〈含英吐華:譯者張愛玲--析論張愛玲的美國文學中譯〉(頁一五九─一七九)與〈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頁一一七─一四六)。張愛玲的譯作一覽表可參閱前者之二附錄(頁一八○─二○一),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美國文學中譯分類表可參閱後者之附錄(頁一四七─一五七)。本文撰寫期間承蒙鄭樹森先生與高全之先生惠賜高見,陳雪美小姐與金文蕙小姐提供資料,謹此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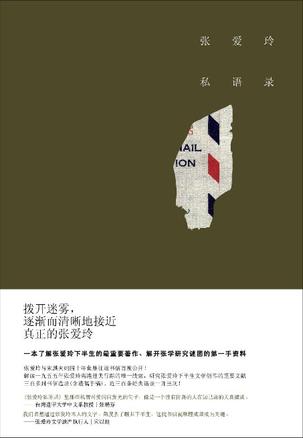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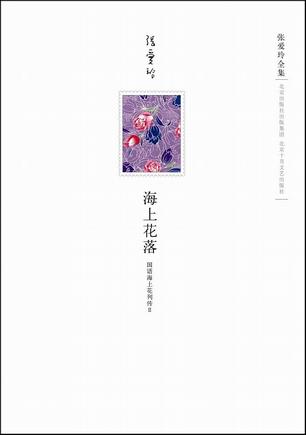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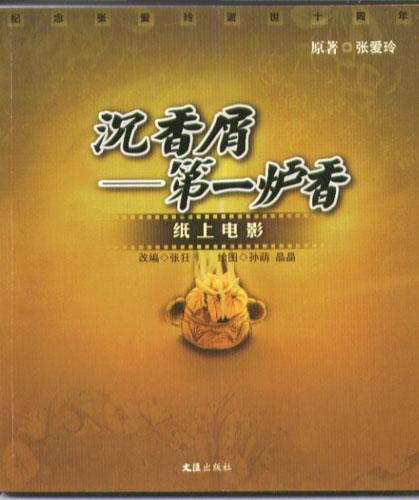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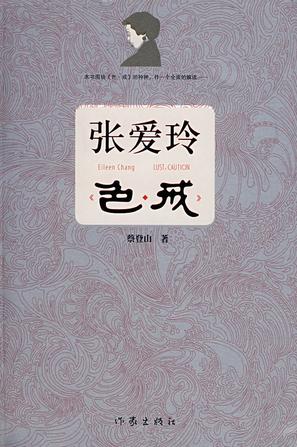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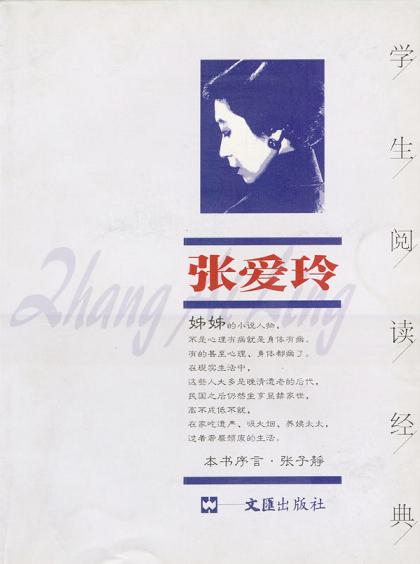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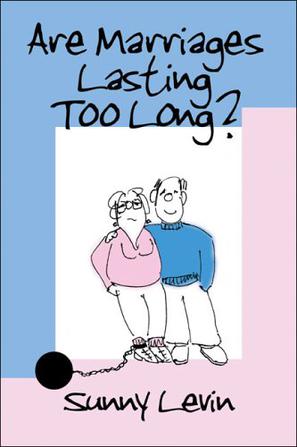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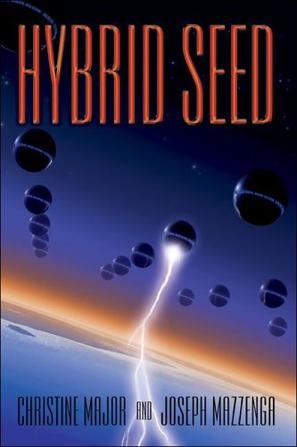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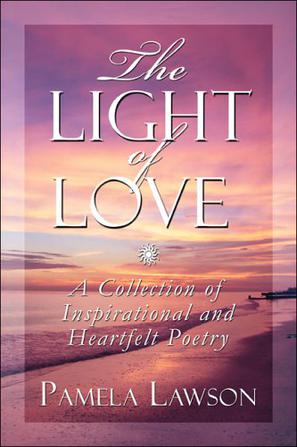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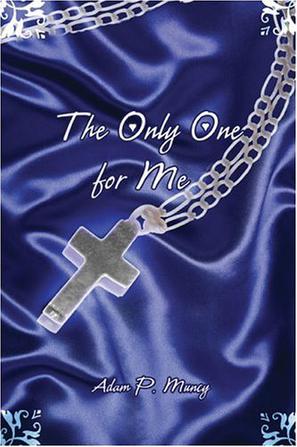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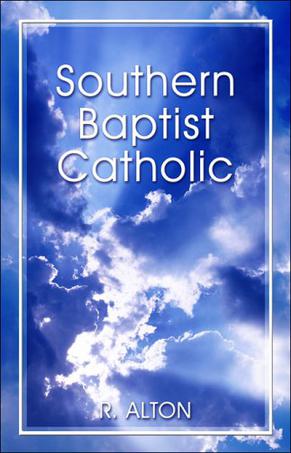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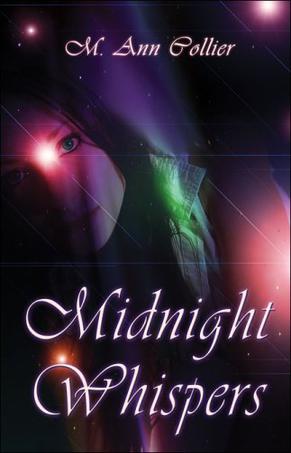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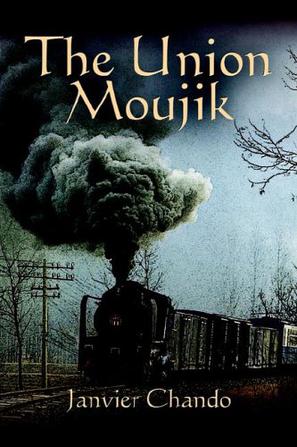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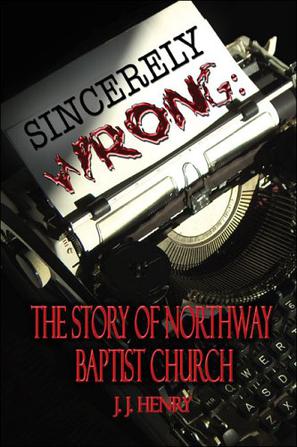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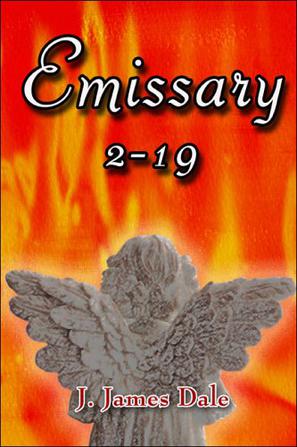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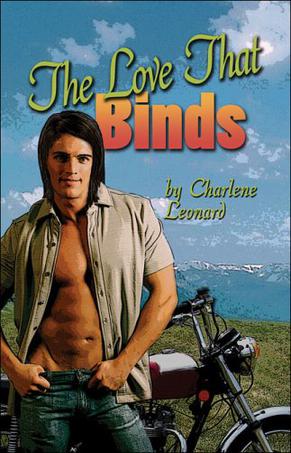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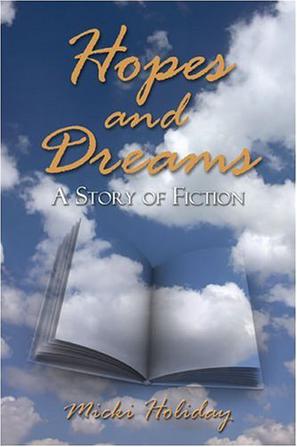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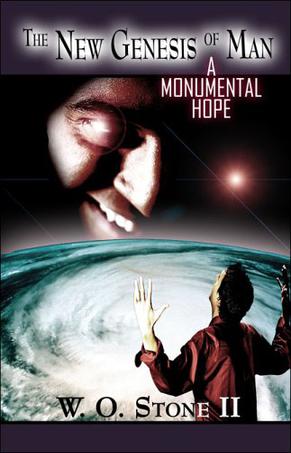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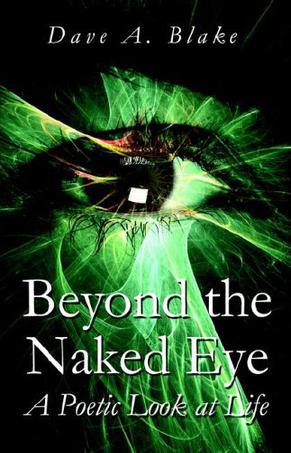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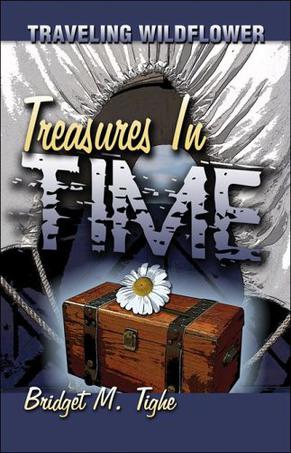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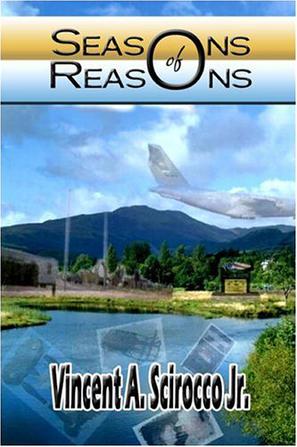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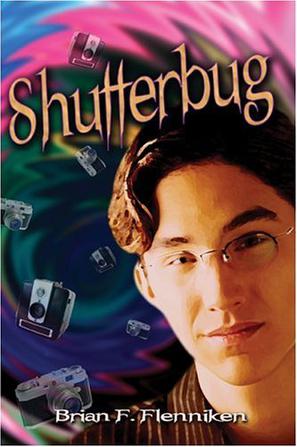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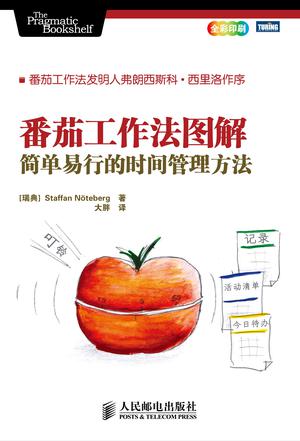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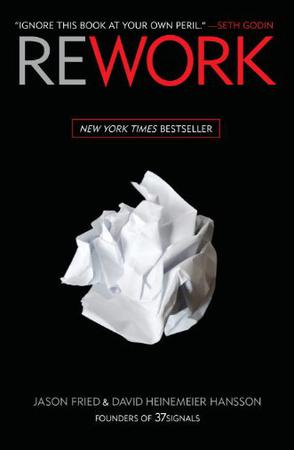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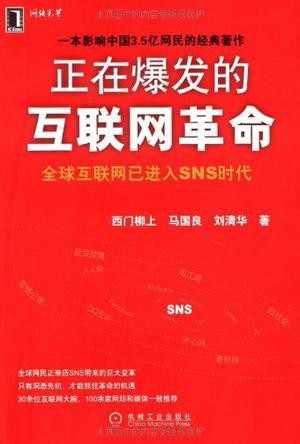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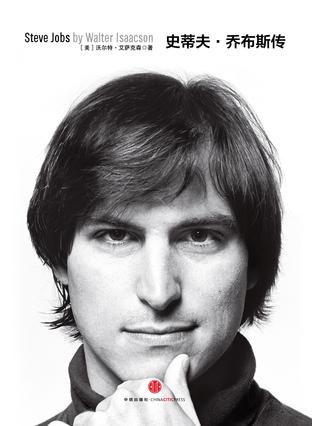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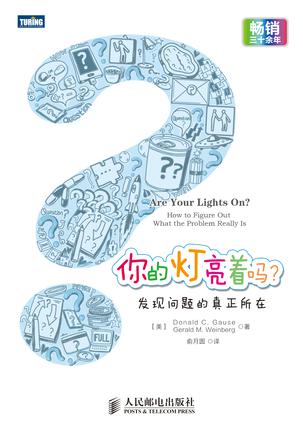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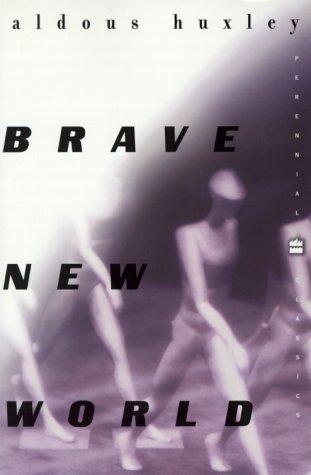
评价“張愛玲譯作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