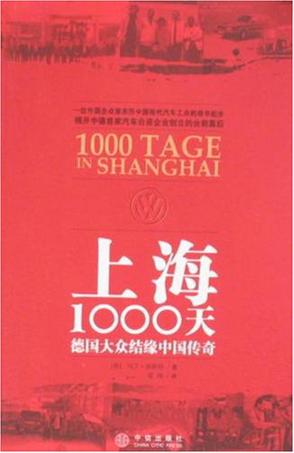1 有那么一刻我呼吸停止: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些落伍的厂房,脑子一片空白。难道这些遍地尘土的简棚陋屋,就是一家汽车制造厂?就是在这种地方,大众要联合中国人一起造车?然而,望一眼公司的招牌,证实了我的确没有走错地方。我站在上海拖拉机汽车总公司,即上海拖汽总公司的一家工厂前,这是家中国的国营企业,而狼堡的大众集团刚与这家企业签订了合资合约。这份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SVW)的合同才于前几周,即1984年10月10 日,在北京签署。 与安亭工厂的初次接触 时间是1984年11月初。我从汉斯-赛德尔基金会那个小型的巴伐利亚代表团活动开溜了一天。这个团受邀于中国友协,在中国已遍游三周。作为奥迪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我想近距离观察一下我的母公司不久后要与中国人共同建设中国首家现代化轿车生产地的地方。 在一名中方代表团团长的陪同下,我坐着出租车从上海市区出发,前往其西北部30公里之外的安亭,嘉定县一个所谓的工业区 “industrial zone”,英语——译者注 中的一座村庄。由于自行车、水牛,加上本身的路况,车快不了,我们在路上就花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路边,看到的是农民在稻田里劳作。我们的车也顺带给农民们特意铺洒在路上的稻子脱粒。尽管我早已预感到,中国人急需实现生产的现代化,但第一眼看到某一天会成为上海大众的那块地方,这种隐约的预感却变成了痛苦的事实:大量的金属废料散乱地堆放在厂区地面上,那些房屋,与我们想象中的生产厂房,风马牛不相及。 窗户漏风。那条满是沙土、未经夯实的道路从厂区中央穿过。室内不仅与室外同样潮湿,而且还同样阴冷。没有暖气。我觉得,这一切似乎被如此荒废,可以说是到了被拆毁的境地。这根本无法想象,某日如何从这样衰败的厂房,生产出来哪怕只有那么一辆我们可以勉强认可的轿车。“天啊”,这一声惊叹在我脑中回旋,“谁要想在这里同中国人合作,那将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狼堡对那份合资合同做何考虑?带着这个疑问,我离开了安亭,在上海市区与代表团汇合,不日便返回德国。 首次中国之行的经历,让我思考良久。在那里,人们生活在欧洲人几乎无法想象的贫困境地可同时,我又能感受到整个国家对改善的期盼。人们表现出乐观主义的精神,一种实实在在的对变革的兴致。这种情形,我在德国鲜有经历,那个共和国在经济奇迹发生后的年代里似乎更想安于舒适的现状。 其时,我年届四十,才刚刚签订了一份担任奥迪人事董事的为期5年的新合同。当时,我有着幸福的婚姻生活,两个妙不可言的女儿、一幢新的楼房、一名司机;总而言之,我拥有人们想拥有的一切。但是,伴随着中国之行,那种印象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加深:天啊,这世界也还有另一面呢。我要重新定位。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邀请世界各国的企业,以资本和关键技术参股于中共倡导的工业现代化项目。以西方技术和西方管理知识为交换,中国人首次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了通往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国家市场的通道。那是一个未来将有显著增长率预期和指日可待的诸多赢利前景的市场。因为当时,无论如何,中国的需求增长在望。 与世隔绝了一百年,经历了各种动乱、内战和饥荒的几十年,中国大地似乎开始了一个新纪元。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济改革家逐渐地在管理着那个泱泱大国的中共组织中赢得优势。那些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家们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社会已超过10亿的人口,会随之带来各类诸如粮食和能源等的供给问题。改革家们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中国农业和工业低下的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这些问题才能得以解决。为此,这个1983年人均年收入尚不足350美元的国家,需要来自外部的经济援助——尤其是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 中国政府计划在上海将汽车工业扩建成重点产业。由于汽车工业为其他许多现代化国民经济行业的核心,所以一开始,中国人就特别坚定地推动着它的发展。早在1978年,中国政府的代表就开始与德国大众商讨在上海合作生产轿车事宜。因为在那里——中国的经济改革家们决定——应该形成一个中国汽车工业未来的重心之一,即中国的底特律。 藉此,上海可以传承20世纪30年代的传统。当时,这座城市是汽车之都,这块土地上曾有过一次中德合作。采用德国进口的零部件和以技术援助的形式,中国人于1936年在上海制造了他们自己的第一批卡车,发动机和关键技术则是来自戴姆勒—奔驰股份公司。 不过,中国汽车工业史的真正开端,一如名称所揭示的那样,其实是第一汽车制造厂,简称“一汽”。该厂于1953年在俄罗斯人的援助下建于吉林省首府长春。就其面积而言,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厂,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汽车帝国,是那个有着百万人口的城市——长春的象征。一汽的第一代中方筹建人,来自中国的各个汽车制造厂,其中大部分来自上海。1969年,十堰的“二汽”,即第二汽车制造厂,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它吸纳和采用了长春一汽的专业人员和工艺技术。十堰距武汉西北方大约有半天的火车车程,而武汉作为人口密集的湖北省的省会城市,是中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之一。出于战略考虑,二汽未直接安置在武汉市,而是落户于偏僻的山区腹地;这样,一旦发生军事纷争,敌人要进入该地区便没那么容易。二汽职工的构成,表明了中国汽车工业三大基地,即上海、长春和十堰的代表们的推心置腹。 上海拖汽总公司是典型的国营企业,1959年以来在安亭制造了以“凤凰”(Phoenix)命名的一种汽车,那是一款仿照 1956年由戴姆勒—奔驰推向市场的梅赛代斯220 S的车型。60年代早期停产一段时间之后,这款车型于1964年又以新的名字“上海牌”进入批量生产。70年代中叶以来,上海拖汽总公司每年生产3 000~5 000辆这款车型。三家汽车厂,一汽、二汽和上海拖汽总公司,均是典型的国营企业。只是上海拖汽总公司不像一汽和二汽那样直接受北京的中央政府领导,而是属于具有政府直辖市特征的上海所有。 寻找中国开路先锋 当我在印格尔斯达特的办公室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从中国回德国才三天。我拿起听筒。“我是维斯纳。波斯特先生,还好吗?”埃克哈特?维斯纳博士负责大众集团所有国外企业的人事工作。不管是在墨西哥还是在南非,只要是涉及安排公司高级职位的事宜,均由维斯纳博士负责。“我还好”,我答道,“刚从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回来。”维斯纳道:“所以我才打电话给您。您倒说说看:你们那里有没有一个财务控制人选?”“我们这里有很多财务控制员。您要的是哪一级别的?”“科长级。”那时,集团内划分有四种不同的主管领导等级:董事级、部长级、处长级和科长级。要寻找一名科长人选,宁可求一个比较经济的解决办法,即找一个具有公认的业务能力、但领导才干不一定出色的人。“那么,那名控制员的工作是什么?”我询问道。维斯纳答曰:“喔,我们在寻找派往中国的头号人选。” 难道是我听错了,还是他真的这么认为?难道维斯纳真的十分严肃地认为,那个中德合资的汽车厂只靠一名财务控制员身居领导要位就可以建成了?对安亭那个衰败的总装车间,我还记忆犹新。因此,我恳求维斯纳说:“维斯纳先生,我刚从中国回来。您可知道,那里是怎样的情形?您想一开始就把企业搞垮?我去过安亭,察看了上海拖汽总公司的那家工厂。您完全想象不出,那里是什么状况!如果想在那里有朝一日用汽车来赚钱的话,您需要派遣经验丰富的领导人员,实干家类型的,并要将必不可少的开路先锋的精神带去。” 维斯纳博士,这位从头到脚地地道道的人事专家,表示反对:“您说的也许是对的。可是,我们付不起这些人的工资。那个合资企业还没有赚钱。一切皆空,八字还没有一撇呢。”我继续问道:“那技术方面上您有哪种人选?”他回答:“啊,那方面我们已经有个科长级人选了 ……”我试图再次说明,面对中国的挑战,我们需要的不是二流或三流的人员,而是具备企业管理经验和勇气的一流领导团队。我坚决提请维斯纳再次慎重考虑一下整件事情。此间,可能由于情绪激动,我脱口说出:“说来说去,还不如我本人来干。” 就像我随后得知的那样,我那句顺便带出的口头意见,却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因为紧接着,维斯纳就到大众董事长卡尔?H哈恩博士那里汇报了我们的通话内容。“我与波斯特谈过了,他刚刚结束长长的中国之行。他也去安亭了解了情况,并告诫说,派一名控制员作为中国企业的领导不太好。另外,”维斯纳补充道,“我感觉他本人可能对此工作感兴趣。” 而在与维斯纳通话之后,我自感有义务向哈恩博士通报我为何担心中国业务的成败。我致电博士:“哈恩博士先生,虽然您是掌管一切的监事长,但今天我想跟您谈谈计划中的中国区业务。只派一个财务科长去中国,我们在中国的企业将一事无成。”哈恩博士答道:“您说得完全正确。中国业务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为此我们需要另外的人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恩博士借机也问了我,这份工作是否会对我本人有吸引力。我遂平息了误会:“我没当真,我当时只是激将一下而已。”我们相互约定另找时机深入这个话题。 然而最后,我对刚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那个泱泱大国的好奇心,占据了上风。我可以一同经历那个国家如何开放国门,行动起来并发生变化的过程;或许,我们甚至还可以以我们的创业来一同为构建这个国家尽微薄之力。中共决心进行的这项借助西方合作伙伴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世纪工程令我敬佩不已。最终,我为自己设想了对于第一个勇于吃螃蟹的西方汽车制造商而言,中国市场蕴藏着的无限商机。 这种能够直接推动一些事情发展的机会,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思忖着,“如果你在德国做什么事,你会浪费你一半还多的时间来管理,由此浪费了宝贵的精力。但是在上海每一步均会带来结果,即使有时会有磕磕绊绊甚或倒退。而这一切,均是你自己可以安排掌控的。”经过认真思考,我告诉自己:“这才是你想做的事。” 圣诞节期间,我向我当时的妻子海尔佳—英格讲述了那份供职提议,并最后承认:“我打算接受这份工作。”我妻子没有提出异议,相反,她倒是愿意冒这个险。于是,我们正式对两个女儿宣布:“我们有个惊喜要告诉你们!”亚力克莎,当时7岁,而雅娜,近8岁,坐在走廊上,高兴地期待着祖母送给他们的小礼物。因为一般情况下,那是紧随着我们的这种告知后发生的。不过这次并非是小包裹,而是一次前往世界另一端的搬迁。孩子们顿时欢喜雀跃,开心起来。她们对中国的所有了解,都是从我中国之行回来后的叙述中拼凑而得。这些报道也足以让她们激动。两个女孩高兴得手舞足蹈,在房间来回穿梭,欢呼着: “我们到中国去喽,我们到中国去喽!” 在热烈期待的欢乐气氛中,这两个孩子的小脑瓜里又会描绘出怎样一个童话般的国度?她们把中国想象成什么?面对雀跃的孩子,一丝疑虑向我袭来。几周前我才第一次踏入的那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会经受住孩子们这种期待的欢乐、实现这种抑制不住的期望吗?不管了,事已至此,我们就去上海吧。顺带说一句,如今我从女儿处得知,她们1985年在中国发现了正巧令她们高兴不已的东西:那是她们好奇打探到的一个令人激奋的“儿童冒险游乐场”。 于是,狼堡、印格尔斯达特和相关的经济新闻报出了这样一条消息,奥迪公司的人事长官马丁?波斯特,将成为大众在华的第一号人物。这消息像一颗炸弹落地。为何不选“纯种的”狼堡人?为何是一位人事专家?人们疑惑着。为何波斯特会有如此之举?他是否失去理智了,让他要将迷人的印格尔斯达特里董事的皮交椅,与世界另一端贫穷国度里的硬板凳调换?有些记者猜测我肯定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以致让我觉得离乡背井不失为可取之举。不管怎样,德国国内有许多人对我的决定持怀疑态度。 只有少数人理解,亲历中国发生的巨变过程这件事,着实吸引着我。当然,安亭那些无精打采的工人和满是灰尘的工厂的景象,也震憾了我。中国人不就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方式极其落后才需要我们的吗?只要人们在1984年有那么一点想象力,就可以想象得出,这家合资企业的成功会给大众集团提供何等巨大的商机。倘若中国的共产党人成功将国有计划经济向国外私有资本开放的话,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缓慢但肯定——会成长出世界上最大的国内销售市场之一。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觉醒阶段。人们想要变革,正如我所发觉的那样,其间他们确实会需要我们的援助。 1985年1月,时任奥迪的人事董事为了大众事业而奔赴中国。于是,整个事件其后的发展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变化。狼堡的生产董事葛恩特?哈特维希博士,原本已为上海的技术工作挑选了一名科长,却又抽回了他的候选人成命。他或许是做了如下一番思考:倘若哈恩博士将波斯特——尽管“只是”在子公司奥迪、但毕竟还是董事会成员——派至现场,那我便不能随便任命一位科长前往上海,也需要我这摊里最好的人选。”这位最好的人选名叫汉斯—约阿希姆?保尔,是大众卡塞尔厂的部长,由此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那真是一件幸事,因为没有保尔,上海大众这家企业或许不会运转起来。虽然我们两人分别由两个互相竞争的集团派系任命,而两大领导波斯特和保尔在整个事件之后的运作中却蜕变成为幸运组合,一个“理想团队”,一如哈恩博士在他的《大众岁月回忆录》里所称的那样。 1985年1月初,我和保尔首次在罗特大院碰面。那是一家大众设在狼堡的招待所。从外表看,保尔就是一个专为投身远东地区天然而成的人。这位因其亚洲人脸型而被同事冠以绰号“蒙古人保尔”的工程师,据说是在认识我之后才做出了决定。我向他开诚布公,说我已决定接受中国的工作,同时向他解释了我的理由。我们一见如故。我们第一次碰面之后,我就知道,对于上海等着我们去完成的那项建设工程来说,他是绝好的事业搭档。而保尔必定也在我们谈话之后坚定了信念,因为他离开了卡塞尔,为的是作为上海大众公司执管会的技术执行经理走马上任。 为在中国创业做精心准备 避免亢奋型或混乱性忙碌。给予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来让事业成熟完善起来——不管在何种情形下,您的中方伙伴会抽出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来。 合同谈判在中国人眼里,意味着建立一种长期的关系。以这种关系积极配合,参与其中。 合作伙伴关系远比策略性的接触更深一层,这种关系必须出于本意,且发自内心。 不要经常更换谈判小组的出场人员,记得将以后现场负责项目的员工吸纳进来。 记住:彼此相处的原则由人自己拟定,并非一定得通过合同、法律和规则来加以规定。故此,在公司合同谈判阶段就要设想今后各种可能出现的冲突情况。 倘若涉及解决一些困难的、您和您的合作伙伴都不熟悉的任务,则不要轻信您的中方伙伴。 不得已时,尽可能采取他人的经验。绝不可以重蹈覆辙。别相信以自己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畅行无阻的范例和实践经验在中国也自然行得通。 不仅要分析今后面临的项目的商务前提,还要分析跨文化条件、人力资源和管理素质情况如何?记住:许多在华的合作项目,败于文化交流的困难,而非败于产品、成本或价格。 别忘记:企业存在一天,可行性研究便是、且一直是圣经。在此,哪怕犯下一丁点错误,日后也会为之付出昂贵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