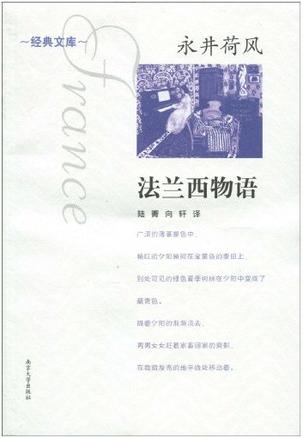船和事 从纽约起航的大概一个星期后,船终于在晚上10点半左右停靠在勒阿弗尔港。 那天,我与其它乘客一同晚餐后,8点半左右登上了甲板,在日暮黄昏水平线处可以眺望到如繁星般闪烁灯光。那里就是著名的勒阿弗尔港。 海在晴空下异乎寻常地平静。虽说马上就要接近陆地,又是七月底的天气,但这里与受雨雾影响而降温的大西洋洋面上没有两样。我还没有脱下航空中一直穿着的那件薄外套。 遥望辽阔的海洋彼岸,三桅渔船来来往往,无数的海鸟在渐渐黯淡的黄昏光影中如落叶一般飞舞。远处的洋面上,到处可见汽船的缕缕黑烟拖曳着长长的尾巴--在越来越靠近大陆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海水也柔和多了。 随着愉快心情的与时俱增,那远远的灯光也在夜色渐暗的同时逐渐增多了起来,可以清晰分辩出哪盏灯是灯塔,哪些灯是街灯。近勒阿弗尔市附近山脚的街市灯光一直散布到高处,时而从高山上明亮地放射出海面探照灯的刺目灯光。 我想起了作家莫泊桑小说--《热情》(La passion)、《我的叔叔于勒》(Mon oncle Jules)以及《皮埃尔与让》(Pierre et Jean)等等小说中描写的港口景象。我对照着大作家的笔下文字,关注地举目四望面前的风景。 很可惜!可能因为是夜色太浓,我遗憾地没有看到自己梦想中的任何景色。船很快就驶近了海岸。海岸一带是坚固的石堤,石堤的上方好像是宽阔的街道,街道两旁路灯规则地排列着。夜色中远远望去,路灯映照下的海边人家简直就像是舞台上的布景。长久以来,我看惯了没有屋檐、方方正正的高楼大厦,法兰西住房自然、精美、小巧,看上去就像一幅画。 船一边减速,一边拉响了两三响汽笛。汽笛声悠长地在街道和山脚附近回荡。可以听到海边上人们的说话声,接着舞曲音乐也随着浪涛传了过来。海边的大道上,有前来纳凉散步的男女,餐厅窗口透出美丽的灯光……这下,全都可以看清楚了。在一家凸建在水面上的显眼的大房子里,眩目的电灯光下,很多人在跳着舞。 “装潢得很漂亮的那家是赌场。”站在我身旁的一个男人自言自语道。 石堤下,停靠着几艘小型蒸汽船,稍远处还停泊有大型汽船。我以为自己乘坐的船也会在此下碇,可是船沿着石堤静静地滑行着。甲板上有些人挥动着手帕叫喊着,在岸上玩耍的男女孩童们也大声地呼喊着,跟着船奔跑起来。船看上去很慢,但实际还是行得很快,不知不觉中沿着海岸驶到了郊外。住家渐渐稀落,岸上耸立着几座石砌的仓库,那里的码头边停靠着两三艘和我们的船差不多的汽船。很快,船驶入标有大西洋运输公司名称的船坞。在船要停未停的时候,水手已经奋勇地叫喊着放下了船梯。船梯正对着列车的站台。从甲板上可以看到站牌上写着的字: TRAIN SPECIAL POUR PARIS H 7 55,A.M 站牌上写着前往巴黎的列车早上七点五十五分发车。甲板上有许多人抱怨着,但没有办法。不论是待在船上,还是去宾馆,反正都得等到天亮。 次日。天还没有亮,汽船的周围停满了小商贩的船。 “要葡萄酒吗?”“要啤酒吗?”到处可闻男女的叫卖声。 我早做好了登岸的准备,喝了咖啡后,走上了甲板。天气还像昨晚一样凉。法兰西原来是这么一个寒冷的国度!我感到微微吃惊。天空阴沉着,好像夜里下过小雨,近处的地面上还有些湿。我现在很想看一下晨光下的街道以及塞纳河入海口的景色,但从甲板上望出去,视线都被仓库及铁道边的建筑挡住了。只能看到远处郁郁葱葱的的高岗上稀稀拉拉建着人家。 因为火车站直接连着码头,上车也没有人管。我提着手提箱,走过宽敞的候车室。候车室的墙上单一清丽的草绿色彩吸引了我,这与涂金抹银的美国品味有着天大的区别。同时,以浅色调描绘着瑞士和南欧各地风景的铁路公司的广告,也让我停下了脚步。……我再一次深深地意识到,我踏上了欧洲的土地。 汽笛声响起,列车启动了。 读过左拉作品的人也许都知道,因描写杀人狂凶残心理而出名的《人面兽心》(La B te Humaine)是以勒阿弗尔和巴黎之间的铁道为舞台的。左拉笔下的荒凉寂寞,而又充满杀气的各色风景都取材于这条铁路沿线。于是,我比昨天进入港口时更加用心地望着窗外,甚至从窗口把头探了出去。但在急行列车从鲁昂到巴黎不到4个小时的路途中,几乎没有一处像是小说中的风景,只不过是过了五、六个稍显冗长的隧道。在看惯了北美大陆广漠无垠的荒野景色的我眼中,途经的诺曼底原野风景,简直美得像一幅画,由于收拾得过于整齐,让人感觉到那好像根本不是天然的景色。 在广阔的金黄色成熟的麦浪中,开辟了出了一条迂回曲折的小道。已经收割了的田地里像血滴一样盛开着艳红的虞美人花。漫山遍野都种植着蔬菜田的小山丘陵,色彩分明,连绵起伏。行驶着如山般堆积着枯草的双驾马车的道路旁,直立的白杨树不规则地排列着;在小池塘边牛打着盹,夏日的树木茂盛翠郁。这种构图、这种色彩,像自己多年前曾欣赏过的一幅油画,似乎这自然风景只是为美术创作而打造的。也正因为这样,大自然的美一旦达到了极点,就进入了经典的范畴,不是个人想象所能够达到的。 列车渐近巴黎。鼠灰色的积雨云全都向西边移动。可以看到夏日的天空,但这天空色彩是美国的晴天都看不到的蔚蓝。在这样的天空色彩和日光普照的映染下,原野景色变得更加地清澄。每每看到绿色树荫下红瓦屋顶和灰色墙体的住家时,我都会不由地羡慕:啊!这个国家的人们住在这么美丽的乐园里是多么幸运呀! 远处的天边,夏日浮动的白云中间,艾菲尔铁塔映入眼帘。车窗下的一条清清的小河在静静地流淌着,河岸边是枝叶繁茂的树林,枝叶沉甸甸地垂在水面上。水边有人在钓鱼,小鸟在鸣叫,流水被成堆如浮萍的树叶形成的小岛分开又合在一起。我从贴在列车上的地图得知,这大概就是赛纳河。 列车马上就要到巴黎的圣雷札火车站了。一路上,郊区的树林间有不少别墅小屋,这大概是有钱人的住宅吧!这些小屋从阳台到窗户都构型简洁,整齐的花园设计中有不少独具匠心的地方,很具专业水准。看到在别墅窗口和花园里望着列车的女人,让我联想起法国戏剧以及小说中出现的许多女主人公。 到了巴黎圣雷札火车站。这一带是巴黎比较繁华的地段,小偷扒手多得惊人。在船上,就有法国人提醒过我,手表、钱包等重要的东西一件也不能放在外衣的口袋里,一走上月台,我就提高了警惕。虽然这里也一样人马喧杂,但与美国纽约中央车站的喧闹完全不同,人们的行动十分缓慢,没有了美国人瞧人时那种严峻的目光。也见不到毫无表情地突然从后面冲到前面去的男人。在月台上行走的旅客中,大概我是唯一没有人来迎接和导游,独自鼓足勇气走进巴黎这个大都会的男人。 火车站附近站着两三个穿着制服的宾馆服务员,一边喊着:“先生!先生!”一边忙着递送着名片。我直接穿过车站前的广场,朝着电车、马车、人力车混杂的大街走去。盘算着,也许会在这条街上找到一个价钱便宜的客栈。 在以法国《世界日报》而闻名的大街拐角处,我看到了一家小客栈。在这里,回首可清晰地望见火车站的灰色大楼。小客栈的入口处写着大字 “PRIX MOD?R?S(便宜)”。这对囊中羞涩的旅客来说极具诱惑力。 “你好!先生。”一走进客栈,旁边一间房里的女主人迎了出来。女主人头发花白,身子胖得像一个酒坛,和身体一样肥胖的脸,像熟透了的苹果一样,血色很好。下巴上有一颗黑痣,黑痣上长得了几根长毛。她的样子像极了杂志和报纸插图上常见到能干的巴黎女主妇。“您从哪里来?累了吧!”她说了一些客套话,叫来了一个跛脚男仆为我提行李。我登上了旋转扶梯,来到三楼的一间客房。 我在巴黎只停留两天。为了生计,我受雇于银行,所以必须尽快赶往南部城市里昂。虽然以后我仍会有机会再游巴黎,但周围能去的地方依然不想错过。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女主人,于是她为我包了一辆一日游马车,让我周游一下市内的风光。 啊!这就是巴黎!我震惊了。我不光去了闻名世界的协和广场、行道树成荫的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布涝涅森林,还见识了里沃利路的热闹非凡、意大利亚街的纷沓杂乱。我走过了赛纳河岸,甚至走访了不知名的细小街道。所到之地的所见所闻,都会让我想起曾经读过的法国写实派作家的小说、帕尔纳斯流派的诗篇,这些作品都精确、忠实地反映了这个大都市的生活。 我是在法国艺术中第一次了解法兰西的都市田园的。坐在马车上,我不由地想起远方的故乡以及它的艺术。明治时代的写实派作家们是否很精确地研究过东京?也许即将形成的自然派和象征派作家会比明治写实派更加进步成熟吧! 短短两天的观光后,我将在黄昏时离开巴黎前往里昂。我在附近的咖啡店里进了晚餐,再回到客栈结了帐。胖胖的女主人在马车到来之前,把我招呼到帐台旁的长椅子上坐下。她详细地给我讲了列车和火车站的有关情况,还教了我买票的方法,并告诫我,这里的假钱很多,要处处小心。在马车到来后,她一时兴起,从壁炉上的花瓶里取出一支白玫瑰递给我,并祝我旅途愉快、一路平安。 这支像牡丹花一样大的法国白玫瑰,使我不由地十分感动。在这偌大的巴黎,在这偌大的法兰西,我只认识这么一位女主人。但今晚我就要离开这座城市,这是我们相处的最后一刻。也许过一段时间后,我们俩都会彼此相忘,女主人上了年纪也许会悄悄地离开人世,我呢,或许会在哪个国家中生病倒下。……也许没有人会知晓这世上有一个与历史毫无关联的我,也不会知道女主人送给我的白玫瑰,时光会一如既往地向前行进。…… 从巴黎去里昂。在火车站乘坐上前往开往马赛的快速列车。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看着列车徐徐离开巴黎郊外。广漠的薄暮景色中,艳红的夕阳映照在金黄色的麦田上,到处可见的绿色夏季树林在夕阳中变成了藏青色。随着夕阳的渐渐淡去,男男女女赶着家畜回家的剪影,在微微发亮的地平线处移动着。望着这明亮而静静的法兰西平原的夕阳,我不由地得回想起自然派作家朱尔·布雷顿的一首诗: “Voici I’ombre qui tombe, et l’ardente fournaise S’ teint tout doucement dans les flots de la nuit, Au Rideau sourd du bois attachant une braise Comme un spr me adieu.Tout se voile et s’apaise, Tout deviant ideal,forme,couleur et bruit, Et la lumi re avare aux details se refuse; Le dessin s’ennoblit, et dans le brun puissant, Majestueusement le grand accent s’accuse; La teinte est plus suave en sa gamme diffuse, Et la sourdine rend le son plus ravissant. Miracla d’un instant, heure immat ridlle, Ou l’air est un parfum et le vent un soupir! Au crepuscule mu la laideur meme est belle, Car le myst re est l’srt:l clat ni l’ teincelle Ne valent un rayon tout pr t s’assoupir. (黑影现在就已来临/涌动如潮的夜/淹没了燃烧的晚霞/森林无声的深处/如余声袅绕/那是最后的谢幕/万象将归于宁静/声色形影 一切都趋于理想/细微 在薄暗中高大/伟岸的投影 伴着雄壮的色调/色彩 趣味横生/轻弹之乐 格外迷人/这是瞬间的奇迹/梦幻的一刻/在这里 空气芳香/风儿轻叹/神秘就是艺术/日近黄昏/丑陋化为美丽/辉煌夺目即将消逝/只因消逝而动人心弦。)” 一点红得像玛瑙一样的星辰在闪动,那是路傍住家的灯光映在河水里的反光。我望着夜色在无边无垠的麦田里越来越深浓。离开巴黎后,只停靠了几个小村的火车站,还没有经过一个像样的城市。列车一直如风地行驶在平坦的麦田间、繁茂的树林里、修然的小河流水旁,这一切好像永无尽头。但这些与单调漠然的北美大陆中部平原截然不同。堪萨斯州的田野、密苏里州和伊利诺伊州的玉米田,同样是平静的原野,不知为什么总给人带来荒凉无人的感觉,让人升起一种悲伤的情绪。换句话说,那里有一种雄性的悲愁。而眼前的风光却相反。无论何处都带着一种女性的温柔。夜雾中的沉默的森林,不但不会让人感到寂寞,还会使人倍感温暖和平静。这原野和流水给我一种温柔的抚慰。如果把美国的大自然比做严父之爱的话,那法兰西的大自然景色就是博大的母爱。不!更确切地说,一种带着情人眷恋的温情。 这秀丽优美的风景,在夜空升起的半月映照下,显得分外宜人。在离开故乡的四年飘泊之中,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像现在这样美丽的景色。打开车窗,我在迎面扑来的枯草芬芳中沉醉。由于远渡大西洋的车马劳顿,我渐渐陷入了半梦半醒的昏沉中,一会儿睁开眼睛,一会儿又阖上。每次睁开眼,我都要眺望一下窗外清澈的月亮,深夜的天空。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中的景致,连我自己都分辨不清了。 大约过了十二点,列车进了站,列车长报着站名,车窗外有几个女人在询问去瑞士湖畔乘什么车。我感到很不可思议。这深更半夜的,几个年青女子居然要越过法国,到瑞士湖畔去。这几个女子要不是天上下凡的仙女吧?我心怀憧憬地想着,目送着这几个女子向反方向走去。列车停了不到五分钟,马上又出发了。 我感到很疲倦,一直坐在铺着天鹅绒的椅子有些腰酸背痛,眼皮也越来越沉重起来。不知不觉中,我进入了梦乡。但是我还是不舍得这难得的月光,睡着睡着,就会不由自主地睁开眼睛。这时我发现窗外的景色有了变化。窗外是一片平坦的平原,繁茂的树林渐渐地变得稀疏起来,没有人家,与列车平行的笔直宽阔的大道旁,种着法兰西特有的高矗挺拔的白杨,都是差不多一样的高度,数以百计地排列着,忽然间,四周像降下白色帷幕般地起雾了,景色被浓雾遮挡住了。从雾幕的缝隙中,我隐约可见铺满细砂的白色沙滩,地面低得吓人,我猜那里有可能是一片很大的湖。我定睛想看看流动的湖水,但月光把地面映成一片青蓝,叆叇的雾色又太过苍白,在我疲惫的双眼中这就像是一场梦。列车的墙上挂着地图,但要站起来看一下,对现在的我来说,是很艰难的。得看一下!得看一下!我一直着急地想努力做到,一边却又不听使唤地睡着了。 突然列车经过一座铁桥,过桥的隆隆响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向外一看,岸边高高的石堤上鳞次栉比地排列着白墙人家。不知是灯光,还是月光,四周显得异常明亮。 马上要到里昂市了。我慌忙捡起了掉在地上的帽子戴上,拍了一下衣服上的尘土,走下了列车。火车站的大钟显示着已经是凌晨三点半,夏季的天空星星正在渐渐消失,月亮也西沉了下去,已经快要天亮了。 乘上马车,经过宁静沉睡的大街。我住进了河岸边的一家宾馆,睡觉之前,我还想要欣赏一下这欧洲的黎明。打开阳台的窗户,小鸟的鸣啭从四周传来,……在都市的黎明前听到鸟叫,这对我这个从纽约而来的旅人来说实在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 天亮后醒来马上就想起巴黎客栈的女主人送给我的那支白玫瑰。它被我插在列车的窗上,由于下车时十分慌忙,竟然把它忘得一干二净。现在,那支已经到达马赛的花是依旧吐露着芬芳,还是被上下车的人踩在脚下变得惨不忍睹了呢? 明治四十年七月于里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