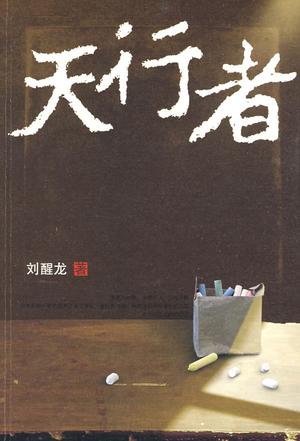母亲生气了:“天上雷公,地下母舅,你敢骂谁?” 张英才说:“谁让你生了我这个没出息的儿子,读书不行,骂人的水平比天还高,不信你就等着听。” 果然,挑水回来时张英才又骂了一声。 母亲上来轻轻打了他一耳光,自己却先哭了起来,嘴里说:“等你爸回来了,让他收拾你。” 张英才因此没吃晚饭,父亲回来时他已睡了。躺在床上听见父亲在问为什么,母亲没有说出真相,还替他打掩护,说是突然有些头疼,躺着休息一会儿。 “是读书读懒了身子。”父亲说着气就来了,“十七八的男人,屁用也没有,去年高考只差三分,复读一年倒蚀了本,今年反而差四分。” 张英才蒙上被子不听,还用手指塞住耳朵。后来母亲进房来,放了一碗鸡蛋在他床前,小声说:“不管怎样,饭还是要吃的,跟别人过不去还可以,跟自己过不去那就太划不来了。”又说:“你也真是的,读了一年也不见长进,哪怕是只差两分,在你爸面前也好交代一些。” 闷了一会儿,张英才出了一身汗。见母亲走了,他连忙撩开被子,下了床,闩上门,趴到桌子上给一位叫姚燕的女同学写信,他写道:我正在看高二上学期你在班上推荐的那本《小城里的年轻人》,其中那篇《第九个售货亭》写得最好,很多情节就像是发生在我们学校里,那个叫玉洁的姑娘最像你,你和她的心灵一样美。 一张纸才写到一半,张英才就觉得无话可说了,想了好久,才继续写道:我舅舅在乡教育站当站长,他帮忙找了一份很适合我个性的工作,过两天就去报到上班,这个单位人才很多。至于是什么单位,现在不告诉你,等上班后再写信给你,管保你见了信封上的地址一定会大吃一惊。 写完后,他读了一遍,不觉一阵脸发烧,提笔准备将后面这段假话划掉,犹豫半天,还是留下了。回转身他去吃鸡蛋,一边吃一边对自己说:“越是漂亮的女孩子越爱听假话。”鸡蛋吃到一半,张英才想起自己口袋里那枚帮自己做决定和预测未来的硬币了,要寄信,还得向父母伸手要钱。他勉强吃了两口,便推开饭碗,倒在床上,盯着屋顶上的亮瓦发呆。 张英才醒来才知道,自己睡了一夜,连蚊帐都没放下,身上到处是红疹子。他坐起来看到昨夜吃剩下的半碗鸡蛋,觉得肚子饿极了,想起学校报栏上的卫生小知识说过,隔夜的鸡蛋不能吃,就将已挨着碗边的手缩回来。这时,母亲在外面敲门。他懒得去开门,门闩很松,推几次就能推开。 推几下,房门真的开了。母亲进来低声对他说:“舅舅来了,你态度可要放好点,别像待你老子那样。” 母亲扫了几眼那半碗鸡蛋和张英才,叹口气,端起碗三下两下地吃光了。张英才穿好衣服走到堂屋,本想冲着父亲对面的男人客客气气地叫声舅舅,也不晓得哪根筋长反了,事到临头却冒出一句:“万站长,你好忙呀!”听起来有点故意寒碜的意思。 万站长说:“英才,我是专门为你的事来的。” 父亲说:“蠢货!还不快谢谢。” 万站长说:“我给你弄了一个代课的名额。这学期全乡只有两个空额,想代课的有几十个,所以拖到昨天才落实。你抓紧收拾一下,吃了早饭我送你去界岭小学报到。” 张英才耳朵一竖:“界岭小学?” 母亲也不相信:“全乡那么多学校,为什么要去那个大山窝里?” 万站长说:“正因为大家都不愿去,所以才缺老师,才需要代课的。” 父亲说:“不是还有一个名额么?” 万站长愣了愣:“乡中心小学有个空缺,站里研究后,给了细张家寨的蓝飞。” 母亲见父亲脸色变了,忙抢着说:“人家蓝小梅守寡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照顾照顾也是应该的。” 父亲掉过脸冲着母亲说:“那你就拿一瓶甲胺磷给我喝了,看谁来同情你?” 万站长不高兴了:“是不是有肉吃了就挑肥拣瘦?不干就说个话,我好安排别人,免得影响全乡的教育事业。” 父亲马上软了:“当宰相的还想当皇帝呢,是人哪个不想好上加好呢,我们只是说说而已。” 母亲抓住机会说:“英才,还不赶快收拾东西去!” 一直没做声的张英才冲着母亲说:“收拾个屁!也只有你哥哥想得出来,让你儿子去界岭当民办教师。” 父亲当即去房里拎出一担粪桶,摆在堂屋里,要张英才随粪车到县城去拉粪。张英才瞅着粪桶不做声。 万站长挪了挪椅子,让粪桶离自己远点:“你没有城镇户口,刚毕业就能找到代课机会,说好听点是你有运气,说势利点是因为有个当教育站长的亲舅舅。你不吃点苦,我怎么有理由在上面继续帮忙说话呢?” 父亲在一边催促:“不愿教书算了,免得老子在家没帮手。” 张英才抬起头来说:“爸,你放文明点好吗?舅舅是客人又是领导干部,你敢不敢将粪桶放在村长的座位前面?” 父亲愣了愣,将粪桶提了回去。 母亲去帮张英才收拾行李,堂屋里只剩下舅甥二人。张英才也挪了一下椅子,和万站长离得更近些,贴着耳朵说:“我晓得,你昨天先去了细张家寨。”停一停,他接着说:“假如我去了那上不巴天、下不接地的地方,你被人撤了职那我怎么办?” 万站长回过神来:“大外甥,你不要瞎猜。我都下了几十年象棋,晓得卒子是要往前拱。你先去了再说。我在那儿待了好几年才转为公办教师,那地方是个培养人才的好去处,我一转正就当上了教育站长。还有一件事,那地方群众对老师的感情不一般,别的不说,只要身上沾着粉笔灰的气味,再凶恶的狗,也不会咬你。” 万站长从怀里掏出一副近视眼镜,要张英才戴上。张英才很奇怪,自己又不是近视眼,戴副眼镜不是自找麻烦么。万站长解释半天,他才明白,舅舅是拿他的所谓高度近视做理由,才让他出来代课的。 万站长说:“什么事想办成都得有个理由,没有理由的事,再过硬的关系也难办,理由小不怕,只要能成立就行。” 张英才戴上眼镜后什么也看不清,而且头昏得很,他要取下,万站长不让,说本来准备早几天送来让他戴上适应适应,却耽搁了,所以现在得分秒必争。还说,界岭小学没人戴眼镜,他戴了眼镜去,他们会看重他一些,另外,他戴上眼镜显得老成多了。 张英才站起来走了几步,连叫:“不行!不行!” 父母亲不知道情由,从房里钻出来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叫不行!”父亲还骂他:“你是骆驼托生的,生就个受罪的八字。” “你除了八字以外什么也不懂。”张英才用手摸摸眼镜,说完便钻进房里,片刻后又夹着那本小说出来,对万站长说:“我们走吧!” 张英才心里一默算,就发现有问题,想细问,又怕不便。回校后就给万站长写了一封信,要他查一查为什么这里只有四个民办教师,却能领五个人的补助金。 两封信都交给了父亲。张英才再三嘱咐,要父亲将姚燕的信用挂号寄。他怕父亲弄错,特地说邮费涨了价,挂号要五角钱。父亲要他给钱。 他有点气,说:“父子之间,你把账算得这么清楚干什么,将来有我给钱你用的时候。” 父亲品出这话的味道:“这才叫水往下流呢!” 父亲走时,张英才正在上课。听见父亲在外面叫一声:“我走了!”他走到教室门口挥挥手就转回来。 下课后,孙四海过来对张英才说:“你爸让我转告,他将那瓶油送给余校长了。他怕你生气,不敢直接和你说。他说中午在余校长家吃饭,一大盆青菜里,挽起胳膊找半天,才能找到几个油星子。” 这天特别热闹,放学后,降旗仪式刚结束,呼呼啦啦地来了一大群家长。也不喝茶,十几个人分成两拨,一拨人帮孙四海挖茯苓地四周的排水沟,一拨人帮余校长挖红芋。 张英才到窖茯苓的地里转了转。大家都在议论,说孙四海的茯苓丰收了,地上裂了好些半寸宽的缝,一定是底下的茯苓太大,涨开的。孙四海笑眯眯地说,头三年自己种的茯苓都跑了香,这一次就当是对上一次的补偿吧。张英才不明白什么是跑了香。孙四海告诉他,茯苓这东西怪得很,三年前在这儿下的香木菌种,三年后挖开一看,香木倒是烂得很好,一个茯苓也找不到,而离得很远的地方,会无缘无故地长出一窖茯苓来,这是因为香跑到那儿去了,有时候,香会翻过山头,跑到山背后去的。张英才不信,认为这是迷信。大家立即对他不满,埋头挖沟不再说话。 张英才觉得没趣,便走到余校长的红芋地里。几个大人在前面挥锄猛挖,十几个小学生跟在身后,见到锄头翻出红芋来,就围上去抢,然后送到地边的箩筐里。红芋的确没种好,又挖早了,最大的也大不过拳头。余校长说,反正长不大了,早点挖还可以多种一季白菜。张英才看见小学生翘着屁股趴在那里折腾,开始心里直发笑,后来见到他们脸上黏着鼻涕和泥土,头发上尽是枯死的红芋叶,想到余校长将要像洗红芋一样把他们一个个洗干净,就喊道:“同学们别闹,要注意卫生,注意安全。” 余校长不依他,反而说:“让他们闹去,难得这么快活,泥巴人儿更可爱。” 余校长用手将红芋一拧,上面沾的大部分泥土就掉了,送到嘴边一口咬掉半截,直说鲜甜嫩腻,还叫张英才也来一个。张英才拿了一个要去溪边洗,余校长说:“不用洗,洗了不鲜,有白水气味。”他装作没听见,依然去了溪边。将红芋洗干净后,他不好再回去,只有回屋烧火做饭。 走到操场中间,听见有学生叫张老师,一看是叶碧秋。 “你怎么没回家?” “我小姨就住在下面村里,我爸让我上她家去,为张老师要点青菜炒着吃。”说着,就将半篮子青菜递到他面前。 张英才生气了:“我是一个人吃全家人不饿,不像余校长,要管二十个人的伙食,怎么会要你去帮我讨吃的呢?” 叶碧秋嘟哝着说了句什么,脸上很不高兴。 张英才换个口气说:“这次就算了,以后就别再自作聪明了。”叶碧秋忙放下菜篮,转身欲走。张英才拉着她的手说:“你帮我一个忙,问问余志,他知不知道是谁弄断了凤凰琴的琴弦。” 见叶碧秋点了头,张英才就送她回小姨家。 进村后才弄清楚,叶碧秋的小姨就住在邓有米的隔壁。 邓有米见到后,又要留张英才吃晚饭,张英才只好谎称已吃过饭。往回走时,张英才记起叶碧秋刚才走路时款款的样子,很像那个给他写信的女同学姚燕。他不由得有些担心,父亲会不会将给姚燕的信弄丢。随后又想,可惜叶碧秋比姚燕小许多。如此想来想去,他仿佛记起来,刚才拉住叶碧秋,要她找余志探听是谁弄断了凤凰琴的琴弦时,那只暖暖的小手,在自己的掌心里柔柔地抖了几下。 天气一天比一天凉。 一个星期下来,学校里的日常事务就熟悉了。每日几件旧事,做起来寂寞得很。凤凰琴断弦一事,便成了真正的大事件。等了几个星期,叶碧秋不仅没来汇报情况,反而老躲着他,一放学就往家里跑。这天下午,张英才让邓有米一上课就宣布,放学之后,让叶碧秋到办公室见他。 放学时,叶碧秋果然不敢抢着跑了。 张英才问:“你问过余志没有?” 叶碧秋说:“问过,他说是他干的,还要我来告诉你。” 张英才说:“那你怎么迟迟不说?” 叶碧秋说:“他晓得我是你派来的汉奸特务。我要是说了,就真的成了汉奸特务。” 张英才说:“那你为什么还要说?” 叶碧秋说:“是你要我说,不是我要说的——二者完全不一样!” 张英才被叶碧秋后面的话说愣了。这是他来界岭小学后,所听到的最有文明含量的一句话。当然,他所感受的文明,多半来自每天都要翻开来看一看的《小城里的年轻人》。他很想问叶碧秋看过这本小说没有,或者问她想不想看这本小说。 张英才回过神来:“我不相信是余志干的。” 叶碧秋说:“我也不相信,余志尽冒充英雄。” 张英才说:“那你再去问问他。” 叶碧秋说:“我不敢再问了。三年级时,他说他吃了蚯蚓,我刚说不信,他就当面捉了一条蚯蚓吃下去。” 眼看谈不妥,张英才只好让叶碧秋走了。 “我们研究过了,大家一致决定,下一次再研究这事。” 张英才气得直擂床板,用牙齿将枕巾咬成团,塞在嘴里狠命嚼,才没有跳到操场上破口大骂。 学校一如既往,不安排张英才的课。哪怕是请了学生家长来帮忙挖茯苓,孙四海不时要跑去张罗,也不让张英才替一下。茯苓挖到第二天中午,山上一片喧哗。张英才以为出事了,心里有些幸灾乐祸。 没过多久,孙四海兴冲冲地从山上下来,手里捧着一个灰不溜秋的东西,嘴里叫着:“稀奇,真稀奇,茯苓长成人形了!” 张英才忍不住也凑拢去看,果然,一只大茯苓,长得有头有脑,有手有脚,极像一个小娃娃。余校长从孙四海手里接过茯苓人。细看一遍后,遗憾地说:“可惜挖早了点,还没有长成大人,要是长得分清男女,就值大价钱了,说不定还能成为国宝。” 孙四海愣了一阵,才回过神来,双手一用力,将茯苓人的头手脚一一掰下来,扔到张英才的脚下。张英才见孙四海的眼里冒着火,不敢吱声,扭头回屋,将自己反锁起来。 张英才想了好久,觉得老这么斗也不是事,回避一阵也许能使事情有所转化。他向余校长交了一张请假条。余校长立即签了字,还说一个星期若不够,延长一两个星期都行。张英才拎上一只包,装上牙刷毛巾和给姚燕的信外加那本小说,就下山了。 下山后,他没有回家,直接去乡里见万站长。 舅妈李芳站在门口说,万站长到外地参观去了。 李芳的样子明显是不想让他进屋。张英才只好在心里骂:你这个母夜叉,难怪丈夫会在外面偷情!嘴里依然道了谢。 出了教育站,看见从县城开来的末班客车停在公路边上。车上人不多,有不少空位,他摸摸口袋里的钱,打定主意,干脆上一趟县城,他想到县文化馆看看,如果运气好,碰上那位写了如此好的小说的干部,就将心里的话全部说给他听听。张英才一上车,车就开了,走了两个小时,在县城边,他叫了停车。张英才记得姚燕家在城郊,父母是种菜的。上高二时,学校开运动会,张英才参加万米长跑,曾经从姚燕家门前跑过。张英才记得具体方位,一路找过去,还真让他找到了。大门上着锁,听邻居说,姚燕的父母上省城看姑娘去了。张英才本没有见姚燕家人的意思,只想认路朝拜一下。转身再到县文化馆,一打听,这才真正失望:那位写小说的干部,已经作为人才,调到省文化厅去了。 张英才的第三个愿望是看电影。他发现电影院居然不清场,看了上一场,只要不出去,就能接着看下一场,虽然是同一部电影,张英才还是一口气看了三遍,直到电影院关门为止。 从电影院出来,张英才去了那家农友旅社。过去父亲来学校看他时总住那儿,同学们还用此事笑话他。他和父亲说了几次,父亲不肯改,仍住农友旅社。张英才不去想为什么自己也只能住农友旅社,找到地方,交了两元钱,登记了一个床铺,也不去看看,拿了号码牌,出门买了一碗清汤面,三下两下吃完,回到旅社,蒙头就睡。 后半夜,那些要赶早去集贸市场上抢占位置的人,早早地就将张英才闹醒了。他跟着那些人起来,去车站搭车,到了候车室,才发现自己也起得太早了点。候车室里只有几个要饭的躺在那儿,他在那里坐下也不是,站着也不对。 幸好候车室的报栏上还夹着一张旧报纸,张英才站过去,从头开始看,连最小的标点符号也要看清楚是顿号还是逗号。看到第二版,突然发现一篇通讯员文章,是说这次贯彻义务教育法工作大检查的,从头到尾全是好话,居然还点名表扬了万站长,自他任教育站长以来,西河乡义务教育工作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英才将这张报纸看完之后,又集中注意力来研究这篇文章。连着看了好几遍,脑子里的思索次数就更多了。 随着有人将要饭的人撵出候车室,车站里慢慢热闹起来了。 好不容易回到西河乡,没想到刚下车就遇上蓝飞。张英才夜里没睡好,有些恍惚,想躲开已经来不及。更想不到蓝飞会主动迎上来,问他何时回去上课。 张英才一时大意,脱口说了句:“上个鬼的课!” 再听蓝飞说出来的话,张英才忽然明白,自己的事已被大风从山上刮到山下来了。 蓝飞说:“鬼才不上课!你是教育站用红头文件批准的教师,不说为万站长争口气,也要为自己留点尊严!” 蓝飞胸有成竹地为张英才出主意,要他回去后,装出一副准备进行转正考试的样子。蓝飞断言,不出三天,那几个民办教师就会想尽办法来巴结他。到了那一步,他就是界岭小学的阿弥陀佛了。 蓝飞说完自己的想法后,不清楚是叹息别人,还是叹息自己,或者只是发泄心中郁闷,他将嘴张得大大的,对着太阳长长地吁了一下。一直侧面对着别处的张英才,情不自禁地随着他的表情看过去,刚刚还是?里无云的天空,仿佛也被触动了伤心事,变得阴阴的。他俩都没有将心里想到的话说出口,似他们这类只是民办教师初级阶段的人尚且如此,界岭小学的那帮民办教师,少的干了十几年,多的干了二十几年,日日夜夜对转正的渴望,早已化为一种心情之癌,成了永远的不治之症。 张英才在心里接受了蓝飞的主意后,回家吃了顿中饭,又让母亲准备几样可以存放的菜,便赶回学校。路过细张家寨时,张英才看到万站长的自行车放在一户人家的门口。不用猜他也明白,那一定是蓝小梅的家。过了细张家寨,便全是上坡路。脚步一慢,就有时间想事情了,特别是遇上一阵大风,吹得身上凉透了,他才恍然大悟:蓝飞也是高中刚毕业,凭他的心智,就算将那些从学校图书室偷出来的厚黑与权谋方面的书背得滚瓜烂熟,也难以在这么短时间里,将民办教师心理摸得如此透彻,所以,一定有高人在背后指点。 张英才冲着滚滚袭来的林涛大吼一声,心里却在暗暗叫苦:若是在万站长心里,亲外甥连老情人的儿子都不如,这符合天理吗?这时候,他已经认定,蓝飞的突然出现,一定是奉了万站长的旨意。他忍不住骂万站长是老狐狸,又骂蓝飞的母亲蓝小梅是老狐狸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