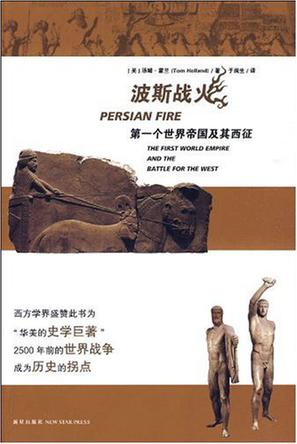早在波斯人刚刚开始崛起的时候,那时居鲁士还在吕底亚,他曾意外地接见了一个来自爱琴海彼岸的代表团。这些使节是希腊人,但同亚洲部分的希腊人有很大的差异,他们的城邦繁荣诱人。当时居鲁士曾经密谋征讨并占领它们。这些陌生人蓄着长发;身披耀眼的猩红大氅;他们说话的方式不像一般使节们所用的那种精细而得体的口吻,而是非常粗俗、坦率且无礼。他们向这位世上最伟大的君主传达的口信非常简单:居鲁士最好不要侵犯那些伊奥尼亚城邦,否则他就要应付那些派这些使节来的人--斯巴达人。显然这些陌生人觉得这个少见的名字足够让人胆寒,所以它们没有补充任何说明。居鲁士转身命令召集身边的伊奥尼亚随从,他疑惑不解地问道:"告诉我,斯巴达人是谁?"1 这个问题对每个希腊人来说都会让他目瞪口呆难以回答。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亚洲人竟然不知道斯巴达人?没有别的东西能比忽视历史上最有名的女人更能说明波斯人的孤陋寡闻了。斯巴达的海伦曾经在几百年前毁灭了亚细亚和整个希腊。由于她被从她的丈夫斯巴达王美涅拉欧司(Menelaus)家族中诱拐到传说中的特洛伊城,让整个世界陷入血光之灾。在长达十年的时间中,来自东西方的许多英雄在特洛伊平原的尘土中互相厮杀。希腊人认为只有彻底消灭这座亚细亚最大的城邦,屠尽他们的男子,掳掠他们的妇女,才可能最后终结这场可怕的战争。在这些胜利者的后裔看来,在这次彻底的破坏中最令人冷静和惧怕的是:仅仅"为了一个斯巴达女人就纠集起一支巨大的远征军,侵略亚细亚并彻底消灭特洛伊的势力。"2无疑很多希腊人,尤其是那些居住在亚洲边缘地区者,想象着辽阔的东方仍然因为这怨气而闷闷不乐,反复思考着古代的过节。由于依附在辽阔大陆的边缘所处的不安定状态,伊奥尼亚人非常有理由害怕特洛伊死难者报仇的预兆。 对于斯巴达人来说,关于这座城邦的著名女儿的记忆实在过于珍贵。据说美涅拉欧司王在大屠杀之后的特洛伊城中寻找他的妻子,本打算将她也杀死以惩罚她所造成的这一切杀戮的罪过--但是,当他最终找到自己的妻子时,非但没有杀掉她,反而让宝剑从手中脱落--因为当他看见这女子裸露着的完美胸部时,顿时哑口无言,张开双臂将她紧紧拥入怀中。他们两人一同返回了斯巴达,他们的坟墓就建在城南的地岬上,人们可见那巨大的封石颜色一如美涅拉欧司王的头发一样火红。海伦本人堪称"女性的光辉"3,比她的丈夫更加耀眼:不仅因为她金发碧眼,而且她拥有佩带金饰的窈窕身姿。居鲁士在得知斯巴达人就是一群在这样一个女人的神龛中举行祭祀的人,是这样一群好色且沉溺于欢愉之徒之后,他对这群人可笑的傲慢态度更增添了几分轻蔑。他们的使节蓄着长发,身披猩红大氅显然具有海伦信徒的倾向;因为居鲁士常常有机会知道在希腊人之中,蓄长发通常被看作女子气质的某种证据,而使用昂贵的银朱染料则标志着极度的奢侈。波斯人轻视斯巴达人的威胁并不让人感到惊讶。显然他们不必害怕这样一个喜好奢华的民族。 表面现象有时当然具有欺骗性;但这次却是符合事实的,在他们早年的历史中,斯巴达人确实以享乐主义和贪婪而臭名昭著。他们得到的共同神谕是:"贪婪令其毁灭。"4公元前八世纪和七世纪的时候,斯巴达曾经一度是其他各个希腊城邦所厌恶的一切的典型:他们中的精英分子既残忍又贪婪;他们渴望土地到了令人厌恶的地步;他们的市民阶层普遍贫困,这些统治者还剥夺人民的财产甚至自由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看到斯巴达各阶层之间的仇恨到了戕害自身的地步,外邦的分析人士为之震惊,毫不犹豫地将它判断为"希腊最糟糕的政府"5。在那个时代里竞争还不算激烈:公元前七世纪正是希腊世界各处之间的贫富多寡差距逐渐拉大的时候,所以人们用"优诺米亚"(eunomia)来称呼一个理想的好政府,这就像是一个遥远的梦境一样飘忽不定。 社会的动荡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存在,例如米底和波斯的那些部落酋长们曾经多次引发这样的事件。而在希腊人中间,对好政府的渴望确实特别的急迫。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追求好政府的旅程是孤独的。贫瘠而落后的国土无法与拥有上千年君主统治传统的东方相提并论。他们也不像扎格罗什山脉中的那些部落居民,因为距离文明发祥的土地太过遥远。由于没有现成的官僚机构和中央集权的范例可以模仿,希腊世界很早就分裂为众多互相竞争的城邦,每一个城邦都拥有独一无二的体制危机。尽管他们常年处于紧张的社会冲突的痛苦之中,但是希腊人没有完全忽略地方主义给他们带来的自由:他们可以试验、创新并铸就自己的独特道路。"一座弹丸小城,只要能够得到良好的管理,也要比一座愚蠢的尼尼微所有的辉煌之处都要出色。"6当然,同希腊诸城邦所在的崎岖地势相比,两河流域冲积平原的开阔地面可能确实显得有些缺乏生机。在希腊,众多山脉将平原分割成小片,也把各个国家彼此相互分隔开,更不用说它们也因此同更为广阔的世界隔离开来,这为它们提供了相对独立隔绝的地理环境。 斯巴达人显然得益于他们城邦的地理位置。他们能够任意地纵容自己好战的阶层,因此得到的一切利益都要归结于他们占尽地利。他们城市所统治的疆域位于希腊南部的偏远地区,名为拉克第蒙(Lacedaemon),这片土地由一些天然的屏障所环绕:东、南两面临海;北方矗立着灰暗可怕的大山;西面又有荒凉高大的泰格托斯山脉(Taygetos)横亘,其五座如利爪一样耸立的山峰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也时常覆盖着积雪。在这些险要的边界之内,一座城市可以轻易地从毁灭的关头恢复过来,并继续安定地存在。 但是在这样的边界中也同样容易发生进化和变异。斯巴达人和波斯人一样起源于部落君主统治,其国家产生于古老的游牧时代。虽然斯巴达这个名字非常古老,但是它本身只不过是建立在一块新垦土地上四个村落的联合体。它同原来的那个斯巴达,也就是海伦和美涅拉欧司生活过的那个斯巴达没有任何关系。在拉克第蒙平原上矗立的这对夫妇的坟墓虽然让人难以忘记,但是他们的神庙并没有见证延续不断的历史,恰恰相反:是历史彻底、粗暴的断裂。在神庙周围到处散布着许多墓葬的封土,这些都是荒废已久的宫殿,也许它们就是当年海伦和美涅拉欧司居住过的那些地方;然而,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包括这些在内的所有拉克第蒙的辉煌建筑都被洗劫一空并付之一炬。是谁,为了什么原因做出这种事来,很快就被人忘记了,随之被人遗忘的还有一切关于这片废墟曾经有过的东西。数百年之后,美涅拉欧司的王国崩溃所留下的空白逐渐被某些来自北方的新移民占据了,这是一些后来被称为多利安人(Dorian)的游牧部落,他们以彻底区别于那些被征服的希腊原著居民而骄傲。7这些多利安人也属于希腊人,然而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所继承的这块土地上辉煌的过去。对他们来说,这里"有关英雄时代、城邦起源以及任何联系着遥远时代的传说"8比任何一个国度都更加宏伟动人。这些定居者对拉克第蒙家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己也开始赞颂他们。大约在公元前700年,几乎在与米底人和波斯人在遥远的扎格罗什山脉定居下来同一时期,人们偶然发现了海伦的墓地。更令人热血沸腾的是,斯巴达的精英人士开始为自己制造一个古老的家系,这个家系可以上溯到早于美涅拉欧司王统治的时代,一直追溯到他们中最为伟大的人物,就是那位杀死怪兽的英雄赫拉克勒斯,众神之王宙斯的儿子。这样,多利安人远祖的入侵行为如今就表现成为一次回乡;他们通过征服而得到的东西反而成为一笔遗产。斯巴达人的领袖将自己称为"赫拉克里德"--这个称号表示他们是赫拉克勒斯的后人,这也说明他们不仅是拉克第蒙,同样也是大部分希腊的统治者。 这一切当然向他们的邻人们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到公元前700年,斯巴达人就已经取得惊人的成功,跨越了最具威胁性的自然边界--泰格托斯山脉,发动了吞并位于山脉西侧的梅西尼亚(Messenia)的土地的战争。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宽敞的舞台",这里的土地"适宜耕种,丰产水果"9,甚至比拉克第蒙那里的土地还要肥沃,虽然梅西尼亚人同样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多利安祖先的世系,但是斯巴达人以残忍的侵略和无情的决心,野蛮地对任何可能的血缘关系表现出他们的蔑视。像梅西尼亚这样广阔的土地不会轻易屈服,但是斯巴达人不断冷酷地保持对他们的目标的控制,年复一年地血洗那里的田野和树林。当最后梅西尼亚终于投降的时候,已经彻底屈服了。这场胜利让征服者花去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像这样,一个希腊民族对另一个希腊民族的奴役之彻底是史无前例的。斯巴达人不仅成了希腊最富有的民族,同样成了一种奇观,一个奇怪、独一无二的变异民族。在斯巴达人自己看来,这种神秘的光环是他们独有的。世界上还有其他哪个民族在黄金时代的英雄已经逝去这么久之后,还能够将自己的血脉向上追溯到众神之王自身?斯巴达人制造这种迷信完全出于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他们自己也虔诚地相信了这一切。他们对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情的看法完全受到了这个神圣幻觉的影响。如果冒犯了神灵,则一切都将失去;如果重视神谕,斯巴达人的伟大则完全可以得到保证。因此,斯巴达对梅西尼亚的征服,是注定能够实现的。也同样因此,它能够无视漫长的战争,甚至还能够从更为重大的危机中挽救自己的命运,从几乎彻底崩溃的社会中令人惊讶地铸就出一个"好政府"的典范。 在改革和毁灭中做出这样的选择是赫拉克里德人经过漫长思索之后才作出的决定。然而,占领梅西尼亚却并没有拖延任何时间,而几乎是仓促行事。胜利虽然给斯巴达人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却丝毫没有改变穷人的悲惨境遇。事实上,由于更大量的资源被集中到贵族手中,反而严重加剧了贫富差距。或许,斯巴达人上层阶级的条件同遥远的米底人上层阶级的状况相比的话,他们就完全可以忽视那些服从自己的市民们贫困的境遇了,也不用再以他们所呼吁的重新分配土地以及所有"反对国家的煽动言论"。10但是斯巴达并非米底--恰在这时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军事革新,这场革新逐渐在整个希腊地区造成了风云激变的局面,也几乎给赫拉克里德人造成了倾覆性的后果。由于为斯巴达赢得梅西尼亚的并不是那些雄赳赳、耗费昂贵、永远处于上层阶级的骑兵。反而是那些出身农户的重甲步兵,这些人虽然无法负担起马匹的费用但仍然能够置办武器盔甲;尤其是所谓"重盾",这是一种设计新颖的圆形盾牌,高宽都达一米,在其木质表面上包裹青铜。一排手持"重盾"的人--即所谓"重甲步兵"--以方阵的队形前进,形成铜墙铁壁般的防护,或许他们还身着头盔和胸甲,手持长矛,这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破坏性进攻武器;斯巴达人在同梅西尼亚人的战争中有机会对这种极端致命的新型战法进行各个方面的尝试。然而这并非一种容易的战法。每一面铜盾如果能够发挥其功用的话,就可以为其两侧的人提供如持盾者一样的保护--所以方阵在向敌人进攻的时候,如果存在任何阶级分化,它都要担负边线遭受攻击而崩溃的危险。 在一首斯巴达人的战歌中唱道:"团结一致,保持方队,绝不放弃,永不言退。"11言论号召在每个阶层中以重甲步兵为目标进行军事训练。毕竟,如果不能完全信任队列中自己身边的农民战友,那些最为纯种的赫拉克里德人在战场上的命运是无法想象的。进一步假设,如果农民们自身不能继续负担制作盾牌的昂贵费用,斯巴达自己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一片废墟--尽管残酷但这简直是一定的,因为梅西尼亚对它怀有刻骨仇恨。虽然斯巴达人依靠下层阶级发家致富,但是他们在获得成功的同时,突然之间发现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时刻面临着灭顶之灾。到公元前七世纪中叶为止,有关公民团结的观念不再仅是那些邋遢农民们一厢情愿的渴望了。甚至对赫拉克里德来说,它也成为生死攸关的大事。 恐慌导致了特殊的解决办法。拉克第蒙开始改革。对未来感到绝望的斯巴达人被迫忘掉那些由来已久的阶级差异,转而服从一项恢宏但难以接受的社会整合试验。但是怎么会,准确地说--受到何人的煽动?斯巴达人曾经狂热地沉迷于古代英雄令人难忘的各种传说,他们不是那种受到某种无名的社会力量影响便为自己树立新秩序的人。显然这只可能是某个传说中的圣贤的作为。过了很久,一个名字"吕库古"(Lycurgus)开始浮现出来。在斯巴达建立"好政府"之后仅仅过了大约一个世纪,这个神秘人物就已经被当做这项功绩的建立者明确地受到人民的赞颂。一般说来,人们认为他是一名赫拉克里德显贵,斯巴达王的叔父,脾气非常严苛,"气节高尚而且公正"。12这就是所有他的传记作家们所公认的全部行状了。甚至是那些神谕者都承认难以弄清吕库古究竟"是人还是神"--尽管如此,总而言之,他们大多倾向于认为他是一名圣贤的超人。13斯巴达人接受了这个看法,修建了一座神庙用于纪念这位伟人,而委托于他的改革事业很快也被定格于遥远不明的年代中,如同所谓的"赫拉克里德家系"一样,人们也为他假造了一部古老神圣的族谱。掌握了过去也就掌握了未来:一个国家刚刚为自己尝试着动过一场好像外科手术一样的改革,立刻就将它视为自己传统的最关键部分。随后人们提出,吕库古"看到自己所立之法拥有的美与崇高,深受感动,并心满意足,如今这工作已完成并贯彻实行,他希望使之永世不朽,坚定不移--或至少在人类所能预见的时代中能够如此"14。斯巴达人为了尊重他,或者很可能也是为了虚构他,完全实现了他的梦想。他们是历史上第一个发现,巩固革命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它变成一个神话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