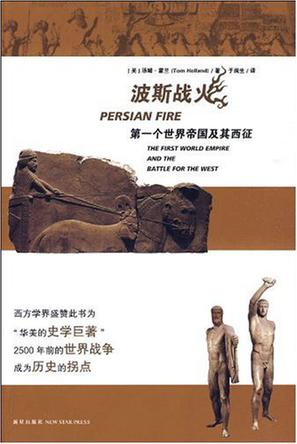如果没有尘土,世上永远不会有市邑或者帝王。所以巴比伦人认为自己的文明完全是从泥土中塑造出来的。鸿蒙初辟,当整个大地还是一片汪洋的时候,众神之王马杜克(Marduk)用苇草建造了一艘筏子,表面铺垫尘土,和水搅拌成稀泥并用这些材料为自己制作了住所,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房屋,名叫埃萨吉拉(Esagila)。很久之后人们还能够看到他矗立在巴比伦的腹地--但是无需任何神庙建筑告诉巴比伦人,他们就能认识到土与水的功用了。他们对这一点的认识非常深刻,马杜克神在太初之时就宣称"我得到血液,我将创造肉体,我将塑造出第一个人类。1"正如所言,他适时地将尘土和被杀死的敌人的淤血块掺在一起,并用这种混合黏土制作出人类。这样,在创造人类最初的行为中,就已经为一切奠定了基础。沙场上的尸体,城墙中的砖头:这些除了泥土之外还有什么呢?巴比伦人处在阴冷的群山和荒漠的环绕之中,他们看着自己的土地,就知道自己是世上最为幸运的民族了。得到了不仅一条而是两条河流的庇佑,这就是众神青睐的最大证据。他们拥有肥沃的土地、高耸入云的辉煌建筑、商贾兼海运之便;这些都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赠礼。所以,希腊旅行者将这片尘土原野称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因为,如果没有水,巴比伦的全部财富除了干燥的尘土之外都会变得一无所有。 这座城市被看作波斯国王王冠上的宝石。巴比伦人清楚地知道--失去了它,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他们信心满满地习惯于认为自己的城市是一切重大事件的支柱。数百年以来,他们的野心曾震动过整个近东地区。在所有亚述的敌人当中,巴比伦一直是最为顽固的一个,它曾带领着米底人发起叛乱并摧毁了那个可恶的帝国。在这个废墟之上,巴比伦人随后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强迫邻人们接受他们比较温和的统治手段,这些手段亚述人也曾经运用过,那就是"铁轭"。2正如耶利米在遥远的犹大哀歌的那样:"他们的箭囊,是敞开的坟墓,他们都是勇士。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是你儿女该吃的,必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又必用刀毁坏你所倚靠的坚固城。"3一切正像这位先知所预见的一样发生了。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攻陷,成为一片废墟,不幸的犹太人遭到流放。就在这片土地上,伴随着巴比伦河水的哀哭,犹太人各部被异族从自己的国土上一起迁移出来,横跨整个近东,来到两河流域,这里虽然繁荣富庶,长久以来早已不能够自给自足。这座城市只有像吸血鬼一样依靠遥远属国的供给才能够维持它自身的享乐,只有不断剥削外族人和他们的产物,才能满足它庞大的胃口。各种移民,不论是努力还是遭到流放的人,不论是雇佣兵抑或是商贩,云集在巴比伦城市的街巷之中--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多元文化的城市。即使在被居鲁士征服之后,它仍然是整个近东地区最大的熔炉,在其街道上可以听见成百上千种不同的语言,徘徊着各种异域动物,无数珍稀禽鸟羽翼闪耀,还可见各种来自遥远国度的金银珠宝。还有哪里堪与其相比,可以成为波斯的后花园呢?这里可能是帝国的故土--但却难以成为世界的脉搏。 所以巴比伦人认为波斯人的统治仅仅是神意暂时性的偏差,这一点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居鲁士以其惯有的堂皇宽宏之气概,不屑于将所征服的统治家族彻底铲除;所以即使巴比伦的末代国王纳博尼杜斯(Nabonidus)在他的城邦陷落之时已经是一个垂垂老矣的人,此人死后仍然留下不少可靠的后人。其中一人利用了巴尔迪亚遇刺所造成的混乱时期,在十月上旬宣布自己为尼布甲尼撒三世。这个名字对于那些过去曾经饱受巴比伦人压迫之苦的民族来说,就像一个可怕的预兆一样:因为尼布甲尼撒二世是巴比伦最为伟大的统治者,他不仅征服了耶路撒冷,还拥有许多其他的功勋,他是城市的毁灭者,是各个骄傲民族的破坏者,对他的记忆保存在他曾经征服过的人们心中,他的名字就是繁荣、黄金时代和死亡的代称。但是如果新国王的名字能够让整个近东地区再次破碎的话,对巴比伦人来说这种效果正是他们自己梦寐以求的。他们的世界似乎必须恢复到从前的平衡状态下。对全世界的统治权力被波斯盗贼从美索不达米亚手中偷走了,现在是时候将这个权力归还到它应该从属于的地方了。因此,作为惟一的权力化身,尼布甲尼撒可以再次登上权利的顶峰。 大流士对宣传活动的可能性向来非常警觉,他非常了解这种情感,并没对其掉以轻心。因此,当埃兰发生叛乱切断了他回到帝国腹地的道路时,他并没有前往波斯,而是直接赶到两河流域。如以往一样,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山区赶来,所走的道路正是十七年前居鲁士曾经走过的那条--也正如居鲁士曾经做过的那样,起初他发现这条道路完全向他敞开。在道路旁边矗立着一个巨大的石头阳具,这就是两河流域的界碑;在他的面前就是平坦完整、一望无垠的冲积平原。偶尔只有弯腰耕种大麦的农民身影,闯入这空旷的原野中,此外就是随处可见的棕榈树丛为天际线增添几分曲折。这些景物标志着层层叠叠的沟渠和运河,但远不及更南方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地区富饶;因为底格里斯河与其姐妹河比较起来最令人难忘的就是陡峭的河岸--这对农民来说非常不便--这条河流正如其波斯文名称所说的:它像"箭"一样飞快地流淌着。 然而,人们可以将另外一面看作对农耕灌溉目的不利因素的补偿,它是一条理想的天然防御工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坦无险的地势中,这里显然是最为易守难攻的地点。为了抵御米底人入侵的威胁,阻塞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一马平川的地区,这里修建了一条坚固的边墙加以防守,墙厚八米高达十米,从令人乏味的平原上可以看见城墙辉煌的垛口。在它修建起来七十年之后,"米底边墙"仍然可以证明修建它的君主--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强大确实令全世界颤栗。诚然,除此地人们难以想象另有一处更加适合修建这样的工事,足堪展现王权的伟大。米底边墙横穿整个阿卡德地区,这个神秘地区充满了关于致命侵略的回忆。在这里,早于尼布甲尼撒数千年之前,有个令人沉醉的梦想曾经在一个名为萨尔贡的男人手中变为现实,他从此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因此,巴比伦的诸王皆以自己被称为阿卡德国王为荣。这样的一个头衔,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其他称谓--所谓的"天下四方之主"或者"宇宙的主宰"--相比起来要显得谦逊得多;但它可以将巴比伦的各个国王同这个帝国的源头联系起来。尽管阿卡德的辉煌早已随风而去,很久以来它已只是一个地方省份的名称了,但是它曾一度作为世界统治者的宝座--因为早在公元前23世纪的时候,正是在阿卡德孕育了最早的世界观念。 萨尔贡这位远古的冒险家,尽管来自于蛮荒之地,但还是培养了这种骄傲的野心,消除邻近城邦的独立并将"普天之下的土地"4统一到最高的统治者手中,这一直是两河流域所有强者的典范。在建立阿卡德大约两千年之后,他仍然是伟大国王的指针。确实,在波斯人征服这里之前几十年,人们对他的执迷达到了真正狂热的地步。在埃兰的首都苏萨,原先由萨尔贡的孙子所铭刻的胜利纪念碑被清理出来,长期展示;在阿卡德,当一尊这位伟大人物的雕像出土的时候,纳博尼杜斯马上前来视察并指导对它的修复工作。各种"博物馆"到处兴建起来:例如在乌尔,纳博尼杜斯国王的女儿恩尼加尔迪南娜公主收藏的大量古物被认真地加以分门别类并向公众展出以达到启迪民智的作用。而同时在巴比伦这里,许多学者们在各个大图书馆的浩繁卷帙中查找古代的文献,引经据典,依古法为他们主人的各种奇思妙想和需求寻找合法依据。在两河流域生活的人们,由于长期生活在数千年来留下的积习之中,向来谨慎遵循古制。他们并没感觉受到古法的压抑,而是不断重新利用它们、组合它们,并利用它们寻求利益。 面对这种古老带来的威胁,人们期待波斯人用不同的方式回应它:怀疑,最好是恐惧。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很多人的历史与之相比,也只不过是一瞬间。随着世界时代的变迁,有人谨慎记录着王家世系和星象图示,对于依靠这些材料的人来说,它们都是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巴比伦向来以神巫云集著称。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自古以来建立起一个天文观测台的庞大网络,以便于占星士观察上天的各种警示,并以最快的速度将它们的消息传给他们在巴比伦那些智慧过人的首脑们。这种预见未来和绘制为管理国家提供依据之用的星图的能力通常能够成为巴比伦各个国王的潜在武器。他们的城市同样也因精细而神秘莫测的宗教仪式而闻名,那里有无数的塔庙和神殿,据猜测那些纪念碑基座修建于远古时代,其设计图可以追溯到鸿蒙初辟的年代,用来修建这些建筑的砖块上印有众神的指模,当这一切联系起来的时候,巴比伦几乎无人能及,不可战胜。 而当公元前539年居鲁士第一次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并没有感到任何威胁。的确,他自己对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异国的复杂传统表现出比纳博尼杜斯更大的兴趣,他认识到这些因素对帮助自己统治具有重大的潜能。巴比伦的末代国王虽然对古物非常着迷,但最终在研究这些问题上走得太远。他不满足于对萨尔贡的英雄崇拜,甚至吹捧亚述诸王,将他们称为自己的"王家祖先"5并采用他们的头衔。这种做法在一个某位亚述国王试图从地球表面将其抹去的城市中,应该说至少是不够谨慎的。然而对巴比伦人来说从情感上更觉得是被冒犯的,在纳博尼杜斯的行为中最致命的是,他居然将马杜克神像的鼻子从接合处弄掉了。 对于一位神来说最为麻烦的就是尊重他的尊严,这一点通常是难以想象的。任何人类,即使是最为伟大的统治者也难以承担冒犯他所造成的后果。这就是每当新年到来的时候,人们都愿意看到国王拜访城市中最大的神庙埃萨吉拉,并在马杜克神像金身的责备目光注视之下,接受一个宏大仪式的羞辱,在这里国王被他人掴面颊和揪耳朵。如果国王因此泪流满面,那就最好不过了,因为这意味着神对此感到满意;如果国王对此无动于衷,那么这预示着他的王国将要遭遇某种灾祸。纳博尼杜斯的行为对巴比伦人的思考方式来说,可以认为特别恶劣。不仅因为他自己经常不在巴比伦,整整十年没有拜谒埃萨吉拉,而且更为火上加油的是他在马杜克神的宫殿中提倡崇拜古老的月神辛(Sin)。他的确发掘到了这样做的完美的古代理由,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巴比伦并不像它的市民们所夸耀的那样,是世上最为古老的城市,事实上反而修建的相对较晚,因此,其庇护神马杜克同样也应当是后来才登上众神宝座的。纳博尼杜斯希望通过发动对辛神的崇拜,为他历史悠久的帝国提供一种不太明显的爱国尽忠的情怀,从而削弱马杜克神盛气凌人的感觉。然而,这样做的结果,使他亲自为居鲁士致命的宣传攻势彻底地敞开了道路。据说,"马杜克纵览天下万国,寻求一位合适的统治者,"6并最终找到了一位波斯国王。居鲁士被他的新臣民迎进了巴比伦城,谴责纳博尼杜斯为异端,并高兴地将自己宣布为马杜克神所选择的王者。城市古老的宗教仪式现在被允许继续举行免遭打扰;那些用于礼拜的偶像,原先被纳博尼杜斯挪作警卫之用,现在也被重新放回适当的神龛中,据记载在波斯统治的头几个月中,冈比西斯作为其父亲的代理人,也曾经前往埃萨吉拉参加掴耳光的新年仪式。 马杜克神因此非常满意,两河流域的土地上也秩序井然。诚然,波斯人只不过是些暴发户,诚然,对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居民来说遭到他们眼中乡下人的统治实在令人心神不宁;但是居鲁士和冈比西斯为巴比伦人带来了和平。作为王者来说,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美德了。马杜克神的祭司们,得到了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首要地位和占有巨额财富两方面的确认之后,和别的本地人一样热心地同异族统治密切合作起来。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依然繁荣。在纳博尼杜斯统治时期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商路不再由于波斯的制裁而中断,现今重新充满了车队。对于商人和银行家们来说,将美索不达米亚吸纳到一个世界帝国中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商人们不会将对故国尽忠的感情看作牟利的因素。例如埃吉比斯这个银行世家世代以来为巴比伦本地王公们提供信贷,但是在他们见证了纳博尼杜斯垮台之后,立即顺从地接受了新秩序,他们在自己的商业文书中采用了居鲁士继位后的纪年,并希望将事业扩展到伊朗。几年之内,他们就在埃克巴塔纳和整个波斯开办了自己的办事处,在各个不同的广阔领域中积极投资,其中包括奴隶贸易和婚约的买卖。随后,由于在两河流域突然爆发了叛乱,埃吉比斯家发现自身遭到垮台的威胁。公元前522年深秋,他们在巴比伦的总部和各地分支机构失去了联系。这个家族中两个兄弟被滞留在波斯。银行的外债开始增加。所以在埃吉比斯家族看来,这座城市的叛乱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灾难。如果能够尽早镇压它,并恢复市场的稳定,那才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对大多数巴比伦人来说,波斯人的统治如果陷落到谋杀和分裂中,就是由于他们叛变造成的后果。正如纳博尼杜斯冒犯马杜克神所造成的后果一样,现在一切不言自明,他本人不得不屈服于他所反对的居鲁士战争机器之下。这种假设虽然威胁到大流士对王位的继承,也同样为他提供了一个炫目的机会。作为受到阿胡拉马兹达神选立的人,他为什么不能证明自己也是巴比伦最高神所钟爱的人呢?马杜克神毕竟推翻了异端的纳博尼杜斯,难道现在可能反过来支持他的儿子么?对大流士来说,没有别的机会比粉碎巴比伦这次叛乱能更好地证明自己是全世界的合法统治者了。毫无疑问,他为了抵达米底边墙费尽了千辛万苦。接下来,大流士调转队伍的侧翼,带领军队渡过底格里斯河,他的士兵们或者紧紧抓住马匹和骆驼,或者伏在充气的皮囊上。公元前522年12月13日,他的军队在战场上遭遇了尼布甲尼撒三世的队伍,并且击溃了对方。六天之后,他又取得了第二次胜利,大流士就完全击溃了巴比伦的军队。尼布甲尼撒同他的骑兵残部掉头逃回了自己的首都。而那些落在后面投降的人没有一个得到了宽恕。通往巴比伦的大道如今在他们面前敞开了。 大流士毫不犹豫地踏上征途。他的面前是这个星球上最为庞大无匹的都市所发出的遮天蔽日的滚滚烟尘,令地平线模糊不清。在巴比伦城狭窄蜿蜒的街道中,居住着大约二十五万居民,这个数字是前所未有的;城中到处都是砖块、人和动物以及粪便,而且城市还需要修建最为漫长的城墙以便保卫延伸出去的各个部分。巴比伦城中任何事物都无比巨大,它的城墙包围起来的面积几乎达到整整三平方英里,拥有八座装饰豪华的城门,在那些没有幼发拉底河天然保护的地段,人们修建了护城河来保护城墙,"河中的水流掀起如同海浪一样狂暴的波涛。"这座巨大的城市为天下各种梦想提供了合适的演出舞台:"巴比伦,这是一座富足的城市;巴比伦,这是一座处处欢庆、喜乐、歌舞升平的城市。"7即使在那些阴暗的小巷中,都可能看见爱情女神伊师塔(Ishtar)降临她所钟爱的酒馆或者街道时,悄悄经过的身影,因此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发生艳遇的地点,显示出欲望的迹象。无怪乎巴比伦在遭到流放的犹太人眼中,像是一个淫荡的大妓院,而对于那些来自遥远国度的人们来说,这里是神奇而魔幻的地方。它号称拥有固若金汤的城墙,绵延长达五十六英里,有一百扇青铜大门。据说,在大街小巷中,人们将娼妓看作神圣的职业,父亲们兴高采烈地为自己的女儿拉皮条。巴比伦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毋宁说它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事实的确如此,据说"它的规模如此之巨大,以至于居鲁士几乎已经控制了它的近郊,而城市中心的人完全没有察觉他的到来,所以巴比伦人仍然继续庆祝他们的节日,继续歌舞升平,放纵自己。这就是这座城市第一次陷落的过程"。8 那么第二次会如何呢?传说中居鲁士攻占巴比伦的种种难以理解的地方,仍然暗示出某种战略上的实际情况:任何一支军队攻破城墙之后都会发现自己被它庞大的身躯吞没。当大流士的士兵们看到巴比伦城墙从薄雾中向他们显现出来的时候,一定觉得心跳加快;没有任何东西,即便是埃及的神庙,都从未让他们见识过这里如此巨大的体量,但是他们的将领并没有觉得有任何失败的预感。大流士清楚,因为他的谋士们已经向他献策,现在巴比伦就像一枚成熟的果实等待采摘。这城市,表面看来似乎无法攻破,事实上却过于分散而难以防御。如果有人惊讶于它所声称的那样,是世界的镜子,那这镜中反映出来的只有社会和种族之间的仇恨。渴望和波斯国王合作的人不只包括教士和商人。巴比伦到处都是刑徒流军之后,这些人散居在城郊附近。他们中没人愿意为尼布甲尼撒卖命。这座城市的国际性从前曾经是它帝国强大的标志和拱卫,如今却成为威胁它安全的无政府主义。巴比伦人在这样的前景中畏缩不前,他们甚至愿意以接受异族统治的代价来避免改变。美索不达米亚的混乱状态一直是人们最严重的噩梦。他们认为世界产生之初就受到魔鬼的摆布,无法控制荒蛮,直到众神出现,垂怜人类,为他们树立王者以确保秩序。如果没有君主,城市生活自身就会停滞,魔鬼一定会重返。从非常遥远的古代开始,甚至在比萨尔贡和他的帝国年代还要古老得多的时候,人们就认为:"要拥有权威、财富、力量,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神圣权利……你要屈服于强者面前;要在拥有权力的人面前显得谦卑。"9这或许算不上最富英雄气概的格言,但却是万民遵奉的生活实践习俗。巴比伦人看到波斯国王气势汹汹地策马奔来,立刻望风披靡。就像他们曾经对居鲁士所作的那样,又一次敞开了自己的城门。 就这样,在大流士进入砌满金碧辉煌的琉璃砖的主城门时,轻松地拥有了这座城市。他没有被城市迷宫所困。巴比伦中既有混乱也有对称性。正如众神创造好无形的人类社会的同时也为它准备了神圣的统治机构,同样,在这座世界上最大城市的扰攘纷乱中,有一片布局方正的皇家大街组成的街区。大流士如今就通过其中最为宽阔的"游行大街"举行入城仪式。 巴比伦人将这条大道称为"愿傲慢者不得昌盛",用它来纪念过去的许多辉煌;君主骑马经过整个大街,用这样的仪式来宣告这座城市最为骄傲的那些梦想。在巴比伦,王权的本质就是炫耀。这远不只是一种空洞的浮华,它被看作是对神授秩序的见证,想象一下,这如同一道闪电照亮整座城市,感染了所有人的身体和灵魂,感染了每一粒尘土、每一块石头和砖块。"游行大街"的建筑为这种隐喻提供了激动人心的背景。在大街遥远的尽头,矗立着所有巴比伦建筑物中最为惊人的--一座宏伟的塔庙,与之相比,即使是埃萨吉拉也会显得黯淡无光,这座塔庙由一千七百万块砖修砌而成,高度几乎达到一百米高,这就是埃特美南基(Etemenanki,又名"巴别塔"),或者被称为"位于仙凡两界之间的殿堂"。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它位于城市的正中央,这里存在着深奥的秘密,安置着预言性的象征物。但是埃特美南基并不是它的惟一化身。在巴比伦人的观念中,他们国王不仅是一个凡人;根据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古老传统,国王必须既是整个社会跳动的心脏,也得是绝对引人注目的人。因此这没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需要用一次在"游行大街"上进行简单访问来加以阐明。在所有进入巴比伦的人眼前,除了城市的正门之外,在他们道路的尽头,还看得见一座庞大的宫殿,这就是埃特美南基在这条大街远处的尽头矗立着;这座宫殿由彩色的砖头砌成,其辉煌灿烂如同镶嵌了黄金、白银、天青石、象牙和雪松木一样,那些看到这样景象的人都会不禁低头垂目,盯住地面。这样一番秩序井然的场面不仅是皇家权利的表现,而且是经过精确算计,正好可以强化它。任何人都会从心底对它表示屈服和顺从。 美索不达米亚具有迷人的长处,常常会对邻近地区的国家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其中安息的国王们一直将巴比伦作为王家统治最好的典范。大流士经过"游行大街"进入了宏伟的皇宫,宣布继承这笔丰富的财产:他,波斯国王,同样可以作为巴比伦国王来统治,也同样是阿卡德国王。尽管他拥有傲人的家世:他是"阿黑门尼德王族的一员,是一名波斯人,是波斯人的子孙",10大流士仍然乐于用劫掠来的战利品--美索不达米亚的"万国之主"这样的头衔来加封自己。比起居鲁士和冈比西斯来说,大流士更有理由来试穿这件黄袍。因为作为一名篡位者,他需要利用任何可以找到的东西来修补自己继位的合法性。 通过征服巴比伦,大流士给所有需要警告的城市上了一课。因为有洞见智慧的人看得出来,这座城市一定被作为王权统治的伟大注释,被铭记在宗教仪式、奢华生活和铭文中。他在巴比伦所吸取的教训显然非常有价值,而且必须有价值--因为当大流士在这座城市中逗留时,开始收到各种不安的消息。他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胜利并没能给他的敌手们施以致命一击。在他努力统治的整个国家内,反叛开始到处出现,并不断增加。有关起义和战争的消息开始不断传来。 对大流士来说,整个世界目前危如累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