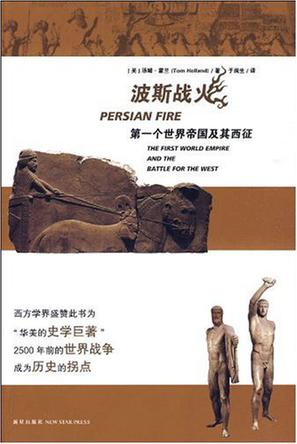双重幻影 他真的这样死了么?刺客们制造这次血腥事件之后立刻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传说。被害者的尸体不能呈现在大众面前,但是现在可以泄露出大量的其他消息来引起全国震惊。谋叛者们讲的故事太令人惊愕了。他们声称,那个被他们谋害的人根本不是居鲁士之子巴尔迪亚。真正的巴尔迪亚已经死去很久了。嫉妒而残忍的冈比西斯数年之前曾经下令将他杀害。如果不是聪明的大流士和他的支持者们偶然发现了这个秘密,并勇于将其公告天下,波斯人永远也不会知晓这个可怕的阴谋。 这些都会遭到明显的质疑。如果在西基阿沃提什遭到刺杀的不是居鲁士的儿子,不是合法的国王,那么又会是谁呢?这种揭露显示出一个更加险恶的倾向。一个冒名顶替者曾经占据皇室血缘下王子的角色长达数年,这本身就足够引人警惕了,但是他甚至能够不受到家人和王室怀疑这一点只能证明他使用了最为黑暗的巫术。显然,一名受到这样的训练,且善于控制超自然力量的祭司,是最值得怀疑的对象。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冒名者在祭司们著名的大本营--尼赛亚圣马平原上遭到袭击。似乎并非如此,叛乱者匆忙宣称巴尔迪亚的替身实际上是一名祭司"名叫高墨达",47此人出身低贱,很可能是个身份不明的恶棍,他的巫术如此有效,阴谋异常胆大,几乎用自己设计的圈套攫取了整个帝国。 预感论的复述能够挑明这些流言蜚语的暗示,并对之推波助澜。尽管此人大权在握,但是这名祭司忘记隐蔽一项关键细节:他的耳朵,由于犯下了某种不明的罪行,很久之前曾被居鲁士下令处以刵刑。欧塔涅斯的女儿帕伊杜美(Phaidime)是巴尔迪亚的妻子,从来未曾怀疑过自己的丈夫被人谋害并代以替身。某天夜里,她趁丈夫睡着轻轻摸索他的头侧,发现了这个可怕的真相。她将此发现告诉了她的父亲,并因此加入了密谋者的行列,做下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大事,最后以杀死替身结束。这就是至少数年以内在整个帝国流传的故事版本。也没有人被允许讨论其真假。 如果有人质疑关于刺杀事件的当晚叛乱者的正当性,抑或指出更为明显的不真实性,或者有人追问为何这么仓促地处理掉替身的尸首,那他也一定有足够的智力来保持沉默。人们还在忙着擦拭西基阿沃提什家具上的血迹之时并不是说这些双关语的正确时机。叛乱者并没有多少心情来容忍各色不同意见。大流士发出的警告已经足够严重了:"今后为王者,当勇于震慑流言,敢于传布流言者,必为王家所不容!"48从政治权术家手中变出来的是令人目眩的戏法。这有利于将原告推上被告席而不会使那些刺客们遭到指控。所有心生怀疑的人都被作为真相的敌人而遭到抵制。 这对于所有波斯人来说都是一个可怕而恐怖的命运。有一种约定成俗的信念,相信大流士的国民是世界上最为忠诚的臣民。他们从小学会了三件事:"骑马、射箭和说实话"。49大流士通过对任何怀疑有关祭司罪行的故事的人加以威胁,不仅仅是为了支持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而同时提出更为高调的主张。只有波斯人会这样做--因为只有波斯人才知道"真理"的真正含义。很多愚昧的民族并不理解,而他们则清楚:没有真理的世界将会走向毁灭并落入永恒的黑夜之中。这不仅是一种抽象,也不仅是一种理想,毋宁说它构成了存在的基础。 这就是众神之中最伟大的阿胡拉马兹达神(AhuraMazda)创造时间与万物之初就造出的真理的化身阿尔塔(Arta),来为宇宙建立秩序。如果没有阿尔塔,世界就缺少形式和美,按照天主马兹达之推动而运转起来的存在物的大循环就难以将生命带到世上。即便如此,真理的作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波斯人清楚,正仿佛火焰升腾朝向天空的时候总伴随着黑色的烟尘一样,阿尔塔也伴随着谎言的化身德鲁伽。这两种秩序--一方面是完美的,一方面则是谬误的,两者互为镜像,从时间初始便相互纠缠,冲突至今。人类应该怎么做呢?显然要站在阿尔塔一方对抗德鲁伽,以真理对抗谎言,否则宇宙自身有可能遭到动摇抑或失败。自古以来有一种看法认为:"那些制造骗局的卑劣之人会让国家遭受死亡之灾害。"50而如果有这样一个"卑劣的人"用某种手段窃居国家王位,那将会给人们带来多么严重的灾难!这个形如巴尔迪亚的祭司装扮成合法的国王,将世界的权柄授予了德鲁伽。大流士和他的伙伴们火速赶往西基阿沃提什,他们推翻的不仅仅是一个冒名顶替者,而是一个更有威胁性的恶魔。他们并不是犯上作乱,而是从事了一项堪比拯救宇宙的伟大事业。 而今,高墨达被推翻并被处死,他玷污过的王冠空置下来。王权的象征物--一件长袍、一把弓箭和一面盾牌--正在西基阿沃提什等待合法的继承。谁将成为这个人呢?在刺杀发生的那天晚上,他如何被人们认出,如何抵抗都已是秘密。最后只留下极为混乱的记载。据说叛乱者趁夜色逃到开阔平原上。在某处约定好的地点,他们勒马驻扎并等待着黎明的降临。当第一束阳光出现在东方山峦起伏的地平线上后,大流士的坐骑首先向晨曦嘶鸣起来。他的同伴们慌忙滚下马鞍,跪倒在地,向他行礼致敬。希腊人在重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认为这些叛乱者在事前曾经约定:"坐骑在黎明时最先鸣叫的人即承大统"51--他们还进一步说明大流士在其中作弊。据说他的马夫此前将手指插入母马阴道之中,当太阳升起的时刻,他把手放到大流士坐骑的鼻子底下。但这是典型希腊人的下流胡说,他们太喜欢糟蹋真理的神圣仪式了! 很显然,即使从这个最不令人满意的说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大流士的登基充满了影响力和威严的礼仪。这些叛乱者聚集在九月夜晚的寒风中,并不是因为他们希望发现谁可能是下一个国王,而是因为已经知道一切。欧塔涅斯这个大流士惟一值得考虑的对手早已臣服于不可改变的事实,并主动退出了对王位的竞争:这些贵族骑马穿过尼赛亚平原是在庆祝一个既成的事实。大流士得到了白色神马嘶鸣的祝福,也得到了群山晨曦的祝福,他知道自己得到了阿尔塔的双重支持。当第一束阳光照亮大地,而在德鲁伽统治下危险晦暗的夜晚逐渐在太阳的光芒中退却。"我能感受到您的强大和神圣,马兹达神,当您掌握着不义之人和正义之人双方的命运,当您的火焰散发出真理的温暖,神圣智慧的力量就降临到了我的身上。"52如今,在这个九月下旬的黎明时分,神圣智慧的力量真的降临到尼赛亚,因为不义的人已经死掉,而正义的人成了国王。 也许,这样的声明让大流士感到高兴。尽管这种想象充满了他的宣传,但这不属于他个人。如果它在所有雅利安人之中导致了对阿尔塔的崇敬,那么它也会引起一种更为严格的二元论教条。"不义与正义之人的命运是一对孪生子"--这不是大流士的话语,而是传说中最富有幻想力的琐罗亚斯德说的,他是雅利安人的预言家,他是第一个向人们揭示世界就是神与恶魔之间无情作战之战场的人。这场战争是所有事物之间的殊死搏斗,预言家在他新奇的学说中继续阐述,这种普世的循环并不会像人们通常假设的那样永远继续下去,而是会朝向一个有利的结局,在这个时候,宇宙的启示指出真理会消灭所有谬误,并在其废墟的基础上建立永久和平的王国。掌握着这最终决定性胜利的是生命、智慧和光明的主宰阿胡拉马兹达神本人--而不像有些伊朗人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众神灵之一--他是至高的、全能的惟一,而不是受造的上帝。从他开始,如同火焰从一座灯塔传递到另一座灯塔一样,各种善行传播开来:从他永恒的光明中产生了六种主要的发散之物,它们是阿胡拉马兹达神座下六位神使,这是神圣的永生者;53还有更为广泛存在的一类善灵;充满众多美好之处的世界;植物和动物(特指那些终日忙于捕食各种来自黑暗势力的昆虫及其虫卵的刺猬一类动物);忠诚而且永远正义的狗;最后才是造物中最为高贵的人类自身。"不要堵塞自己的耳朵,要倾听福音--用聪明的头脑注视明亮的火焰!"这就是预言家的宣言,警示人类面对伟大的裁决。"你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要追随的信念,每个人都拥有由强大的生命考验所赋予的自由。"54选择错误,就会走向谎言、走向混乱;选择正确,才会通向有序、宁静和希望。 大流士是第一个重视这种伟大的和平的人,而正义的宗教可能为他个人的目的服务篡位者么?我们无法真切地知晓。琐罗亚斯德早期的历史及其学说对于他自己的信徒来说也是一团迷雾。这名预言家刚出生时是惟一不像其他婴儿一样啼哭反而发笑的人;人们认为他三十岁那年第一次看到阿胡拉马兹达神的幻象从河水中浮现;他最后在七十岁的时候死去,一名刺客用匕首杀害了他:这就是被崇拜者保留下来的一点点生平碎片。但是一旦涉及他所生活的年代、地区,人们就各自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有人将琐罗亚斯德看作与时间一同产生的人物,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生活在阿斯泰厄吉兹国王统治的时代;55有人认为他从小生活在大夏,其他人则认为他生活在草原地区。但有一点所有人都承认:那就是他既不是米底人也不是波斯人--他的教诲最初只是从东方传到扎格罗什山区。56 但是这有什么作用?毕竟居鲁士所建立的帝国显然不是神权政体;而且永远不会在任何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的国家。波斯人仍然继续崇拜他们古老的神祇,向群山和溪流表示敬意,并在他们国王的陵墓之前用马匹作为牺牲。但由于阿黑门尼德宫廷在他们大部分的仪式中保留异教成分,同样也不会从主流情感中完全去除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正像在伊朗东部各个王国中,这位预言家的一神教信仰仍然有力地控制着一切,在西部,阿胡拉马兹达神也一直被作为最高的神崇拜。在波斯民族的异教信仰和琐罗亚斯德的教义之间并不是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相反,更是一种配合甚至融合的关系。二者来自于相同的宗教冲动表达,这种冲动已经产生了数百年,直到波斯人征服世界之时,仍然保持了发展的状态。尤其是在那些掌握着最为玄秘和神圣的知识的祭司与琐罗亚斯德教士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人们甚至不清楚哪一个教派最先提出要永远同各种爬虫作战,谁最先穿上白色长袍来标志自己的身份,谁最先将同伴的遗体暴露在高处等待鸟类和狗来吞食(这种做法在波斯人看来非常可怕,是为弑君者准备的命运。)这样,伴随着对善神阿胡拉马兹达神自身的崇拜,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米底人和波斯人的马兹达信仰不仅没有将他们和东方的兄弟部族分离开,反而成为他们联合统一的源泉。居鲁士非常重视这样的结合。他希望,在伊朗各族人民之上建立的这个空前的统治具有更大的戏剧性,曾经采用某些来自本民族腹地的古代风俗。为了照顾自己在帕萨尔加迪的部族远离粟特人的侵扰,他曾经下令修建三座惊人的建筑物:这是一些石头建造的巨大火坛,每一个顶部都凿成大而深的碗状,用来承装永远燃烧的白热灰烬。57火对所有伊朗人来说都是神圣的,但是任何人都不会比琐罗亚斯德本人更加崇敬,他教导人们火焰正是正义和真理的象征。他的信徒们将每日朝圣火祈祷看作是必修课,居鲁士在征服东部的过程中一定亲自见证了这些崇拜的场景。毫无疑问,波斯人"反对将死人的尸体焚烧或者其他污染火焰的做法",源于琐罗亚斯德,一位吕底亚学者这样评论,这是非雅利安人中最早有关这位预言者的记载。58居鲁士建造的火坛上的火焰升向波斯湛蓝的天空,的确照亮并突现了新教条--但是它们同样有助于传播另外一种非常不同的训示。居鲁士无意间找到了自己权利的最好形象。有什么样的方式能比火焰更好地表达皇家的伟大呢?甚至那些不了解伊朗人习俗的外乡人也可以很容易看出这样的概念。很快,类似的圣所开始在帝国境内的各地出现,祭司们守卫着这些火焰,只有在位君王驾崩时才会熄灭这些象征阿尔塔神和波斯国王统治的火焰。 现在双手沾满皇室鲜血的大流士开始着手建立天国和人间两种秩序更明显的一致性。他将一切任何已获得和拥有的事物,归因于对阿胡拉马兹达神的热爱:"他令我得助,其他众神也是,我不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我也不是走上歧途的人,我也没有什么不当的举动。"59大流士当然反对了太多此类说法。但是作为一名弑君者和篡位者,他无可选择。他声言拥有王位的理由太过牵强,几乎无法依靠它来为自己的政变作辩护。必须很快地策划另一种合法化的手段。这就是大流士坚持认为自己的角色是上帝选定的--这一点远远比居鲁士和他的子孙们的要求更为急切。 究竟这位上帝是他祖先神谱中的阿胡拉马兹达神,还是琐罗亚斯德所宣称的至高存在者,这一点即使不甚明了也会让这位新王觉得满意。模棱两可自有它的用处。最重要的本质是大流士对自己人民的各种传统表示敬意--他在尼赛亚平原上的情况证明这是完美的表演,一切就这样发生了。昏沉沉的西基阿沃提什高高矗立在平坦的原野上,在此以北大约十五英里的地方,隐约可见整个扎格罗什山脉中最为神圣的山峰--"诸神宫殿"比西顿(Bisitun)双峰耸立。60在此,离伏击巴尔迪亚不远的地方,大流士像所有波斯人和米底人一样在圣洁而纯净的开阔地奉献了牺牲。然而这次严峻而具有历史意义的谋杀,以及刺客们的安排,应当能召唤到琐罗亚斯德教徒们的协助,而大流士的宣传潜力也得到了发挥。根据教义,从阿胡拉马兹达神发生出来的座下善神有六个,而在大流士反对谎言的战斗中的助手也有六人。人们对这种巧合或者雷同现象的思考会有助于新国王统治的巩固。尽管大流士不是居鲁士的儿子,但是他可以表现成为给人无限想象的其他人物,例如伟大的主阿胡拉马兹达神自身的代理人。 这样将他自身权利和某个普世上帝紧密统一在一起的做法是种充满了未来感的做法。篡位者们声明其行动从远古时代开始就得到了神意的认可,但是从来没有堪与阿胡拉马兹达神所提供的相提并论。大流士以其标志性的勇敢而富有创造力的个性开始飞速利用这一事实。他从谋杀与篡位的指控中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少见的合法性;从弱小中为自己铸造了此前所有统治者所未曾拥有过的力量。 这惊人的野心如此令人迷惑,以至于等待它实现所需要的时间太久而令人失去耐性。而选择阿胡拉马兹达神不容许犯任何错误:只要稍有闪失,大流士就会一败涂地。而当他和其他叛乱者还在米底积蓄力量之时,有关帝国对政变反应的令他们担心的消息就传来了。同波斯相邻的另外一个古老王国埃兰爆发了公开的叛乱。在世界上最大最富庶的大都市巴比伦,位于今天巴格达南部。有报告显示出现了一个冒名者声称继承空闲已久的王位。突然之间,波斯帝国看起来并不是为人类带来阿尔塔神的世界和平,而仿佛即将解体,迷失在漫长的阴影之中。对自称为光明战士的大流士来说,最后的考验迫在眉睫了。他和整个中东地区的命运都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 通向巴比伦的道路等在他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