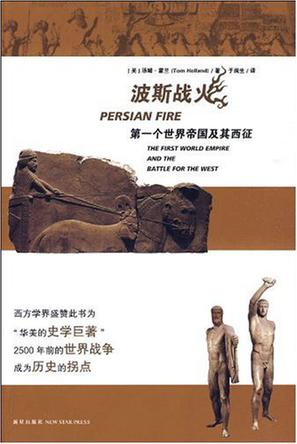世界主宰 据说,即便在所有证明其伟大的事务簇拥之中,阿斯泰厄吉兹仍然被一个预言的重重鬼影所包围:他不断梦见自己受到折磨、不断有迹象警告他国家将被毁灭。米底人将这归结为一类幻觉,而所有在世的祭司们都在试图占卜这到底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些宗教方面的专家善于趋吉避凶之术,他们向国民保证人们性命无忧,因为对这个虔诚而规矩的民族来说,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即使在最明亮的光芒之下也会有黑暗的阴影。而对于祭司们来说,好像全世界都已经对这一显而易见的真理感到熟视无睹。在遥远的地方人们照顾着一丛永恒的火焰,它既不在最寒冷的泉水旁边,也不在最高的山峰之上,这火焰燃烧在一处不被尘世污浊之物沾染的纯净地方。造物主同时带来了黑暗和光明。蝎子、蜘蛛、蜥蜴、蛇和蝼蚁,各种爬虫和蠕虫都是从无处不在的阴暗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祭司的职责就是只要见到这些生物就消灭它们,同样他们也要保卫人们的梦境免遭黑暗的侵扰--尤其是国王的噩梦。"由于空气中充满了鬼魅,它们漂浮在人的呼吸中,现形在那些被幻觉惊扰的人的视线里。"11伟大的国王也需要像圣火一样得到精心照料。 但是一个像米底这样强大的王国,崛起并获得独立走向强大还不到一个世纪就又一次屈服于外来统治,在很多人看来都是难以置信的。对于米底人自己来说,却有很充分的理由了解本地区令人痛苦的大国角逐规律:盛衰无常。没有一个王国,包括亚述,能够击败所有与之抗衡的力量。在近东地区,那些掠食者潜藏在各个角落,捕捉着弱者的气息,伺机发动攻击。古老的国家不断消失,新生的国家取而代之,那些编年史家们在记录他们曾经赞美过的王国的毁灭时,可能觉得自己正在描绘一些古怪的年代久远的陌生民族。 这当中有不少人和米底人一样同属于雅利安人,这是一些在历史上很少被记载到的游牧部落移民。例如,公元前843年,亚述人曾经在他们王国北边的山区同一支自称为帕尔苏阿(Parsua)的部落战斗过;两百年后一个名字非常相似的民族在南方,古老的安息王国的废墟之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其位置在扎格罗什山麓和波斯湾闷热的海滨之间。没有一位编年史家能够说清他们是否是同一个民族。12这些新到来的人只能扎根于此,吸收所取代民族的某些文化,最终才能被那些资格更加老的邻居们接受。如同以往一样,提到这个地区总会谈到那些数百年来难以改变的积习;但是这些外来者,当他们称呼他们新故乡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命名。因此从前被人们称为安息的地方逐渐变成了另一个不同的名称:帕尔萨或者波斯,波斯人的土地。13 公元前559年,当阿斯泰厄吉兹还统治着米底国的时候,一个年轻人登上了这个突然崛起王国的宝座。他的名字叫做居鲁士,此君行状可以概括为:鹰钩鼻、志大、才高。甚至他在出生之前,就已经被送上了伟大的光环;如果你相信故事的话,正是他被预言为伟大的米底人的克星。可能阿斯泰厄吉兹曾经在梦中看到过这一切:他在幻觉中看到,他的女儿芒达妮正在撒尿,可是尿出来的却是止不住的金液,甚至将整个王国都淹没了。第二天早上,国王将这个梦讲述给他的释梦家祭司听,祭司变得面色苍白,并且警告国王,芒达妮所生下的任何儿子都可能威胁到米底帝国的大统。于是阿斯泰厄吉兹将女儿匆忙地嫁给了一位波斯人臣子,此人也是一个落后的无关紧要的小邦的君主,希望这样可以抵消不幸的预言。但是当芒达妮怀孕之后,阿斯泰厄吉兹第二次做梦:这次他看见了从她女儿的两腿之间生出葡萄藤来,这葡萄藤不停地生长,直到将整个亚洲都覆盖在它的树荫之下。他在惊恐之中等待着这个外孙的降生,并且立刻命人将这个刚生下的男孩处死。这类故事总会发生一些意外,这个命令并没有被执行。婴儿被抛弃到山边,但是被一位牧羊人发现并抚养长大;或者可能如传说中那样,是强盗发现了……或者甚至是一条母狼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他。无论这些细节怎样,成长中的神奇特点都会明示这个弃儿得到神宠的未来--当然,因此也证实了居鲁士活下来并发展壮大。当他长成一个成年男子的时候,他天性中的高贵为他赢得了波斯的王位。这就是阿斯泰厄吉兹用尽计谋想要避免的事情--从此米底帝国的命运就注定了。 也许这就是传说表达的方式。伟大人物的特点就是能够吸引夸张的故事,也许居鲁士早年的命运并不像波斯人后来所声称的那样明确。14即便如此,不管是否有这样的预言,居鲁士的能力一定足够引起阿斯泰厄吉兹的警惕:米底人是扎格罗什山区的霸主,对于他们来说非常警惕那些臣属们的崛起,所以当这位外孙登上波斯王位几年之后,如果继续对居鲁士坐视不管的话,他很可能会变得极具威胁。鉴于此,在公元前553年,他召集了强大的骑兵南征。尽管人数处于极大的劣势,波斯人仍然顽强地抵抗。当他们就要屈服的时候,他们的妇女都走上了战场鼓舞居鲁士和他的战士们继续战斗下去。战争持续了三年,整个扎格罗什山区都动荡不安--但却在公元前550年突然停止了。甚至众神都对此感到惊讶。他们开始在邻近国家国王们的梦中散布消息。"居鲁士以弱胜强,击退了米底人的大军,并且生擒了米底人的国王阿斯泰厄吉兹,将他作为俘虏带回了家乡。"15自从亚述帝国覆灭以来,还没有什么消息能引起这样重大的动乱。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的确,居鲁士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定、不屈不挠的竞争对手。而他的臣民们则习惯于贫困艰苦而变得坚忍不拔,从不抱怨条件困难--甚至以"茹毛饮血"闻名。而如果没有遭到背叛,拥有一个强大帝国所有资源的阿斯泰厄吉兹当然可能继续他的辉煌。而他遭到背叛的事件非常怪异,年月的流失使得重述这次事件变得愈发离奇和诡异。但事情的关键问题还是非常清楚的,部落酋长中的杰出人物,米底军队的统帅哈尔珀格斯(Harpagus)变节投向居鲁士,并在作战中带领一支叛军俘虏了阿斯泰厄吉兹。但是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叛变呢?传说认为是由于哈尔珀格斯虽然是阿斯泰厄吉兹的亲属,但是他同时和波斯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根据米底人的记载,正是哈尔珀格斯被指派杀害婴儿居鲁士,而这项任务并没有完成但他却上报自己已经做到。几年之后,当事情真相大白的时候,阿斯泰厄吉兹狂怒不已,展开了血腥的报复,他将哈尔珀格斯的儿子杀死并将其尸体剁碎,把它当做羊肉赐给这位不知情的父亲。哈尔珀格斯吞吃了自己的孩子,也吞下了凌辱的苦果,继续作为一个驯顺的臣子贵胄服侍着他的国王。或者这只是他伪装出来的样子。他的行为显然非常可信,所以当同波斯的战争爆发之后,国王仍然指派他作为自己军队的最高指挥。显然这不是明智的用人之道,或许真的如此愚蠢荒谬。 那么这样一个夸张的故事怎么会有人相信呢?也许在这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谣言般的皮影戏中有一丝真相?在阿斯泰厄吉兹和居鲁士之间的家族关系反映出波斯人和米底人之间紧密的文化和血缘纽带。这两个民族都属于雅利安人,而对于雅利安人来说只有所谓的anairya(非雅利安人),也就是外族人。因此,阿斯泰厄吉兹那些犯了思乡病的廷臣只有南望故国,才能一瞥"过去的好时光"。而波斯人和他们的米底人表亲一样,内心深处仍然是游牧民族,他们的故土上"到处都是良马,到处都是善良的人民",16这样的国家实际上只是一个由不同部落组成的联盟而已。虽然居鲁士是"安息国王",但他也声称自己的王冠是凭借人民最伟大的酋长的地位获得的--他是阿黑门尼德(Achaemenids)家族的族长,这是波斯最强部落帕萨尔加迪(Pasargadae)的统治家族。他既通晓近东宫廷中各类死板的仪式,也擅长组织不拘小节的骑手们在露天地进行聚会,他是古代城市和群山与原野的主宰,他既是波斯人未来的掌控人也是他们过去的记忆与习俗的主人,居鲁士在扮演这诸多角色时游刃有余。因此波斯极大地避免了曾经折磨米底的那种冲突:国王无法忍受民族传统的部落结构,而他的贵族们仍然坚持这种特点。米底人的部落酋长们注意到阿斯泰厄吉兹中央集权的野心而为此痛心疾首。随着时间的流逝,前面我们提到的他们的国王和居鲁士之间的对比,逐渐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几乎一定由于这种原因,促使哈尔珀格斯迈出了上述至关重要的一步。"从此,以前作为米底人奴仆的波斯人翻身成了前者的主人。"17居鲁士走入了埃克巴塔纳,收获了他隐忍、敏锐而又令人愉快的性格结出的果实。 甚至在这样一次重大的胜利之后,居鲁士的平衡政策也没有失效过。亚述的历代君王为了征服荒蛮的山峰履行自己的传统权力而头疼不已,但是经过严密的算计,宽容的居鲁士采取了更加宽大的政策。将米底贵族中的一部分人吸引到自己的阵营中的同时,他经受住将对手变成奴隶这样的诱惑。甚至对待阿斯泰厄吉兹,他也没有采用剥皮酷刑、喂野兽或者投入监狱这样的方式,而是为他提供了一份相当体面的俸禄供其安度余生。当然,埃克巴塔纳中的财富被洗劫一空,所有物品都被运回到安息,但埃克巴塔纳并没有遭受尼尼微那样的命运。居鲁士不打算摧毁这座扎格罗什山上最为险要的都市。虽然冬天严寒难耐,暴风雪封锁了山路,而夏天,当波斯的平原地区受到烈日炙烤的时候,埃克巴塔纳则是一派令人愉悦的绿色天堂,它身后的群峰依然覆盖着白雪,而高墙之外的山坡上则层层叠叠布满了果园和花园,空气明净清冽。这座城市曾经是米底王国的都城,而今它变成了居鲁士帝国在炎夏时节最有效的首都。因此米底人能够感觉到,即使不是同那些征服者们完全平起平坐,至少也是彼此联合在他们新国王统治下的一种大胆投机,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这样的投机随后被一系列振奋人心的事件证明一切才刚刚开始。像阿斯泰厄吉兹这样伟大的国王被推翻,在整个近东引起巨大的冲击。不仅将米底帝国本身,甚至连多年以来建立起的国际关系也被彻底破坏。突然间,这里看似充满了可以争夺的对象,彼此相邻的大国们还难以将波斯人看在眼中,他们开始考虑自己的开价能得到多少战利品。公元前547年,吕底亚国王克里瑟斯(Croesus)带领一支庞大的军队跨过了哈吕斯河,想试探对手。居鲁士异军突至,从扎格罗什山迅速赶来同他会面。居鲁士经过一座座曾经设有哨卡的亚述城市遗址,如今只剩下尘土飞扬的凌乱土堆沉默地见证着权力的脆弱。这样的教训对于一位雄心勃勃的人来说,既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激励,对于目前已经在战场上失去先机的居鲁士来说,仍然迫不及待地想要同克里瑟斯一决高下。当年吕底亚人和米底人遭遇的战斗并没有最后的结局;但这次,没有任何日食,战争也不会中途停止。相反,由于冬天到来,克里瑟斯撤回到自己的首都萨迪斯,他没想到居鲁士居然敢于追击自己,因为这座城池距离西边爱琴海只有三天路程--这对于米底的边界来说距离非常遥远。可是波斯人却没有退却,他们冒着严寒,兵临城下,克里瑟斯没料到敌人会出现,根本没有时间召集自己的军队,只能龟缩在城中等待敌兵散去。随后在居鲁士的攻势下,萨迪斯陷落了,克里瑟斯召集起仅有的零星部队进行了殊死抵抗。但是这是一场令人绝望的战斗,吕底亚人把全部的希望押在最后一场骑兵冲锋上--但结果只是萨迪斯陷入混乱,克里瑟斯本人受俘。在遥远的两河流域,此事被记录下来,但简练的言语几乎看不出这件事的轰动效果:"(居鲁士)击败了(吕底亚)国王,占据了他的财宝,并将自己的军队驻扎在这里。"18克里瑟斯倒台的消息在吕底亚帝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以至于据说一位神庙中的女祭司听到这个惊人消息之后居然长出了胡须。如果只是如此倒也罢了,但仅仅六年之内,波斯就从一个国小民寡、曾经落后而默默无闻的民族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的王国。 胜利不仅属于他们自己。米底骑兵装备了为冬战而准备的羊皮大衣和耐力很好的山地马匹,这已超出了坚守岗位的需要。米底人的将领也是如此。战场上哈尔珀格斯向居鲁士提出了最好的建议,他提议在吕底亚骑兵发动总攻之前,将辎重骆驼安排在波斯人战线的前锋上。居鲁士依奏下令,吕底亚人的马匹受到骆驼发散出的陌生臭味的惊吓,纷纷掉头逃窜,这场战斗也因此获胜。居鲁士受到这次胜利的激励,因此也并不奇怪他希望像以前安抚米底人一样来安抚吕底亚人,虽然这些新的臣民是anairya(非雅利安人)。克里瑟斯和阿斯泰厄吉兹一样被免予处死,他被接纳为征服者的扈从;他那些丰富的宝藏则被完好的保存在萨迪斯;甚至本地的税收也被放心地交予当地显贵管理。然而吕底亚人显然被这样的宽宏大量惊呆了,将这看作软弱的表现;居鲁士刚刚返回埃克巴塔纳,最受到他信任被委任看管此处财富的贵族就发动了叛乱。这是一次致命的误判。居鲁士将这样的行径看作最为低劣的背叛和忘恩负义,面对挑衅他以立即发动远征作为回应。新令、新兵迅速从埃克巴塔纳开出。但这次再也没有任何仁慈可言。取而代之的是得到命令的波斯人要用更为传统的绥靖手段来证明他们的统治:犁庭扫闾,叛乱的首领被处死,追随者被转为奴仆。这些都是按照波斯国王的指示完成的。 尽管居鲁士表现了自己报复的力量,但并没有放弃他帝国政策的根本。如果不再有吕底亚人,那么米底人仍是被他当做令人赞扬的新政的参与者。出于这样的安排,哈尔珀格斯这位居鲁士外国侍从中最显赫最有价值的人,被派往西部统帅帝国的军队。这个机会是即使他继续忠于阿斯泰厄吉兹也永远不会得到的,因此这位来自于扎格罗什山脉的部落酋长抵达吕底亚公开地使用了"海洋大元帅"19这样惊人的头衔。他以惊人的效率在自己的官邸开始工作,为了在"苦海"20(爱琴海)之滨的亚洲边缘尽快建立起标准,他迅速收拾了吕底亚人。沿着海岸线,这里布满了美丽而繁荣的城镇,波斯人称当地居民为亚乌那人(伊奥尼亚人)亚乌那人是伊奥尼亚(Ionia)的变体,是指称分布在近东地区的希腊人的专有名词。例见《创世记》10.2,雅弗的一个儿子名叫雅完(Javan)。希腊人将希俄斯和萨摩斯岛上的各个城邦称为伊奥尼亚,因此共计十二座城邦属于伊奥尼亚。。几百年来,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此前从希腊来的移民,伊奥尼亚人和他们隔爱琴海相望的母邦同胞们一样仍然明确坚信自己属于希腊人。他们彼此争吵不休不能形成统一的阵线,对于哈尔珀格斯来说,这样的人如同俎上之肉一样。他一座接一座地将这些城市收入囊中。的确,他的大名对很多伊奥尼亚人来说都是一种威胁,如果不想臣服于波斯人的统治,他们只能选择逃到海外,移民迁往西西里岛或者意大利半岛上。有一座城市福西亚(Phocaea)甚至迁走了全部人口,"妇女、儿童和可以带走的财产,实际上所有的东西……只给波斯人留下一座空城。"21哈尔珀格斯给伊奥尼亚人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他要到来的回忆长久以来成为一个梦魇,即使在最私密的愉快场合中也是如此: 当冬季降临,你躺在炉火边柔软的沙发上时, 四周都是美食,一边嚼着干果一边饮着美酒, 这时你一定会问: "你来自何方?告诉我你多大了? 当米底人来到的时候你的年龄是多少?"22 不,也许应注明"当波斯人来到的时候你的年龄是多少?"--这就是哈尔珀格斯给伊奥尼亚人留下的困惑印象,即使当他们已经臣服于这些新的统治者之后依然如此。甚至很久之后,当希腊人提到波斯人的时候,仍然不变地称他们为"米底人"。这种混淆一点也不令人惊奇。扎格罗什山区民族的复杂情况对于一个遥远地方的人来说的确难以弄清。这些西部海滨城市意识到自己臣服于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民族的事实意味着一个崭新而动荡的年代的来临。世界似乎突然急剧地缩小了,此前,从未有过任何一个人能将势力扩展到如此遥远的地方。但居鲁士不仅没有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反而产生了不安和焦虑。他为了吕底亚的所有这些胜利而感受到想象中潜伏在自己身后的危险带来的恐惧。从萨迪斯返回之后,他将注意力转向了东方的地平线。如果忽略了那个方位之外的事物,即使是最为智慧的征服者也会发现自己的功绩只不过建立在流沙之上。没有一个王国能够在担心游牧部落的劫掠以及如雷鸣般跨越伊朗高原的马蹄声的同时保证自己完全安全。有谁能比波斯人更了解这一点呢,因为他们自己就来自于游牧部落。 所以居鲁士亲自扑灭了吕底亚的叛乱后,就踏上和埃克巴塔纳相反的方向,沿着呼罗珊大道朝向东方进发。23这对波斯人和米底人来说一样是一次回到自身历史中的征途,朝向他们祖先传说中的故土前进,"水草丰美,宜牧牛羊",24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气魄宏大,原野辽阔,群山上可摩天。居鲁士进军到高原之上,最终将目光瞄准了兴都库什山脉(Hindu-kush),它能够越过中亚的群峰看到东方太阳升起--"这永不熄灭的、如骏马一样矫健的太阳,正是它最先身披金色盛装,攀上美丽的山顶,并从那里用慈善的目光俯瞰着雅利安人的居所"。25自从很久之前波斯人离开了这片"雅利安人的居所",这里就成了一些骄纵贵族的乐土,和他们那些住在扎格罗什山的表亲相比,这些人虽然落后但或许更加富有而笨拙,并且十分好战。一旦居鲁士成功地令这些人臣服,他们将给他带来令人敬畏的巨大人力和财富资源。这片荒芜的土地绝不会失去自身混沌的特点,他们的新主人如以往一样善变,小心地将自己扮演为本地传统的继承人,任由土著贵族继续他们喧哗的行事方法--但从此以后效忠于波斯国王。这虽然松散,但是居鲁士巧妙地掌握着方向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不仅仅是军队和黄金,还有一片缓冲地带。在这片从兴都库什山脉到咸海的巨大弧形地区中建立起许多省份,它在东北方向上为波斯提供了一道屏障,保护了波斯从前面对中亚草原来的入侵敞开的最脆弱的地区。犍陀罗(Gandhara)、大夏(Bactria)和粟特(Sogdiana):这些地方原来都是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流血之地,如今成了波斯军事力量的堡垒。 堡垒有很多条件。蛮族和开化的各族都认可居鲁士在世界遥远荒芜的边缘为自己指定的居住地。否则可能发生的事变仍然会带来一大堆麻烦事。例如米底人自己的民间传说中就保留了一个故事,他们的帝国在最为强大的时候还曾经遭到"斜眼的"塞种人(Sakas)的奴役,这些人如同他们居住的草原一样以野蛮、残忍和不可教化而著称,米底人被他们控制长达二十八年。当居鲁士后来从粟特向今天哈萨克斯坦进发的时候,发现自己面对的正是当年米底人遭遇过的同样一群魔鬼,人们很容易将这些人认出来,他们头戴高高的尖顶帽子,善于使用斧头发出警告,这是一个严重的危险信号。居鲁士俘虏了塞种人的一个首领,并用高贵的骑士风范对待他,这个首领就臣服于入侵者,塞种人为波斯国王效力,后来成为帝国军队中最残忍的力量。但是这仅仅是一个部落。在它的家乡以外有辽阔的原野,这里盗匪出没,危机四伏,其幅员之辽阔嘲弄每一个试图征服这里之人的野心--甚至是那些我们已知的最伟大的征服者。有些人说无人能说清楚这些原野延伸到何处,也没人知道他们的边际何在;那里有人身羊腿的部落;那里都是冰天雪地的蛮荒之境,那里的居民每年需要冬眠六个月时间;在这些地方以外则流淌着环绕世界的大河兰加(Rangha),这条河如同大海一样宽阔。26居鲁士在跨越景色单调的草原时,显然没有预料到要推进到这样遥远的地方;最后当他发现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之时,便在处处泥沼与蚊虫的岸边修整,并最终停止了前进。这条河就是药杀水(JaxartesRiver),河水很浅而且岛屿众多,为勇敢的人提供了天然的边界;因此居鲁士下令,依山河之险,补其不足,建造七座边镇,并将其中最大的一座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叫"昔罗波利斯"。27从此以后,这片人迹罕至的蛮荒草原就像一名奴仆一样,被打上了波斯国王的印记。 将他的身份烙印打在塞种人土地上的做法显示出帝王的双重信息。第一,药杀水之外那些好战的野蛮群体不再被允许南下侵略,而这条边界之内的居民也不必再为自身的安危而担心。居鲁士的战略总能起到威吓敌人安抚臣民的双重效果--到公元前540年,当东方的边界稳固之后,居鲁士觉得可以准备回头完成自己最后的任务了。于是他返回扎格罗什山脉,将自己掠食的目光转向每一个征服者雄心壮志的终极目标--今天伊拉克南部肥沃的平原,它从亚述延伸到波斯湾,这里从历史伊始就是众多辉煌城邦角逐的舞台。没有人能在征服这片古老的中心地带之前能被人承认为世界的霸主--这一点作为新贵的居鲁士非常了解。他还知道这里的居民不是暴君宣传控制下落后的边地愚民。相反,这些人认为波斯人才是蛮族。居鲁士善于扭转人们的先验观念,决定迎头面对这个新的挑战。他侵入敌人的疆域,却宣称要保护这里;他带领庞大的军队,却表现得仿佛如和平保护神一样。因此,所到之处无不敞开大门欢迎他的到来。 波斯的火力就是一切,这是抵抗者所能做出的惟一理智抉择。曾经有一支军队试图抵抗侵略,但已经被完全消灭;居鲁士曾经在吕底亚向世人展现过,如果他觉得这有助于实现良好愿望的话,并不反对偶尔使用残暴的手段。当然,大体上说他更喜欢按照自己高调的宣传行事。一旦建立起统治,就不再会有杀戮。刑罚也将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他的命令以一种和缓仁慈的口吻颁布。对于那些古刹星罗棋布、香烟缭绕的城市来说,居鲁士将自己表现为"正义和公正"的楷模,他"普世统治权利"来自于众神的回馈。28但到底来自于哪些神祇呢?居鲁士冷静地装作受所有人的悦纳。各界修士都寻章摘句适时地将他拥戴为自己人,各族人民也将他看作自己传统与观念的继承者--这都是他成为世界主宰的完美粉饰。他既是阿黑门尼德家族中新贵的部落酋长,也是乌尔或乌鲁克这样古老城市的庇护人--完美无缺。即使上溯到创世之初,人们也无法在历史记载中找到另一个曾经如此迅速地达到这样崇高地位的人。 但对很多人来说,即使像他这样的天才,有的事情也非常可怕甚至骇人。当居鲁士最后一次陷入战争时,他已经年届七旬,虽然仍然拥有无法满足的征服欲,却最终死在药杀水以北的地方,远离他曾经为自己的野心划定的界线。29杀死他的那个部落的女首领在得胜之后,斩下居鲁士的头颅,将它放进充满鲜血的皮酒囊,好让这个饥渴的老头得到最后的满足。居鲁士最后扮演了一个游荡在近东地区人们幻想中的幽灵,一个在夜晚永远无法餍足于人类血肉的魔鬼。在屈服于他的那些人中保留下了一个不寻常的传统。居鲁士,这个几乎震动了整个世界的人,被人们以一种几乎言过其实的颂扬加以纪念:他性格中非凡的高贵品质以及世界和平的缔造者。许多世纪之后,即使在与波斯帝国最势不两立的敌人那里,其建立者的光辉依然普照着这个帝国。"他令所有其他的君王黯然失色,无论生于他前还是自他之后者。"一位雅典人色诺芬在居鲁士死后两百年左右如是记录。"无论他征服了谁,他都会为这些人注入取悦自己的愿望,让这些人在他良好想法中感到快乐。人们都会觉得自己乐于接受他的治理而非别人的。"30这可能让人觉得的确是惊人的结论,但居鲁士确实诱使或者强迫人们相信自己成为了不同民族的主人,理解和尊重他们,并渴望赢得他们的爱戴。以前从未有帝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也从未有君王曾经表现得如此仁慈,如此克制。 这就是居鲁士的过人天才--他赢得的回报是一个超越所有梦想的主宰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