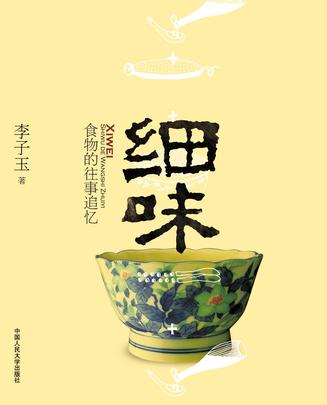八十年代末,我在美国南伊利诺伊州的州立大学读书,从香港的浸会书院中文系转读社会学系。从小就读中文学校,英文不太灵光。但我还是决心入读社会学系,为的是要多了解社会现象,以为中文系加上社会学系就可以自动助我成为作家了。结果取得了学位,仍然当不成作家。 到南伊大第一年,功课非常繁忙,每天要看的书很多,每页的英文生词都得查字典,花费很多时间。最初的一个学期,上课记不到笔记,只得向班上一位英文好的香港女孩借笔记,以强记的方式背诵答案,因为自己的英语写作能力差。有时碰上难解的句子更要请教教授,犹记得当时有位德国籍的教授 Tomas Burger,那时我因害羞而不敢向同学讨教,憋了老半天才羞怯怯地拍这教授的门;甫进门,用细如蚊子叫的声音向他打招呼,却把他的姓叫成 Professor Hamburger,我羞愧得满面通红,差一点哭出来了。他竟然愿意逐句替我解释课文,我在他的办公室足足待了一个小时。幸好这门功课最后得A-,可算没有浪费他的一番心血。 那时每天除了上课,就是读书。我和文正在香港订了婚,为了省钱就合伙租住一间套房,过着同居的生活。也是为了节省开销,每天三顿都在家吃饭,早餐很简单就解决了,午餐及晚餐也是以省繁就简的方法应付,加以我有限的厨艺,故没法做出精致的巧手菜式来。 那时我最常做的一道菜是红烧元蹄(或是猪髀肉)。我们从香港寄来一个电子瓦锅,用法简单又方便。买来元蹄肉一大块,滚水烫过后,蒜粒姜片在锅中快炒几下,放元蹄入锅中,渐次加入酱油、麻油、绍兴酒、糖、盐、及少许五香粉,清水当然是不可少的。把开关掣调校到炆煮位,煮两小时即可。这样大的一块元蹄肉,我们和着生菜或大白菜一起吃,大概可以吃三四天,在繁忙的学习生涯里,确是可以省却很多时间。 这个菜在那段日子煮得很勤,往后到芝加哥也烧过两三次,回到香港之后,似乎完全忘记了这道元蹄肉。其实并非是忘记了它,而是年纪渐渐老大,身体消化肥肉的能力越来越弱了。有一天在芝加哥检查身体,检出身内胆固醇偏高,遵医生嘱咐,以后少吃脂肪食物,我也就少吃为妙了。 现在想起一件事,对我影响甚大:我哥哥的胰脏发炎差点丧了性命,其原因是吃脂肪食物太多了。这病对我的冲击很大,我开始感到生命的脆弱,从而关心到身体的健康问题。刚好彼时在芝加哥伴读,心情颇为苦闷,又没什么重要的工作可做,情感无处寄托,一点小问题都足以令我担心得寝食难安。哥哥的健康困扰了我,所谓物伤其类,兔“病”狐悲,我对健康的关注日深,却成为日后的抑郁症,这是不自觉地慢慢转化而成的。 红烧元蹄只做了一年就很少再做,可能是我们吃厌了这个菜,但最大的原因是此菜能招贼! 事情发生在一天的上午,我和文正早上都有课,出门前我预备了一锅元蹄肉,在锅里烧着,预计午饭回家就可吃到已煮好的元蹄。谁知匆忙中忘记把窗子关上就走了。回家门锁一开,我们不约而同大呼不妙,家中电器用品全被偷走,珠宝财物被洗劫一空——包括我们的结婚戒指也不见了。事后我们估量这名贼人是目不识丁的,几百本书一本不缺;但他肯定是个饿贼——我临走前煮的元蹄肉连锅带肉都被拎走了!他一定是多天没有吃东西,桌子上的两根香蕉也不翼而飞。这个贼更有可能是东方人,因为我家的筷子和碗也都失踪了。 从此我再也不敢开着窗煮红烧元蹄,怕那人闻到香味再回头吃我的元蹄肉。我和欧梵结婚后,明知他最爱吃红烧元蹄,却只做过一次,这又是我的胆固醇惧高症作怪,倒不再怕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