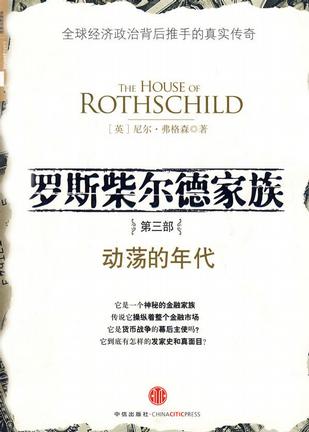列昂内尔的选举所引发的问题随着对这个可预见的结果是感兴趣还是敬而远之,把英国的政治精英们分成两派。出乎人们预料的情况是,罗素废除国会剥夺人权的提案所受到的支持不仅来自议院里他的盟友,还得到了来自两派分裂了的托利党人的支持。当他在1847年正式提出这份法案的时候,主流皮尔派保守党成员格莱德斯东和保守党领导人乔治•本丁克爵士和迪斯雷利都表示了支持。当然,迪斯雷利是对此最感兴趣的人,尽管他的动机和行动非常复杂——复杂的程度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到那时为止,迪斯雷利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相识已经接近10年了。他与这个家族有记录的最早交往是在1838年,此时,他们已经非常熟悉,足以保证当他在1842年访问巴黎时可以享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友好接待。到了1844~1845年,他和他妻子玛丽•安娜常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吃饭:1844年5月、1845年6月两次,那年夏季的晚些时候在布莱顿还有一次。1846年的时候,列昂内尔帮助迪斯雷利在法国铁路上进行投机,稍晚,又帮助迪斯雷利处理他的债务纠纷(当时的金额超过了5 000英镑)。这份友谊超出了迪斯雷利对他们金钱的欣赏,而他们也很欣赏迪斯雷利的智慧。这是迪斯雷利作为小说家最为高产的时期:1844年有《科宁斯比》和《年青一代》,1845年有《女巫》和《两个国家》,1847年有《唐克雷德》与《新十字军》。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帮助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这种认同的程度还远远不够。 大概是由于他曾经受过洗,而退教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父亲依萨克与其犹太教会闹翻,同时他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乡绅的原因,迪斯雷利一生都对犹太教充满了兴趣。他的政敌试图用他的血统来攻击他,但迪斯雷利勇敢地把别人看成是弱点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小说中,他把自己的犹太人“种族”与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相调和,有力地说明他享受着这两个世界中最好的东西。毫无疑问,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交往对他的犹太主义特征有很大的影响。列昂内尔和夏洛特是很有吸引力的一对,列昂内尔富有而又有影响力,夏洛特聪明而又美丽;但他们身上最吸引迪斯雷利的——实际上还包括他的妻子——是他们浑身上下的犹太气息。另外,对没有子嗣的迪斯雷利夫妇更具吸引力的是他们的5个子女。迪斯雷利写道(1845年6月邀请他们到格罗夫纳门观看海德公园里的游行),他们是“美妙的精灵”。 3个月后,这个家庭接待了歇斯底里的玛丽•安娜的一次奇异造访,她让自己倒在了夏洛特的怀里。在发作过后,她和迪斯雷利都进入了精疲力竭的状态(“我一直忙于校清样,出版商是那么讨厌……可怜的迪斯一直坐在那儿写了一整夜”),因此他们准备动身前往巴黎,玛丽•安娜做出的举动让夏洛特吓了一跳,玛丽•安娜宣布她希望把夏洛特6岁大的女儿埃维莉娜指定为她遗嘱里的唯一受益人: 迪斯雷利太太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我这是来告别的,我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生命是这么无常……迪斯和我可能会在火车或者轮船上丧命,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爱我的人,除了我尊敬的丈夫,这个星球上也再没有我关心的人,但是我喜欢你们这个家庭……” “……我使出浑身解数安抚我的客人。”夏洛特写道,“她在对我细数完她的细软和财产后,从她的口袋里取出一张纸,‘这是我的遗嘱,您一定得看看,把这个事告诉尊敬的男爵,而且您要替我保管好它’。” 当夏洛特轻声告诉玛丽•安娜,她“无法承受如此重大的责任”时,玛丽•安娜翻开那张纸,大声地读道:“‘万一我心爱的丈夫先我升天,我将我个人的所有财产全部留给并赠予埃维莉娜•德•罗斯柴尔德。’‘我爱犹太人,’她继续道,‘我已经把自己与您的孩子们联系在了一起,她是我的最爱,她应该也必须戴上蝴蝶(玛丽•安娜一件珠宝的名称)。’” 这份遗嘱在迪斯雷利和他妻子之间发生了“一个事件,一个非常令人不快的事件”之后,在第二天早上被退了回来。然而,这对夫妻对家庭生活的兴趣却丝毫没有任何减退的迹象。当利奥在1845年出生的时候,迪斯雷利(在写自巴黎的一封信里)表达了他的期望:“他将证明自己无愧于自己纯正和神圣的民族,也不逊于他那些漂亮的兄弟姐妹。”“我的天啊,”玛丽•安娜在见到这个孩子时惊呼道,“这个漂亮的孩子可能会是我们正在等待的未来的弥赛亚——天晓得!而你将会是最幸福的女人。” 在迪斯雷利与夏洛特的关系中,总是存在着一种失落的仰慕情愫,同时又夹杂着对他妻子玛丽•安娜难以掩藏的嫉妒。对于这种仰慕,迪斯雷利没有否认。“在我一生的奋斗过程中,”他在1867年3月对她坦白,“来自于那些我们所爱的人的关怀是一种慰藉,我对您的爱无人可敌。”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说法并非仅仅是迪斯雷利式的修辞手法。有一次,当夏洛特造访迪斯雷利家时,很显然有某件事情牵涉到了玛丽•安娜,迪斯雷利赶忙道歉: 我认为……我对给您造成的麻烦深感内疚,总体说来,昨天您要是没碰上是最好的,因为错过了睡觉的时间以及其他原因,她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因此我现在再也不在晚上见她。 她……希望将她对您的爱带给您,我也将把我的爱带给您,而且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经把我的爱给您了。 所有这一切中最奇怪的是玛丽•安娜对夏洛特有确凿证据的深厚的友情——或许是对她可能感觉到的那些嫉妒的补偿。当迪斯雷利夫人在1860年病倒的时候,“她有气无力地让我写信给您”,迪斯雷利信手在一张便条上写给夏洛特。作为回应,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匹克迪利的餐厅送病号饭。(玛丽•安娜病逝后,轮到夏洛特来嫉妒了,因为迪斯雷利“跪倒在布莱德福德夫人脚下的时间越来越多”。她做出的回应是给他送去了6大筐英国草莓、200把巨型的巴黎圣水刷,以及人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最好的斯特拉斯堡肥肝。这只是一个聪明的提醒,让他不要忘记她的资源总是要远胜那些“有钱的老妇人”)。 或许他们之间的关系中最独特的方面在于信仰模糊。按照夏洛特的回忆,迪斯雷利对待自己犹太人的根总是很矛盾。“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在1866年写道,“当我斗胆宣称,蒙蒂菲奥里家族、莫卡塔家族和林多家族的亲缘关系,路易莎•德•罗斯柴尔德夫人非常荣幸地成为他的表亲时,他居然被惊吓得茫然失措;但是连老天都搞不明白的是,不知道迪斯雷利想的是什么,尽管伦敦到处都是他的亲戚,但他对他们的存在根本毫不在意。”但当他们讨论宗教问题时,两人发现了太多的共同点。在1863年,他送给了她一本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年,法国文献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有系列著作基督教起源史。——译者注最新出版的,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的《耶稣生平》(Life of Jesus)。她觉得勒南在剔除基督神话色彩方面的尝试“很精彩”,但她对他的犹太背景的描绘持保留态度: 读起来就像是由一位热情洋溢的诗人写出来的美丽诗篇,诗人受到鼓舞去揭示真理,用满腔的柔情、无限的敬仰以及炽热的情怀来揭示它。对于那些有知识的犹太人来说,我相信他们不会对书中主要人物——这个创造了统治世界长达1 800年的基督教的伟大宗教缔造者——的处理觉得有任何新意;但很多我们的教友对于被勒南描写成这种刻板、令人厌恶的形象深感痛心。当偏见最终开始消散的时候,看到一个长期遭受迫害的民族正在忍受着那些冷静的读者和诚实的思想者将我们嘲笑为不可救药的肮脏、冷漠、狡诈,甚至是顽固、铁石心肠又小肚鸡肠的时候,更是让我们无法释怀。一个伟大的作家表现得如此公平和公正,特别是在表达他的见解方面——他的判断是如此准确、他的感情似乎是如此纯粹和高贵,不应该通过介绍如此极端的阴暗面来拔高他的伟大形象——就好像是他觉得需要通过诽谤犹太人来弥补宗教世界中从全人类利益的全部主体中最伟大、最至高无上的部分所拿掉的那部分特权。 10年以后,迪斯雷利非常感谢她送给了他一本她写的《致辞》。“我读了您写的书,感同身受而且充满了敬佩。”他写道,“弥漫在全书中的那种柔情,以及那些虔诚和令人振作的情感,肯定能触动所有信徒的心灵。昨天晚上(在安息日的圣洁气氛中)我有幸朗读了一篇,它表现出来的虔诚及深远意境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听众……” 迪斯雷利所有的小说都应该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在《科宁斯比》中,希东尼亚的性格特点按照布莱克爵士的说法,是列昂内尔和迪斯雷利本人的交融。说得更准确点,他具备了列昂内尔的背景、专业技能、宗教、性情,甚至也许是外貌(“面色苍白,眉毛浓密,深邃的眼眸里写满了睿智”),但他的政治理念和哲学观点则是迪斯雷利的。因此,他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在半岛战争中发了财,然后 “决定移民到英格兰,经过几年的努力,形成了很多商业网络。他在巴黎和会后到达这里,随身带来的是他的巨额资本。他把所有的资产押在了滑铁卢贷款上,这个举动使他变成了欧洲最大的资本家”。战争结束后,他和他的兄弟们将他们的钱借给了欧洲国家——“法国想要一些,奥地利更多一些,普鲁士要一小点,俄罗斯要几百万”——他“成为了世界金融市场的主宰和领袖”。年轻时候的希东尼亚具备了一个银行家的所有技能:他是一位非常有造诣的数学家,而且“完全掌握了主要的欧洲语言”,这些技能通过到德国、巴黎和那不勒斯的旅行而得以磨炼。他冷静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对这种品质的描写花了很大的篇幅(例如“他对感性的东西总是缩手缩脚,而且常常用一些尖刻的话语来搪塞”)。我们甚至读到了“他对室外体育运动的热爱……是他的精力的安全阀”。还有一段细节的描写,而这些细节只可能出现在巴黎的某一家罗斯柴尔德酒店。很有意思的是,希东尼亚也是小说主人公的情敌:主人公错误地怀疑他深爱的艾迪丝是希东尼亚追求的目标,尽管最后披露出来的结局是冷血的希东尼亚自己本身是另外的人所暗恋的目标。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科宁斯比》中最令人玩味的段落是那些有关希东尼亚信仰的内容。关于这个问题,前面所说的是他信奉 “使徒们在跟随他们的主人之前所传扬的信仰”,而在后面所说的是他“对伟大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典表现出了的忠贞,与号声一直响彻西奈半岛的时候别无二致”。他“为自己的血统感到骄傲,对自己族人的未来充满信心”。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希东尼亚与迪斯雷利的相像程度远甚于列昂内尔,因为他说他出生于西班牙的马拉诺——西班牙系的犹太人,他们表面上改信基督教,而暗地依然信奉原来的宗教——而且迪斯雷利喜欢幻想自己的家族是西班牙系的犹太人。但余下的绝大部分很显然来自罗斯柴尔德的启发。因此,年轻时候的希东尼亚被“关在了?学和学校的大门之外,这些大学和学校对于学习以及先人的事业来说缺乏古代哲学的最初知识”。另外,“他的信仰使他不可能追求成为一个公民的理想”。然而,“在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想法可以诱使他伤害自己种族的纯洁,因为他一直为此而备感自豪”而去与外族通婚。只有当希东尼亚阐述对自己种族的看法时,迪斯雷利才接替了列昂内尔: 希伯来人是一个没有被混杂的种族……组织没有被混杂的种族是大自然的贵族……在广泛的旅行中,希东尼亚拜访而且检视了整个世界上的希伯来人社区。他发现,总体上看,较下等的阶层情况比较差,而上层人士沉浸在对肮脏事物的追求中;但他发现知识的发展没有受到破坏,这给了他希望。他被说服相信组织能经受住迫害的考验。当他反省他们所经受的那些磨难的时候,发现种族居然能够幸存下来,这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管过了多少个世纪,遭受了多少个世纪的谪贬,犹太人的思想对欧洲事务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不用提他们的法律,这些法律你们还在遵守;不说他们的文学,这些文学滋润着你们的思想;我只说说活生生的希伯来人的才智。 然而,就算在这里,罗斯柴尔德的影响也是清晰可见的。当迪斯雷利想办法说明他关于犹太人影响力程度的观点时,他非同一般地直接取材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最近的历史,他通过希东尼亚的口说: 我刚才告诉你说我明天准备去金融城里,因为我一直遵守这样的规矩,当国家事务还在考虑的过程当中时,我会积极介入。否则的话,我从不干预。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很多战争与和平,但是我从来不会惊慌失措,除非有人通知我,统治者想要更多的财富…… 返回到几年以前,俄国向我们提出过要求。现在圣彼得堡朝廷和我们家族之间已经没有友谊可言。他们有荷兰的关系,这些关系基本上可以为他们提供这些服务。我们对波兰希伯来人这个人口众多,但遭受的苦难和屈辱也是所有部族中最多的民族的支持举动,对于沙皇来说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是与罗曼诺夫家族的关系出现了好的转机。我因此决定亲自去一趟圣彼得堡。抵达后,我与俄罗斯财政部长康可林伯爵举行了一次会谈;我见到的是一位立陶宛犹太人的儿子。我们所讨论的贷款与西班牙的事务有关,我决定从俄罗斯到西班牙去着手解决。我与西班牙部长塞诺尔•门迪萨伯尔(Senor Mendizable)原文如此。一到就马上有了一名听众,我见到的是一位像我一样属于新教教徒的阿拉贡犹太人的儿子。在马德里做完这一切之后,我直奔巴黎,拜会法国国会的议长,我见到的是一位法国犹太人的儿子(据推测是苏尔特)。 ……因此,您看,我亲爱的科宁斯比,真正主宰这个世界的那些人士与那些不了解实际幕后真相的人所想象的完全不是一伙人。 撇开迪斯雷利认为所有这些显赫人物都是像他们一样的犹太人的臆想不谈,一个确凿无误的事实是这段描写的灵感来自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事迹。 他还明确提及犹太人在政治上被“当成平等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而列入了同样的阶层,随时准备支持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和财产的政策,而不是驯服地在一个试图降低他的人格的制度下苟延残喘。托利党人在关键的时刻失去了一场重要的选举,出来投票反对他们的正是犹太人……然而犹太人科宁斯比从本质上说是托利党人。托利主义事实上只是抄袭了那些把欧洲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强大的势力”。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汉娜喜欢这本书。正像她在写给夏洛特的信中说的:“经过对希东尼亚身上所具有的民族高尚品质的认真研究,经过使用很多支持他们解放的论述,他很聪明地描写了众多我们似曾相识的事件,人物的刻画也很到位……我已经给他写了张便条,表达我们对他的精神产品的赞赏。” 如果《科宁斯比》暗藏着对列昂内尔的歌颂,那么《唐克雷德》(Tancred)就是在歌颂他的妻子。对伦敦景物的描写再一次充满着对罗斯柴尔德的隐喻。我们参观了一次“西昆大院”,还去了希东尼亚豪华装修的房子。另外,还有一个明确的影射是希东尼亚为获得一条被称为“伟大北方”的法国铁路所做的努力。再一次,希东尼亚成了迪斯雷利理论的代言人——这个理论现在被用来重新定义基督教本质上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犹太教的发展: 我相信(希东尼亚宣称)上帝在何烈山对摩西说过,而且你们相信他以耶稣的身躯在卡瓦利山上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至少在世俗的观念上看,两者都是以色列的子孙,他们用希伯来话对希伯来人讲。先知只有希伯来人,使徒也只有希伯来人。亚洲现在已经消失的众多教堂由一位土生土长的希伯来人建立;罗马的据说要与世长存,而且现在改为信奉摩西和基督的教义的教堂……也是由一位土生土长的希伯来人建立起来的。 然而,是埃娃这个人物按照这些线索发表了最勇敢的宣言。作为一位叙利亚犹太人的公主,表面上看她的身上很难找到夏洛特的影子;然而,对她的外貌的描述显示她给迪斯雷利提供了某些模型。同样,尽管夏洛特的观点似乎不大可能带有埃娃的影子,但我们也无法排除这一点。比如,她具有罗斯柴尔德式的对异族通婚和变更信仰的深深的厌恶。“希伯来人从来没有与他的征服者融合,”她大声地说道,“不,我永远也不会成为基督徒!”相似的,迪斯雷利所喜爱的主题——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同本原——也在她的书信中有所表达。“你是那些崇拜犹太女人的法兰克人中的一员吗?”埃娃第一次(在圣地的一片绿洲中)碰到唐克雷德时问道,“或者是那些辱骂她的人中的一员……?”她提醒他,耶稣“是一位伟大的人,但他是一名犹太人,而你崇拜他。”因此“基督教界一半的人崇拜一位犹太女人,另一半崇拜一位犹太人”。埃娃用另一个罗斯柴尔德式的句子询问唐克雷德: “欧洲最伟大的城市是哪一座?” “毫无疑问,我的祖国的首都伦敦。” “那里最有名望的人是多么富有,告诉我,他是基督徒吗?” “我相信他是一位跟您有着共同种族和信仰的人。” “那么,巴黎呢?谁是巴黎最富有的人?” “我想是伦敦最富有的人的兄弟。” “我对维也纳非常熟悉,”这位女士说,脸上带着微笑,“恺撒给我们的同胞封了帝国的爵位,因为,公正地说,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帝国用不了一个星期就会分崩离析。” 迪斯雷利没有考虑夏洛特的地方是他设计好的(对于他同时代的人来说显得很过分)辩论,说在“基督受难时提供牺牲和祭礼”方面,犹太人“完成了上帝仁慈的意愿”,而且“拯救了全人类”。她也没有接受他的说法(通过女巫的口):“基督教是完善后的犹太教,或者什么也不是……要是没有基督教,犹太教也就不完整。” 在迪斯雷利的小说中提出的这些争论,表明了迪斯雷利对罗素的限制权利法案的态度。他在第一次辩论前两周,告诉列昂内尔、安东尼以及他们的妻子,他准备好了要支持这个法案,但是对托利派的条款,“我们必须主张我们的权利,不是为了什么特权,而是为了良心的解放”。这使得围坐桌前的自由派人士不知所措:路易莎描写迪斯雷利用“他那奇特的唐克雷德似的条理”侃侃而谈,而且 “怀疑他是否有勇气以同样的方式对议会这样说”。他确实说了。夏洛特起初对此相当热心。“没有谁可以,”她在1848年3月告诉德莱恩,“在用伟大的机智……权利、智慧或创造性来表达自己的方面超过我们的朋友迪斯雷利。”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3部——盟友的支持
书名: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3部
作者: [英] 尼尔·弗格森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动荡的年代
译者: 何正云
出版年: 2009-9
页数: 361
定价: 45.00元
丛书: 中信金融史
ISBN: 9787508616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