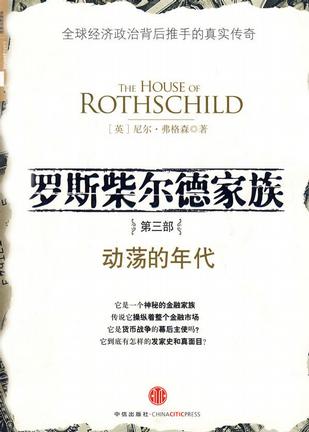如果不提列昂内尔为确保犹太人在国会下院中的席位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话,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历史是不可能完整的。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把这个具体的问题与英国宪政进程中的“辉格党人”历史截然割离开来。犹太人被选举为下院国会议员的宪法障碍——就职誓词里包含有这样的句子“按照一个基督徒的诚挚信念”——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50年代所面对的几个重大挑战之一。1707年通过的一个法案要求投票人也发同样的誓言,但这不是严格强制执行的。对于他们具有类似重要意义的另一个障碍,是牛津大学的入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 另外,还有一些社会机构,尽管之前并没有正式排挤犹太人,但从来就没有允许过犹太人介入。能够进入到这些机构,其重要性与正式推翻这些法律歧视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按照英国19世纪时的法律,下院席位本身的价值有限;地区性的政治势力基本上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有些方面甚至是能够进入国会陈述的先决条件。另外,以城市选民为基础的地方势力与植根于乡村选民的地方势力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差异。因为很多关键性的政治决策并不是在于威斯特敏斯特,而在于“乡村”——那些贵族的乡村别墅所形成的复杂圈子,这些贵族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都会在这些地方度过。就算是在城里,国会也不是主要的政治论坛:那些没有成为一个或多个分布在匹克迪利大街和帕玛街的伦敦俱乐部会员的国会议员,政治生涯不会长久。当然,获得进入下院的资格并不会为犹太人自动打开进入上院的大门。 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想要推进他们进入这些英国政府机构的步伐?那种认为他们希望借以增加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以便使他们对政府的杠杆作用最大化的功能性解释根本说不通。可以肯定的是,很多非犹太人城市平民家族在这一时期出现在了下院(比较知名的有巴林)。到19世纪4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城市里最优秀的私人银行;尽管在内森死后,他们与英格兰银行的关系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但人们没有理由怀疑,当出现英国政府需要借钱的这种难得一遇的情况时,它会很自然地想到纽科特。另外,就在他们得到了进入下院的机会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没有使用过它所带来的便利——最多也只是把下院作为辩解的场所。我们认为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由于受到了母亲的影响,列昂内尔希望赢得的是一种犹太人被剥夺了的根本性的权利。他在欧洲大陆上的亲属一直没有停止为他确保进入国会所做的努力加油打气:对詹姆斯来说,他的侄子是在代表所有的犹太人打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战争,一场继续了梅耶•A•罗斯柴尔德40年前在法兰克福所进行的战争。也就是说,列昂内尔在追求自由的现实意义,尽管当时大多数政治家(包括约翰•罗素爵士)更倾向于给他贴上辉格党人的标签。促使他和他的兄弟们远离托利党人的原因不只是“犹太人问题”,还包括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的更重要的原因——自由贸易,在托利党1846年反抗皮尔的斗争中逐渐发现了自由党的这个企图。 在1848年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矛盾:罗斯柴尔德家族正被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者骂成是反动派的支持者的时候,他们正在英国领导着一场典型的争取法律平等的自由战争。总的来说,犹太人的解放是法兰克福议会的一项成果,尽管随后在1852年,又在法兰克福被废除。就连贝蒂这种坚定的反对革命的奥尔良派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我们犹太人不应该……抱怨这个伟大的运动以及对利益的重新分配。每一个地方的解放都打碎了中世纪的枷锁,把人权和平等的权利还给了那些盲从、浮躁的流氓无产者。我们应该对此为自己举杯庆贺……” 然而,对此我们也还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首先,在革命运动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反犹太人的元素;事实上,针对犹太人的暴力现象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1848~1849年革命最反感的地方。第二,在某些方面看,实际的情况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被限制在了英国犹太人社区里。与其他犹太人精英家族——比较有名的是戴维•萨洛蒙——之间的竞争毫无疑问是一个很强的动力。事实上,对于大多数生活在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情况可能更严重)的贫穷犹太人来说,能在国会露脸就与能够到剑桥上学一样稀罕。在这些为犹太人权利所做的集体抗争的所有说法中,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某种程度上看一直坚持着他们作为一个家族的利益——具体来说,就是他们希望成为犹太人“皇族”。 根据随后所发生的事件,特别要提到的是在1839年《犹太人综合日报》发起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无情抨击,指责他们破坏了犹太人解放的进程: 我们很伤心地看到德国出现的排斥犹太人的态度,这种情况在自由战争期间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现在却随着?斯柴尔德家族企业的发展而不断恶化;而且后者的巨额财富以及他们的合伙企业已经对犹太人的奋斗目标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以至于前者的增长导致了后者更为严重的恶化……我们必须将犹太人的奋斗目标与罗斯柴尔德的家族企业及其合作伙伴彻彻底底地划清界限。 当时的确出现了这个家族对更广泛意义上的欧洲犹太人利益关注不够的情况。例如,最先为犹太人在英国的政治权利赢得胜利的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而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伦敦与威斯特敏斯特银行的戴维•萨洛蒙,他在1835年当选为伦敦金融城行政长官,为英国的犹太人在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中取得了早期的胜利。在选举的过程中,他和他的辉格党支持者共同努力,最终使他们提出的废除要求当选行政长官签署有“以一个真正基督徒信念”等字句的声明条款的提案获得了通过。不是罗斯柴尔德而是费朗西斯•亨利•戈尔德施密特,成为了第一个被律师行业接受的犹太人。同样,不是罗斯柴尔德而是他们的一位名叫摩西•蒙蒂菲奥里的女婿,被授予了骑士称号并被封为男爵,因此,正如詹姆斯所说,“提升了犹太人在英国地位”的不是罗斯柴尔德,而是伊萨克•莱恩•戈尔德施密特领导的犹太人争取公民权利及基本人权协会。 然而在1840年的大马士革事件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有关犹太人解放的问题上改变了自己的立场,首开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应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力,改善欧洲大陆那些对犹太人不很宽容的国家的犹太人地位的先河。在1842年,詹姆斯去拜见基佐时“对波兰犹太人的情况表示关切”,而安瑟尔姆正在协调各种媒体反对当时普鲁士提出的新的反犹太人规定。在1844年,由尼古拉一世提出的进一步减少犹太人聚居区的“令人作呕”的措施,以及将俄国的犹太人学校和社区直接置于政府控制的计划,促使列昂内尔在沙皇到访伦敦前频繁拜访阿伯丁爵士和皮尔。当蒙蒂菲奥里准备到俄罗斯去抗议政府对犹太人的不公平对待时,列昂内尔再次去拜见皮尔,请求为他去见内斯尔罗德伯爵写封介绍信。按照同样的脉络,我们看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怎样利用1848~1849年的罗马政治危机,迫使教皇对梵蒂冈城里的犹太人做出了让步。 就是在英国这样一个以宗教刻板闻名的国家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进行了为争取犹太人权利而进行的最为著名的斗争,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期间英国犹太人的地位在很多方面看都是不平常的,按中欧的标准看,这说明那里的犹太人社区规模非常小。生活在不列颠群岛的犹太人总人数在1828年的时候是27 000人;32年后(经过几十年空前的全国性的人口高速增长后),犹太人的总数也只是40 000人——大约占总人口的02%,其中半数生活在伦敦。在欧洲大陆,当时对待天主教的态度(特别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已有所改变,而对犹太人的敌视已经听不到了。但是在法律上,尽管大多已经形同虚设,但仍然存在各种权利方面的限制,包括禁止犹太人拥有地产和捐赠学校。最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很多的公共机构里——其中最关键的是国会——都要求按基督教徒的方式起誓。废除这个誓言成为了罗斯柴尔德在此期间政治活动的最主要目标。 在妻子汉娜的影响下,内森在1829~1830年《天主教解放法案》成功通过后,提出了犹太人的政治权利问题。罗斯柴尔德对托利党的彻底失望可以上溯到这个时期,因为很明显的是辉格党人更有可能支持犹太人获得相应的权利。这种政治调整在内森死后也一直在继续,其直接表现形式为罗伯特•格兰特在下院面对托利党人的强烈反对,提出了一系列的解放法案。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引起众多研究者重视的记录显示,纳特在1841年为那些当选为地区性政府议员的犹太人争取采用萨洛蒙当选伦敦金融城行政长官时使用的经过修改的誓词的运动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只可惜运动没有取得成功。托利党人在参议院对这个议案的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此非常在意——对改善与这一方的关系没有任何作用。在保守党赢得1841年选举后的第一时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赫里斯就警告新上任的内政大臣亨利•古尔本,他可能得面对金融城里“犹太人和经纪人”的反对: 你应该时刻牢记,所谓的贵族对你的态度不会像过去那么友善。琼斯•劳埃德、萨姆•格尼和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些人在金融城选举中的倾向,表明他们对保守党没有好感。但他们不会太感情用事,去为自己的利益设置障碍,尽管他们永远不会原谅否决了为犹太人当选下院议员扫清障碍的提案。那些资本市场的巨鳄比其他领域的任何人对财政手段的支持或是阻碍都更有力量,就算那些人的资本比他们的还大也无济于事。 一封来自于一名当时的积极分子的信证实了梅耶确实参与到了金融城里的选战,他组织人为自由党投票。很重要的一点是梅耶在1841年的时候被选为了布鲁克斯俱乐部的理事。一直到了1852年,他的弟弟安东尼也成为了一名理事。兄弟俩同时还是另外一家公开的政治改革俱乐部成员。同样的,在1852年的时候,阿尔方索成为了一家高级赛马俱乐部的会员,同时还是团结之家(Cercle de IUnian)的成员。 当皮尔要求威灵顿为支持他的政府擂鼓助威的时候,这位公爵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悲观。他警告皮尔:“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政治目标,特别是老夫人(汉娜)和列昂内尔先生。他们一直都渴望着得到对犹太人政治权利诉求的支持。”尽管他“现在比在伦敦的时候更像是一个托利党人”, 纳特强调说他对皮尔的支持是在严格的条件基础上的:“我相信他对我们可怜的犹太人是有同情倾向的,如果他能还给我们相应的权利,他就会得到我的支持。”对于纳特来说,使罗斯柴尔德家族疏远了保守主义的原因,仅仅只是出于犹太人利益的考虑。就像他在1842年的时候,用半真半假的口吻写道: 你们应该知道,尽管我在英格兰是一名坚定的辉格党人,在这里又是狂热的保守主义者,但我认为如果那不是从身体的某个部位移除一小部分,而且也不是比利(安东尼)一直认为的最具重要性的那一部分,如果它使我们不能行使那些根本不了解我们艰难处境的那些人同样的政治权利和基本人权的话,我想你们应该也得采用后面的那种思维方式。 尽管外表看起来总体上更像是自由党人,但安东尼很乐意看到皮尔与他的党派在下院遭遇到麻烦,他认为——看起来似乎是正确的——这可能会使他“向自由理念的方向上转变一点,如果罗伯特爵士能为可怜的犹太人做点什么的话,我就信任他”。至于列昂内尔,他在1843年10月的城市补选中毫不犹疑地支持自由党候选人詹姆斯•帕蒂森,为了投票,他竟然号召犹太人选民们打破安息日的规矩。这些选票对选举的最终结果是决定性的,因为帕蒂森仅以非常微弱的优势击败了他的托利党人对手——也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对手托马斯•巴林。 然而,列昂内尔对学戴维•萨洛蒙的样子直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一直表现得迟疑不决。对他的这种迟疑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纯粹行为上的问题:政治可能占用掉一个像N•M•罗斯柴尔德公司这样如此规模宏大的高级银行的合伙人的宝贵时间。或许列昂内尔同意詹姆斯的观点——这个观点早在1816年的时就提出来了——“一旦一个商人参与了太多的公共事务,他很难再继续他的银行业务”。另一方面,来自家庭成员的压力——包括詹姆斯——要求他做些工作来提高家族成员在英国的地位,也是相当大的。詹姆斯对政治活动的概念还停留在19世纪20年代那些已经过时的经验里,当时,他和他的哥哥们通过迎合与他们有业务往来的各个地区的封建领主而精神抖擞地去领受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勋章。 他试图在1838年鼓励他在英国的侄子去做同样的努力,他告诫列昂内尔说: 我已经与比利时国王进行了长谈,他向我们承诺同意给英格兰女皇写封信,他还安排他的妻子写信给他们,要求你应该应邀参加所有的舞会……国王给四兄弟下了一道谕旨……如果你,我亲爱的侄子,喜欢这些绶带,那么我保证下次你就是受勋的人,只要条件允许,尽管在英国并不佩戴这些东西。 不太过时的是安瑟尔姆 “在一两年之内能够来为你们中的一个人庆贺坐上了国会的席位,并聆听你们的精彩演讲”的期望。当伊萨克•莱恩•戈尔德施密特在1841年成为第一位犹太人准男爵时,安东尼从巴黎写来的信上说:“我已经喜欢上了列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爵士,他是可靠的。”类似的,当萨洛蒙在1843年被授予维也纳“荣誉市民”时,安东尼明确地希望这件事能“在古老的英格兰产生反响”。 压力在1845年时急剧加大,因为戴维•萨洛蒙又得到了很重要的一分。在赢得了泊特苏肯市参议院的城市选举后,萨洛蒙面临着“以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念”的誓词问题。在他拒绝起这个誓后,阿尔德门法庭宣布他的当选无效。萨洛蒙向皮尔抱怨,与安东尼所预测的一样,皮尔对犹太人给予了更多的同情,他通知大法官林德赫斯特起草一个法案,废除了所有遗留下来的影响犹太人权利的地方性歧视性规定。该法案于1845年7月31日生效。同年,禁止犹太人拥有不动产的老法律也取消了。列昂内尔事实上在确保这份议案的通过方面也很尽力,他作为由仲裁委员会派出的5人小组的成员,为这件事去游说皮尔。但萨洛蒙获得的荣誉却引发了列昂内尔那些充满竞争精神的亲戚们的不满。“我本来应该很高兴看到您成为伦敦的勋爵,而且是代表金融城的国会议员。”列昂内尔的兄弟纳特写道,“你应该去游说东印度公司,我亲爱的列昂内尔。”一年后,纳特还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内容:“我们的法国老顽固……全都在说你不久就会进入下院,而且你现在正在做着准备。”当萨洛蒙在获胜后不久访问巴黎时,汉娜很冷淡。她在给夏洛特信中说:“我们应该允许他去享受(这种出于良好动机的)成功所带来的满足感,我们自己应该全心全意地参加,满怀着美好的意愿,这是我们真心希望和相信会对我们所属的群体带来益处的意愿,从这个角度看,我不怀疑个人的荣誉和影响将会受到适当的重视。”萨洛蒙再次当选为市议员,时间是1847年12月。在1855年的时候,他继任伦敦市长勋爵。摩西•蒙蒂菲奥里在1846年获得的准男爵爵位使安东尼满心希望“当辉格党人来到的时候……他们会想到应该给你一些什么荣誉”。皮尔的政府一倒台,纳特立刻就敦促他的兄弟“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或者明确地声明你代表金融城”,建议他“约一些聪明的朋友过来,在晚上的聚会一个小时左右,一起读一些东西,对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能更多些把握”。 敦促列昂内尔在政治上更积极一些的不只是他自己的家族。1841年,爱尔兰领导人丹尼尔•奥康奈尔的一个政治协会邀请他“作为贵民族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代表”,出席一个公共集会(在安客客栈),他提议讨论“犹太人的政治地位”。两年后,基于他自己希望参与伦敦市大选的假设,有人主动提出为他助选。 列昂内尔仍然很勉强。当其他人——其中包括他的弟弟梅耶,他在2月份时当上了白金汉郡的高级行政长官他马上在怀特•哈特酒店在摆了一个星期的盛宴,由法国厨师按照以他的乡下邻居的饭量计算的需求临时制作菜品。当地的报纸抄录了菜谱,以崇敬的口吻称赞“所上菜品的味道已经到了极致”。——争先恐后地涌入萨洛蒙打开的这个缺口的时候,列昂内尔却一事无成。甚至在新任的首相约翰•罗素勋爵授予他准男爵荣誉的时候,他还很固执地拒绝接受,这让他的亲戚非常意外。他是罗素提交给女王的三人名单中的一位:按照女王的日记,另外的人是弗格森上校,还有一人,“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说明维多利亚对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在心。实际上,这个人是弗雷德里克•居里,孟加拉政府的秘书。列昂内尔可能觉得不值得为皇室的这种小恩小惠太多的精神。列昂内尔为他这样做所给出的理由充分证明了他具有意气用事的性格特点:他不情愿接受已经授予过另外两个犹太人的荣誉,如果不能获得贵族的身份,任何称号都不会让他满意。阿尔伯特王子在报告中说他这样问:“没有更高点的荣誉授予我吗?”这种率直比较符合他父亲的口味,但是他的母亲汉娜生气了: 我认为拒绝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好处,正如你那位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朋友(据推测应该是罗素)所说的,她还能授予你什么更好的?目前还不可能不宣誓就直接给你封爵,而宣这个誓恐怕你也不会愿意。从王室得到的个人荣耀应该珍惜,它可能带来其他的利益,如果拒绝它则可能让人恼怒——而且你接受它也并不意味着你放弃了你本来的地位。这可能会光耀你的门庭。之前对其他两位绅士的封赏我想跟你这次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会使授予你的荣耀失去任何光芒——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请原谅我的直率。 他兄弟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接受这个封赏,面对现在的局面他们全都大惑不解。纳特用轻松的笔触写道:“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接受英国的准男爵爵位,这比做德国的男爵好多了——老比利认为安东尼爵士听起来非常悦耳,就算你自己不想要,你也应该为了他而接受它——我们所有人都得到了非常漂亮的名字,门特摩尔的梅耶爵士这个称号甚至闪耀在一场罗曼史里。” 詹姆斯也加入进来了: 我祝福你,我亲爱的列昂内尔,你是如此幸运,尊贵的女王竟然这样眷顾你,真是谢天谢地。你一定得小心,你的阿尔伯特王子说不定会嫉妒你。因此,我要敦促你接受它,因为我们从来都不应该拒绝这样的荣耀,而且任何人也不应该坐失这样的机会。以前我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然而现在已经没有可能了。 但列昂内尔依然不为所动。最后,打破这个僵局的唯一办法是由安东尼来接受了这个封号。不同寻常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规定,如果安东尼没有男性子嗣,则这个封号将传给列昂内尔的长子。甚至他的最终让步——他终于同意以自由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1847年的大选——也都是在“犹犹豫豫”中做出的。 列昂内尔参加国会竞选的决定——他在1847年6月29日被自由党伦敦注册委员会接受为候选人——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历史上是一个分水岭。他这个决定所导致的结果是,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从此与争取犹太人政治权利的运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他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选战和国会论战中。为什么这个公众人物中最勉强的一位在完全可以轻易地将这个战场留给萨洛蒙——或者也可以让给梅耶(他不遵从他长兄的意愿正在为海斯做同样的事)时,会这样投入?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来自家庭的压力最终使他无法抗拒。第二种可能性是说服他参选的不是他的亲属,而是约翰•罗素爵士,他自己是在任的金融城下院议员,他希望确保自己来自犹太人的选票。第三种可能性是列昂内尔并不希望能胜出,只是以一个“著名的新闻事件”的形式收场,做出一个象征性的姿态。至少有一名与他同时代的人认为他会失败,而且他只是被辉格党人设计,拖进来为“他们承担他们所有的开销”。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的犹太人候选人无一例外地落选了: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角逐,要是托利党人不分裂,那么辉格党和改革派就只会在下院取得简单多数。 维多利亚时期,伦敦市复杂的政治选情使人们对胜利丧失了信心。向东远至哈姆雷特塔的选区是比较大的一个(1847年投出了接近50 000张选票),有4个下院议员席位。这一次,总共有9位候选人——自由党人4名,皮尔派保守党人1名,保守党人3名,自由候选人1名,竞争非常激烈,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举行了大约12场公众聚会。列昂内尔的参选纲领给人的第一印象并没有什么特别:除了显而易见的“信仰自由”的宗教纲领外,他宣布他支持自由贸易。很明显,他并没有遵从纳特的建议“走得比约翰爵士稍远一点”并“尽量地朝自由的方向走”。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他所采取的立场甚至有可能伤害到他自己:他提倡降低烟草和茶叶的进口税,推行财产税,这种立场广受没有投票权的穷人欢迎,但很难想象能在有钱人的选举中胜出。尽管得到了一位名叫劳齐的富有远见的天主教牧师的明确支持——而且看起来列昂内尔接受了他的支持——但列昂内尔宣布他本人反对增加给梅努斯天主教学院的捐款(尽管他回避了政府对教会学校资助这个更为广泛的原则问题)。犹太人的选票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重要:当时还没有太多的犹太人获得投票的资格,而且去登记投票的人也不多。列昂内尔得到了至少一个犹太人保守团体的支持而且得到了他母亲的保证,“犹太人……将会组织起来,身着盛装去为你投票,”皮尔派保守党马斯特曼尽管宣称反对犹太人的解放,但他也在设法保证选举的顺利进行。 从另一方面看,列昂内尔具有两种优势。在伦敦,报纸所起的作用要比在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大很多,而他与新闻界人士的联系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可以肯定,当时犹太人出版事业尚在襁褓之中。1841年,他与其他人一起投资了雅各布•富兰克林的《雅各布之声》,之后不久改版为《犹太新闻》(Jewish Chronicle)。但列昂内尔对《时报》29岁的编辑约翰•萨杜•德兰来说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赞助人,而约翰•萨杜•德兰则成功地为他起草了他的竞选演讲。站在德兰的角度,他相信是他保证了列昂内尔的胜利:他发现结果公布后,夏洛特“处于一种欣喜若狂的兴奋及满心感激的状态之中”,而他被纳特和安东尼铺天盖地的感谢所淹没。《经济学人》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对犹太人的解放持反对态度的人,只是通过站在他们立场上的记者进行辩论。历史学家J•A•弗劳德回忆当他们站在匹克迪利148号前时,托马斯•卡莱尔的感慨: 我并不是说我希望约翰王再回来,但是如果你要问我用哪种方式对待这些人更接近全能的上帝的意愿的话——是为他们建立像这样的宫殿,还是带给他们钳子——我选择钳子……“阁下,现在政府需要你与你的金融机构所聚敛的数百万英镑中的一部分,你不给?很好”——说话的人用他的手腕紧一下旋钮——“现在给了吗?”——再紧一下,一直到拿光这几百万元。 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卡莱尔声称,如果他写一本支持废除限制人身权利的小册子的话,列昂内尔就会给他一笔很慷慨的润笔费。卡莱尔大概是这样回复他的:“这不大可能……我也发现我无法想象为什么他和他的朋友们应该正在等待着希洛,到来的时候,还要寻求在外邦人的立法机构中的席位。”他在给下院议员蒙克顿•米尔尼斯的信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犹太人很坏,而一个假犹太人、一个骗子犹太人又怎么样?而且,不管他所有的思想、行动和努力的方向如何,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又怎么可能企图成为一名参议员,尤其是作为破落的巴勒斯坦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公民?”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卡莱尔正处于与亚历山大•巴林的妻子哈蕾•阿西布坦夫人的三角恋中。不过,卡莱尔没有把对列昂内尔的抵制公开化,并没有像《先驱晨报》那样称列昂内尔为“外国人”,也没有像一位托利党候选人那样说列昂内尔的最适合的地方是“作为犹太的王子之一,在犹太的王国”。卡莱尔的态度明显地站到了萨凯雷的对立面,萨凯雷在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交往之后,经历了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转变过程。具体来说,他表现出了对安东尼的妻子路易莎的好感,他为在1848年时对她的攻击做了道歉。他在1850年2月参加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宴会(发现这家的女人“都很不错”),在1856~1857年间,与路易莎偶尔有友好的书信来往。她出现在《潘登尼斯》上的表象是“一位犹太女士……腿上坐着一个孩子,她面对孩子的脸上闪耀着甜美的天使般的光芒,似乎是一种圣洁的光辉环绕着两人。我承认,我应该会跪倒在她的面前”。 对卡莱尔说法的一种回应,通过列昂内尔所拥有的第二种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优势财力表现出来。根据辉格党战争部部长格雷爵士的说法,他“毫不掩饰他做出的使用金钱来帮助选举的决定”。 纳特在随后从巴黎给他写来的信中,说明他的哥哥确实“付出了……很大的金额”。最后,这些付出改变了选举的天平。列昂内尔在投票中获得了6 792票,位列第三;其他几位分别是罗素7 137票,帕蒂森7 030票,马斯特曼6 772票。他以3票之差击败了另一位自由党候选人拉朋特。他的天主教代理人劳齐相信,是他在那一天拯救了列昂内尔,而他支持列昂内尔的动机则是赤裸裸的唯利是图。劳齐的信很值得一读,它散发着那段时期特有的政治气息:“坦率地说”——我完全同意大家都在讲的,也就是,您,尊敬的男爵,得到了天主教徒的报答,他们对您正义理想的认同决定了您的胜利……对您来讲,这是什么样的远见卓识啊,两个月前,您派人找到我,不顾自己的尊严,谦恭地请求我在即将到来的选战中给予您帮助!我做到了——尽管你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为我的都会组织提供帮助,我还是诚心诚意而且热诚地帮助您——让您看到了我作为天主教牧师的素质……从一开始,我的伟大计划就是决定让天主教选民以团体的形式为您投票——您根本无法想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经受了什么样的痛苦和磨难,我总是通过不同的机构对他们做工作,几乎不能使用这个影响,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他们被什么偏见控制。正当我们开始陷入绝望的时候——因为我们面临着巨大的阻力,无法克服或者是绕过——我们成功了……而在做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时时刻刻面临着因为债务被逮捕或者是眼睁睁看着教会组织的财产执行的危险:同样,我在此函中所写下的每一个字是完全的而且神圣的事实……现在我对您说的所有这一切只是想强调:您没有欠我什么,我不想从您那儿要求什么,天主教各教会不想从您那儿要求什么,我自己会承担所有的开销……而且以名誉发誓,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任何时候,我什么要求都不会向您提,但是从现在算起,一年以前我向您提出的关照,当时我们俩谁到没想到会有一场选战——我为您尽了我的努力……我的心里没有半分钟的怀疑,您会对我尽您的责任。”列昂内尔似乎没有完全满足劳齐的愿望——尽管地安排他与被放逐的梅特涅进行过接触。 对于家族中的其他人来说,这是他们长期以来所期待的政治胜利。纳特写道,“这是家族中一个最大的胜利,同时也是对身处德国以及全世界可怜的犹太人最大的喜讯。”他的妻子称“拥有像你这样最杰出的战士,是犹太民族新纪元的曙光”。“缺口已经打开,” 贝蒂欢呼道,“诽谤、偏见与狭隘的障碍显然正在消?。”甚至梅特涅(他似乎没有想到自由党人的一场胜利会在一年之后使他被放逐)都发来了贺信。然而,所有这些令人愉快的祝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如果列昂内尔想要坐到下院议员的位置上,他还必须宣誓“以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念”——当然,除非政府能通过那项11年前已经证明不可能被通过的议案,也就是废除这个誓词的法案。罗素早就已经提出过一个类似的提案。事实上,列昂内尔的胜利只有当这种提案在国会的两院投票中都获得多数支持时才有可能最终得以实现。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3部——争取政治权利
书名: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3部
作者: [英] 尼尔·弗格森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动荡的年代
译者: 何正云
出版年: 2009-9
页数: 361
定价: 45.00元
丛书: 中信金融史
ISBN: 9787508616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