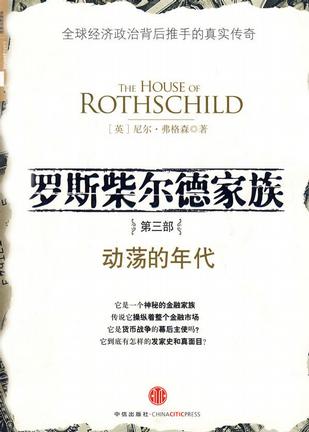我5点睡着,但6点就醒来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巨大的吸血鬼正在贪婪地吮吸我的鲜血……很显然,当投票的结果公布出来的时候,震耳欲聋的疯狂欢呼声回荡在整个上议院的上空……我们没有道理遭受到如此大的憎恨。 ——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1849年5月 尽管他们设法控制住了金融领域的风暴,但1848年还是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命运的转折点——不过原因与经济和政治都没有关系。在大革命刚刚结束后的那些年里,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公司的结构出现了很多问题。在翻阅他们的往来信函时,人们很容易会忽视掉老梅耶当时仍然健在的4个儿子其实都已经进入垂暮之年的事实。在1850年的时候,阿姆斯洛77岁,萨洛蒙76岁,卡尔62岁,而且身体状况都不好。只有詹姆斯还处于精力充沛的56岁年龄段。 从另一个方面说,长寿是这个家族的特点:尽管他们的父亲在68岁时去世,但他们出生于1753年的母亲,亲身经历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在她的家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给一位普鲁士国王加冕,使他成为一位统治整个德国的新国王的历史时刻。事实上,古特尔•罗斯柴尔德在19世纪40年代时成为很多幽默的代名词,比如《时代》的一篇报道中描述的: 德高望重的罗斯柴尔德夫人来自法兰克福,现在很快就要成为一位百岁老人,在她上周身体略感不适接受过治疗后,她非常友善地向她的医生指出给她开的药没有什么效果。“夫人,我还能怎么做呢?”医生说,“很遗憾我不能让您返老还童。”“你错了,医生,”这位诙谐的女士反驳道,“我并没有要求您让我返老还童,我所希望的是长命百岁。” 关于这个故事的漫画很多,其中一幅名为《老奶奶的99岁生日》,画面上是詹姆斯对来祝寿的众人说:“先生们,等她的身体恢复了,我将给国家捐赠10万基尔德荷兰货币单位。——译者注,一点小钱,聊表心意。”画的背景处是古特尔(见图11)。同样的笑话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一名医生保证她“活到一百岁”。“你在说什么呢?” 她很坚决地打断他的话,“如果上帝让我活过了81岁,他就不会在100岁的时候叫我去!” 图11佚名,《老奶奶的99岁大寿》,(大约1848年) 资料来源:富西斯,《犹太人讽刺画》,第146页 她拒绝搬离位于过去犹太老街的那所“绿色盾牌”老宅的固执,也引发了与她同时代人的很多遐想,它总是让人不自觉地将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凡的经济成就与某些犹太戒律联系在一起。路德维希•伯尔内早在1827年就为此替她谱写了颂歌:“看,这就是她的居所,一所如此狭小的旧屋…… 她无欲无求,尽管广大的帝国由她的儿孙们掌管,留给她的也只是祖先留在犹太老街的这所小屋。”当查尔斯•格雷威尔16年后到访法兰克福时,他惊奇地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太太”出现在“昏暗、破旧的楼里……(这座楼)一点都不比”这条“犹太街道”上“其他的房子好”:在这条狭窄、昏暗的街上,在这所破旧的老房子前面,站着一位身披绿色丝巾的精干的老太太,一名身着蓝色制服的男仆守在门边。现在,门是打开的,只见这位老太太正从昏暗、狭窄的楼梯上走下来,搀扶她的是她的孙女查尔斯•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男爵夫人的马车正等在街头。两名男仆和一些女仆负责帮助老太太坐进马车,很多住在同一条街道的人聚集在对面看着她坐进去的这一幕。我以前从未见过如此让人迷惑和震惊的反差:这些女士,无论是老的还是少的,她们身上的服装以及车上的配饰,甚至包括仆人的制服,是如此的光彩夺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位老人坚持不愿搬离的这条街道是如此破败。按照格雷威尔的说法,古特尔经常有这样的出行,而且“长期坚持不懈地去看歌剧或者其他演出”。很显然,他并不像伯尔内和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清心寡欲。 1849年的5月7日,古特尔在她还健在的儿子们的守护之下,最终还是去世了,享年96岁。 这只是这个家族的辞世大潮中的一件。在此一年之前,阿姆斯洛的妻子埃娃辞世。在1850年,内森的寡妻汉娜走了,与此同时,她的孙子——纳特的二儿子——梅耶•阿尔伯特也走了,这件事让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深受打击。卡尔的妻子阿德尔海德卒于1853年,一年后,萨洛蒙的妻子卡罗琳也相继去世。这些事件对第二代那些年迈的家族成员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容易预见的。梅耶•卡尔注意到他母亲的去世怎样“深深地影响了”阿姆斯洛。“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一件重大的损失……我无法告诉你我们后来熬过了多少悲惨的时光……阿姆斯洛叔叔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过在真的令人非常恐惧的第一波悲恸过后,感觉上好了很多。”事实上,当全家人集中到法兰克福为古特尔举行葬礼的时候,阿姆斯洛也仅只是略微镇定了?点点。他和他的兄弟萨洛蒙在他们的风烛残年中忍受了很多孤独凄凉,他们花在账房的时间越来越少,而花在花园里的时间越来越多。 在刚刚恢复日耳曼联邦议会新普鲁士代表身份,名叫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年, 德国政治家, 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译者注的奸雄式、超级保守的容客意为地主之子, 原为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 19 世纪后开始资本主义化, 成为半封建型的贵族地主。这里泛指年轻的德国贵族。——译者注眼里,阿姆斯洛是一位可怜的老人。在到达法兰克福不久后,俾斯麦在给他妻子的信中说道,“在货币领域”罗斯柴尔德在法兰克福的社会中理所当然地是“最杰出”的人。但“如果把钱和薪金从他们身上拿开,你就会看到”他和其他的法兰克福人一样,其实是“多么平凡无奇。”当阿姆斯洛提前10天(主要是为了确定他能接受邀请)邀请俾斯麦参加晚宴时,他这个新面孔令人讨厌的性格特征表现得一览无余——他回答说他应该会到场,“如果届时他还活着”。这个回复“使他大为震惊,以至于他对所有人都重复这句话‘天哪,他怎么会提到死活这样的问题呢?这个人是这样年轻、这样强壮’。”以俾斯麦的有限的收入和微薄的薪水来说,他肯定会对阿姆斯洛宴会上呈现在他面前的银质餐具、金质刀叉和汤匙、新鲜的蜜桃和葡萄以及琼浆美酒的盛况印象深刻并心生厌恶。当这位老人在餐后骄傲地对俾斯麦炫耀他最心爱的花园的时候,俾斯麦再也掩饰不住他内心的蔑视: 我喜欢他,是因为他是一位真正不择手段的老犹太人,而且他并不试图掩饰自己的出身;他严格遵守他们的教规,吃饭时除了教规中认为清洁的食物外不碰任何其他东西。“约翰,带点面薄(包)给小鹿。”当他带我去观赏他养有鹿的花园的时候,他这样对他的佣人说。“兰(男)爵先生,这棵树花了我两欠(千)基尔德,老实说,是两欠(千)基尔德闲(现)金。您要的话,一欠(千)块拿去;干脆,您要喜欢的话,我就党(当)礼物送给您,他会给您松(送)到家里。尚(上)帝知道我是多么得尊敬您,兰(男)爵,您真的是一表任(人)才,一位优秀的人。”他个子不高,很瘦小,头发已经花白。他是他们那一辈人里的老大,但在他的宫殿里他却是一个可怜的人,一个绝后的鳏夫。很多事情他都被他的仆人蒙在鼓里,而且还被他的那些法国化或者英国化的侄子侄女们所鄙视,这些人在等着继承他的财富的同时,对他却没有任何的爱戴和感激。随后,阿姆斯洛提出将他在黑森州的房子租给俾斯麦,但俾斯麦拒绝了,因为他感觉这是企图讨好他的一个试探。按照其他的主要敌视者汉挪威国王的说法,“每当外国王子或者部长,也或者是其他的大人物来到法兰克福的时候”,阿姆斯洛都要做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他的晚宴上总是“通过炫耀金银餐具和奢侈品来显示其无比的华贵和奢华,他总是通过告诉来宾他去哪买来的鱼和肉,以及他为这次聚会所耗费的巨资来给大家取乐……每时每刻都尽显暴发户的本色以及高利贷者和票据交易贴现商人的狭隘心理”。 正像俾斯麦的精明预言一样,最后的问题来了——财富由谁来继承——这些财富占据了老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富的绝大部分,他们因此花费了很长时间对他们的遗嘱进行了左修右补。在多年以前的1814年,阿姆斯洛曾经开玩笑说,一个富裕的德国犹太人和一个富裕的波兰犹太人之间的差别是后者会“在他刚开始失败的时候死去,而富裕的德国犹太人只会在拥有了巨额财富后才死去”。40年后,阿姆斯洛成为了他自己说法的典型例子,他在家族企业所拥有的股份价值近200万英镑。但是谁将继承这些财富?在长期以来祈求生个儿子的愿望没能实现之后,阿姆斯洛开始认真考虑他12个侄子中每个人的优劣,特别是那几个定居在法兰克福的侄子(首当其冲的是卡尔的儿子梅耶•卡尔和威廉•卡尔。最后,他将自己在家族生意中的股份按下面这种形式进行分配:詹姆斯得到了1/4,安瑟尔姆1/4,内森的四个儿子均分1/4,卡尔的三个儿子均分最后的1/4。 萨洛蒙有一个继承人,而且在巴黎还有一个女儿。但或许是因为和安瑟尔姆在维也纳时,对于革命危机可能出现的高潮的认识话不投机,而且说过重话,所罗门力图不把安瑟尔姆列为唯一的继承人。他设计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方案,把自己名下的绝大部分财富直接转给了自己的孙辈。起初,他似乎考虑把几乎全部的财产(175万英镑)留给他女儿贝蒂的孩子(男孩每人425万英镑,而夏洛特只有5万英镑,但在她与纳特结婚的时候已经给过她5万英镑),只把他的三所房子留给了安瑟尔姆和他的儿子,而留给他们已经出嫁的姐妹汉娜•玛蒂尔德的只有8 000英镑。他告诉安瑟尔姆说,至于他的巴黎饭店将留给“你和你的儿子们……我重复一遍,是给你和你的儿子们。我已经认真考虑过,增加了一个条款(来确保它可以一直作为他们的财产)百?不变——女婿或者是女儿都没有任何权利来主张这份财产”。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在身后发挥最大影响力的策略,与他父亲梅耶•罗斯柴尔德在1812年时的所作所为颇为类似;事实上,把女性从家族产业中排除是他从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观念。但与他父亲不同的是,萨洛蒙决定他的孙子中最终只有一人可以从安瑟尔姆处继承他在家族生意中的股份——这是在几乎一直平均对待所有男性继承人的家族中是一个新出现的情况。在萨洛蒙于1853年最后确定的遗嘱附件中,他废除了将继承人的选择权留给安瑟尔姆的条款,指定了(但最终没有实现)他的长孙纳撒尼尔。但最终,萨洛蒙的所有计划全部泡汤,最后的实际情况是继承他财产的是安瑟尔姆,同时也由安瑟尔姆来决定谁做其继承人。另外,俾斯麦也说对了,年青一代的罗斯柴尔德们都嘲笑他们的老叔叔。拜访总是“一脸苦相而且总是郁郁寡欢”的卡尔叔叔,是一件特别令人痛苦的事情。如果1855年注定要有一件悲痛事件发生的话,那么,不会有什么事能比萨洛蒙、卡尔和阿姆斯洛在仅仅9个月之内就相继撒手人寰更令人欷歔了。 这次死神的突袭发生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业务出现剧烈震荡的时期。正如我们已经讲到的,不得不被销账的在维也纳机构发生的巨额亏损很难以让人释怀,特别是伦敦的合伙人,他们对叔辈们那种鲁莽的业务方式可能出现的最坏可能性的担心,看起来已经被证实了。遗憾的是,公司的结构意味着由萨洛蒙造成的损失必须由大家来共同承担;而且他的个人股份在公司总股本中所占的比例也不会相应减少。这种情况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紧接着革命结束后的那段时间,由梅耶•A•罗斯柴尔德在差不多40年前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把儿子和孙子融合在一起的这种血缘联系,会面临如此巨大的分离压力。具体来说,伦敦方面寻求能把他们自己从对四个大陆银行的承诺义务中“解放”出来,因为这四个银行由于欧洲大陆发生革命而遭遇了惨重的损失。正如纳特在1848年7月时所说,他和他的兄弟们希望能够“做某种安排,以便每家银行都可以有相对独立的位置”。当“商业和金融大会”的想法首次在1848年8月提出来的时候,对这个会议前景的忧虑笼罩着夏洛特:“阿姆斯洛叔叔正遭受着丧妻之痛,这使他看上去很虚弱,也很痛苦;萨洛蒙叔叔正遭受着失财之痛;詹姆斯叔叔正为法国局势的不确定而头痛;我的父亲(卡尔)也很焦虑,尽管我的丈夫状态非常不错,但是也一旦得理,决不让人。” 当詹姆斯在1849年出发前往法兰克福去探望他的兄弟和侄子们的时候,贝蒂满心希望大会能“改变我们各家银行之间的基础,跟随伦敦银行,让大家都能从目前这种不能适应政治发展状况的限制中脱离出来”。在同一年中稍晚的时候,巴黎和伦敦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成为争吵,因为詹姆斯听说梅耶•卡尔已经“命令”戴维森兄弟“不要再给巴黎发送任何黄金”——这可是英国方面最高层领导的指令——这让詹姆斯觉得再也无法忍受。而在巴黎银行自身内部,纳特和詹姆斯的摩擦也是由来已久。前者由于比他的叔叔表现得更谨慎,因而生意一直都比较顺手,但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革命几乎摧毁了他作为商人的神经。“我建议你们在正常的商业交往中一定要加倍小心。”他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所写的一封典型的信件中这样劝告他的兄弟们。 对于我来说,我现在对生意是如此厌恶,不想再接手任何类型、任何性质的业务……整个世界局势的现状是革命每时每刻都在蔓延,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跃入齐颈的烫水中只是为了寻求赚一点小钱的机会,那简直就是完完全全地疯了。我们的好叔叔们是如此可笑地着迷于为生意而生意,而且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不想让别人做任何他们发现别人想做而又不能放任让别人去做的事情。从我的角度说,我十分确信巴林银行再怎么努力进军西班牙水银市场对我们也没有任何威胁,如果他们选择这样做,就让他们去做,我们自己应该知足常乐,并以平常心对待。 贝蒂也看到了这种情况。她曾经评论道:“我们的好叔叔(阿姆斯洛)无法接受我们的财富缩水的现实,他急切地希望将它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为此,他会毫不犹豫地将我们重新抛回危险业务的折磨中。” 但是,詹姆斯对纳特的这种怯懦越来越不耐烦。夏洛特猜想詹姆斯应该肯定会欢迎他的侄子从生意中撤出,因为这使得他年龄稍长的两个儿子阿尔方索和古斯塔夫(他们的第一次露面出现在1846年的函件中)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业务中。正如贝蒂所指出的,这种长期以来的“兄弟团结的老传统”似乎“已经接近分崩离析的边缘”。 这些还不是家庭失和的唯一原因。甚至早在1848年革命爆发之前,法兰克福银行就对伦敦方面的态度有很多怨言。安瑟尔姆抱怨道:“做最卑微的仆人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情,在执行您的指令时甚至都无法通过西班牙的信使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准确地说,是我们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很久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这个由不同的公司所组成的群体中被归类为二等公民。”正如这段话所暗示的,安瑟尔姆认为,作为下一辈人中的长子,他应该成为阿姆斯洛在法兰克福的继承人。然而,维也纳分部所受到的打击改变了所有这一切,因为这个变故促使他继承了他父亲在奥地利的位置。也是基于同样的想法,卡尔希望他的长子梅耶•卡尔到意大利继承他的事业。然而,没有子嗣的阿姆斯洛更坚决地认为梅耶•卡尔应该在法兰克福接替他,让他能力稍逊的弟弟阿道夫去那不勒斯。就像詹姆斯所看到的,这样的争论不仅发生在这几个年迈的兄弟之间,也同时发生在他们的儿子和侄子之间,原因很明显,他们都觊觎着法兰克福银行,因为它仍然主宰着维也纳和那不勒斯分部的业务:“安瑟尔姆在和梅耶•卡尔较劲。梅耶•卡尔在和阿道夫较劲。”尽管夏洛特很明显与她的哥哥一个鼻孔出气,但她在日记里还是详细描绘了这种竞争所产生的那种不和谐气氛: 梅耶•卡尔很成熟,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杰出的人士,一个国际公民。他正值盛年,处于无可置疑的权力巅峰。他通过他迷人的举止、活泼的天性以及睿智的谈吐为他自己赢得了比安瑟尔姆要多得多的支持率。事实上,他在法兰克福是一位广受欢迎而且深受喜爱的人物,他受欢迎的程度使我的姐夫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望尘莫及。我深信他所掌握的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绝不亚于安瑟尔姆,我无法评价他是否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生意人,他对重要事件的判断能力是否正确,他是否是一名出色的作家或者是演讲家…… 安瑟尔姆总是在我哥哥面前表现优越感,这种情况是非常没有道理的,因为要想找我哥哥这么一位有才华的人,您可能得搜遍整个帝国。或许他的天资达不到追求人文思想的科学机构所要求的全面的研究能力和长期的学习能力。然而,作为一个银行家和世界杰出人士,作为一位欧洲社会中举止优雅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员(因为他在所有国家及阶层中都能游刃有余),在我看来他没有任何对手。安瑟尔姆用这种轻侮的态度对待我哥哥是很不公平的,而且有些卑鄙。 最后,我们应该牢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在1848年的大动荡后,伦敦和巴黎对维也纳银行的愤怒和不满。曾经有很多次,詹姆斯的言辞中都表露出连他都很想切断与维也?的联系。“我对维也纳没有兴趣。”他在1849年给纽科特写的信中这样说,“当其他人都在那儿对政府进行投机的时候,我们在维也纳的人却一点儿都不聪明,而且很遗憾,他们都是一群差劲的生意人。他们只会一根筋地认为他们做生意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合伙制度在1852年的时候终于进行了更新,对1844年确立的体系进行了一些调整,并在随后的20多年中取得了不亚于之前体系的辉煌成绩。原因是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公司作为跨国合伙制企业能存活至今的最好解释,在于詹姆斯在化解代沟,并把家族中分歧日益增大的各个分支机构再次重新绑在一起的整个过程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夏洛特1849年在法兰克福看她的叔叔时说的一样,詹姆斯从1848年的危机中重新崛起,而且他对生活和生意的欲望丝毫没有减弱: 我以前很少能见到如此精明能干的人,如此具有国际意识又如此谨慎,无论是思维还是身体都是如此积极主动,不知疲倦。当我想到他成长于法兰克福的犹太街,在他的孩提和青年时代从来没有享受过高雅文化的熏陶时,我就更加惊奇,对他的仰慕根本无法用言语表达。无论是任何事情,他都能从中找到乐趣并且自得其乐。他每天写两到三封信,口述至少六封,阅读所有的法文、德文和英文的报纸,冲澡,睡一小时的回笼觉,玩三到四个小时的扑克牌。 这就是詹姆斯离开巴黎后每天的日程安排。年轻的股票经纪人费多在拉斐特大街上遇到的詹姆斯仍然具有海涅在诗篇中所描绘的他在青春全盛时期所洋溢的自然魅力,如果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只能说年龄只是增加了詹姆斯的威严。 尽管詹姆斯年轻时精力充沛,但他当时深深地浸润在他父亲那个时代所形成的家族特质里。在1848年以前,他一直忧心忡忡地关注着5家公司相互间发生争执的各种迹象。他在1847年4月警告列昂内尔,有关账目的纷争将会引发“这样的事态,最终结果是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样会产生大量的不愉快”。“深藏在我心中的只有家族的声誉、幸福和团结的。”在回复父亲梅耶老生常谈般的警告时,他这样写道:“作为商业交往的一个成果,我们保持着团结。如果大家每天都分享并且能接收到同样的账目,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将按照上帝的愿望继续保持着团结。”正是秉承着这样的理念,詹姆斯在1850年的夏天回来了,随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满腔的热情和急迫的心情——下面所抄录的是一封充分说明这种重要意义的函件: 打破一样东西要比将它再次聚合起来更容易。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子嗣将我们的生意延续百年,因此,我们不应该相互为敌……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当(单独的)公司不再存在——那时我们已经没有了团结,也没有了业务合作,然而所有这些在世人眼里是我们真正的力量之所在——那一天,就是我们的生存面临危机,而且每个人都得自寻出路之时。善良的老阿姆斯洛会说:“在家族的生意里我有200英镑,但是现在我打算取出来。”我们有什么办法来阻止他?一旦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方式,他可以娶戈尔德施密特(Goldschmidt),而且说:“我可以按照我的意愿把我的钱投到任何行业。”那时,我们的余生将会在永远无法摆脱的自责中度过。亲爱的列昂内尔,我相信我们是能在法兰克福发挥影响力的仅有的两个人,我们必须将我们的目标确定为在所有合伙人之间恢复和平……如果我们不留神,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高达300万英镑的资本可能会落入外人之手,而不是传给我们的孩子。我想问你,难道我们发疯了吗?你可能会说我老了,而且我的目的是想提高我的资本的权益。但首先感谢上帝,我们所有人的资本储备都要远胜于我们上一次签署合伙合同时的情况;其次,就像我刚到这里的那天跟你说的,你将会在我的身上看到一个全心全意的叔叔,他会以他所有的能力来达成必要的妥协。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理清楚这些争论的思路,并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让两方都做出一些牺牲来保持团结,感谢上帝的恩惠,团结保护我们度过了最近发生的所有这些灾难,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去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来为实现这个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些就是詹姆斯在1850~1851年间经常重复的理念。“我向你保证”他告诉列昂内尔的妻子夏洛特(他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同盟者),“家族就是一切:它是在上帝的仁慈帮助下,我们所拥有的幸福的唯一源泉,它维系着我们(相互间)的依恋,它是我们团结的纽带。” 由于詹姆斯为维系团结所付出的努力,1852年的合伙合同因此也是顺理成章的——不是弱化各公司间的联系,而是通过妥协保留这种联系。妥协的主要内容是英国合伙人放弃他们完全独立的主张,作为交换,他们得到了较高的资本回报率。早在1850年,詹姆斯就提出了这种妥协的框架:用纳特的话说,建议“对于我们的资本回报率应该提高”,前提是英国银行总能比其他银行获得更多的盈利。这是我们上面抄录的他给列昂内尔的那封信中的主要要点,同时也是大家最终在1852年所同意的新的体系的基础。英国合伙人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好处:他们的退股部分不仅可以得到26025万英镑补偿,他们股份(此时占总股份的20%)的利息也增加到35%,而詹姆斯的是3%,卡尔的是2625%,阿姆斯洛和萨洛蒙则是25%。另外,业务管理联合行动的规定也有所松动:从今往后,合伙人不再需要因为多数人要求就必须得进行商务旅行,在对地产投资时也不需要再使用集体基金进行融资。为了回应这些让步,英国合伙人接受新的合作体系。协议第12条中说,“为保证一种公开的、兄弟般的合作,并发展大家共同互惠的商业利益”,应该向其他所有合伙人通报任何超过1 000万基尔德(约合83万英镑)的交易,并在互惠的基础上提供最高10%的参与机会给其他合伙人。老协议中的那些没有被新协议条款修订过的所有条款仍然保持效力,比如共同账目的操作程序。这些措施毫无疑问代表了一种分权的做法。但考虑到另一种选择(在随后的一年中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是对家族集体企业的全面清算,因此对詹姆斯来说,这个成果的取得代表了一场新的胜利。 1852年协议中没有解决的是决定法兰克福?继承人(除了排除了阿道夫的备选资格外):从此之后,安瑟尔姆、梅耶•卡尔、威廉•卡尔都在竞争法兰克福银行的这个职位。(同时,也给阿尔方索和古斯塔夫提供了竞争巴黎公司位置的机会。)当詹姆斯的几个兄弟在1855年辞世后,新的公司结构才最终尘埃落定(参见表1-1)。尽管萨洛蒙在遗嘱中做了明确的规定,但是他在集体资本中的所有股份还是转给了安瑟尔姆(这是詹姆斯在代表他的妻子提出异议的时候显得不是很坚决所产生的结果,而对于詹姆斯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不详)。卡尔的股份在减掉给女儿夏洛特的1/7后,在他的儿子间平分。最后的决定是,阿姆斯洛的股份按下面这种方案进行了分配:詹姆斯和安瑟尔姆每人得到1/4,内森的几个儿子和卡尔的几个儿子也各得1/4。所有这些变故的最后结果就是,安瑟尔姆、詹姆斯与英国出生的合伙人之间的实力基本均衡,而卡尔几个儿子的影响力大大削弱。在决定将阿道夫派去负责那不勒斯公司的业务,而将法兰克福留给梅耶•卡尔和他那对宗教十分虔诚的兄弟威廉后,他们的影响力被进一步削弱了。 这就是在现实中所达成的妥协。在1852年之后,詹姆斯准备提出一项与他的侄子们的想法相差更大的史无前例的改革,但新的董事会不再听候詹姆斯的指令——这可以很容易地从他给伦敦的信在1848年后篇幅大幅缩水的情况中推断出来。他在给纳特的信件中出现“又及”内容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且在他对业务的建议中,最后常以这样的话语结尾——就好像是在提醒自己和他们之间不再有主次之分:“亲爱的侄子,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这毫无疑问极大地满足了列昂内尔的虚荣心。1852年的妥协意味着1848年以前那种业已存在于5个公司之间的合作体系得以恢复,只是做了适度的分权。巴黎和伦敦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表明相互间的依存度确实比19世纪20年代的时候要小一些,但总体来说还是非常大。例如,巴黎公司在1851年12月资产中的174%是其他的罗斯柴尔德公司欠它的钱,而其中主要又是伦敦所欠。 表1-1合并后罗斯柴尔德资本中的个人占股情况,1852年和1855年 1852年 英镑 英镑 百分比(%) 1855年 英镑 英镑 百分比(%) 列昂内尔 安东尼 纳特 梅耶 464 77075 464 77075 464 77075 464 77075 1 859 08300 2005 列昂内尔 安东尼 纳特 梅耶 685 53686 685 53686 685 53686 685 53686 2 742 14744 258 阿姆斯洛 萨洛蒙 詹姆斯 卡尔 1 859 08300 1 859 08300 1 847 08300 1 847 08300 2005 2005 1992 1992 安瑟尔姆 詹姆斯 梅耶•卡尔 阿道夫 威廉•卡尔 805 54066 805 54066 805 54066 2 742 14744 2 727 98743 2 416 62199 258 2567 2274 合计 9 271 41500 100 10 628 90428 100 说明:1855年的数据根据那不勒斯和伦敦的数据(没有法兰克福、维也纳和巴黎公司的文字资料)进行估算。在1852和1855年间,那不勒斯公司的资本增长了135%,伦敦公司增长了228%;我在表中采用了这两个数据的均值18% 资料来源:由阿姆斯洛、萨洛蒙、卡尔、詹姆斯、列昂内尔、安东尼、纳特、梅耶于1852年10月31日共同签署的SocietatsUbereinkunft,CPHDCM,637/1/7/115~120;1855年12月重新分配阿姆斯洛和卡尔股份未标明日期的文件,N,132 AQ 3/1 另外,伦敦的合伙人认为他们的公司比其他公司盈利水平高,最终被证明是过分自信了。尽管那不勒斯和法兰克福公司出现了萧条的迹象(主要的原因都超出了阿道夫和梅耶•卡尔所能控制的范围),但詹姆斯承担起了1852年后的大多数业务,他的大陆铁路业务扩展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到他生命的暮年,巴黎银行的资本已经远远超出了其他合伙公司。安瑟尔姆在重建千疮百孔的维也纳公司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商业天才,也让大家大感意外。在让伦敦合伙人来分享大陆的这些胜利果实方面,没有任何人表现出任何的不情愿。因此,新的体系开创了一个伦敦和巴黎银行间平等状态的新时代,而在法兰克福和那不勒斯银行的影响力走下坡路的时候,维也纳又重新崛起了。 与过去的情况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只是靠合伙协议和遗嘱来维护家族企业的团结。同族婚配继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1848~1877年的这段时间内,我们可以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不少于9桩婚事显而易见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不同支系之间的联系。在1849年,卡尔的三儿子威廉•卡尔娶了他的堂兄安瑟尔姆的二女儿汉娜•玛蒂尔德;一年后,他的兄弟阿道夫娶了她的妹妹朱莉;在1857年,詹姆斯的长子阿尔方索在加奈斯贝里娶了他的堂兄列昂内尔的女儿莉奥诺拉。在这里把这些例子一一列举出来是一件非常乏味的事情。在1826年詹姆斯的儿子萨洛蒙娶了梅耶•卡尔的女儿阿德蕾。1865年,安瑟尔姆的儿子费迪南德娶了列昂内尔的女儿艾福林娜。1867年,列昂内尔的儿子纳桑尼尔娶了梅耶•卡尔的女儿爱玛。1871年,纳特的儿子詹姆斯艾德华娶了梅耶•卡尔的女儿劳拉•德赫瑟。1876年,安瑟尔姆的小儿子萨洛蒙•阿尔伯特娶了阿尔方索的女儿贝迪娜。最后。在1877年,詹姆斯的小儿子艾德蒙娶了威廉•卡尔的女儿阿德蕾德。在1873年之前仅有一个例外,但就是这些没有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通婚的,也没有脱离犹太人“表亲关系”的传统太远。例外是安瑟尔姆的女儿萨拉•露易丝,她在1858年嫁给了托斯卡纳贵族拜伦•莱蒙多•富兰奇迪。1850年,梅耶娶了朱利安娜•科恩——击败了竞争对手约塞夫•蒙蒂菲奥里——而他的侄子古斯塔夫在1859年娶了塞西尔•安斯波。要是威廉•卡尔没有娶到姓罗斯柴尔德的妻子,他可能会娶施纳佩尔——他的祖母古特尔家族的成员。 在将近两代人的时间里,为这些联姻牵线搭桥一直是家族女性成员的主要工作。夏洛特对这一点没有任何的怀疑。当她听到她的兄弟威廉•卡尔与汉娜•玛蒂尔德订婚的消息时,表现得非常热情:“我敬爱的双亲当然会非常高兴,因为他终于没有选择一个外人。对我们犹太人来说,特别是对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最好不要与其他的家族有什么瓜葛,因为这种事情总是会带来不愉快、而且还要耗费很多金钱。”在这种情况下,什么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全都变成了一派胡言。夏洛特的表姐贝蒂用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这种婚姻,她告诉她的儿子说,“可怜的玛蒂尔德只能带着无法释怀的遗憾嫁给威廉”,现在她正“用真正天使般的顺从来说服自己奉献出她年轻心灵里的那些烂漫憧憬。我们不得不说,做威廉的终身伴侣对生长在她这种家庭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子来说,根本不具有任何吸引力”。现在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贝蒂的儿子阿尔方索和古斯塔夫应该娶谁。当时的情况似乎是汉娜•玛蒂尔德对后者比较倾心,而她的姐姐朱莉则希望嫁给阿尔方索。但在就这件事情对她的儿子做了一番调侃之后,贝蒂这样写道: 爸爸是如此直率而实在……他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根本没做任何考虑。他把他所有的悔恨一股脑地告诉了这个可怜的母亲……他使她从幻想中醒悟过来,认识到对成功的渴望最终可能会适得其反,他要求她按自己的想法,但同时也要考虑到女儿的幸福,做决定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三思而后行。 这对夏洛特来说是个好消息,她也正谋划着在贝蒂的两儿子和她的女儿莉奥诺拉和埃维莉娜之间的一举两得的类似的婚姻安排。在她的日记中,她客观地对她的这两名想象中的女婿各自的优点进行了分析: 古斯塔夫是一名优秀的青年。他有一颗最善良也最热诚的心,并且全身心地奉献给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人。他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的任劳任怨可以作为他那一代人的榜样。但无论他是否是天才,我其实都无法做出完全公正的评价。他享有良好教育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和优势,但他却声称自己很笨,很容易紧张,而且在有陌生人的场合甚至都不能把十个单词说连贯。他们说他在数学方面具备很高的技能,但我对这门学科一无所知,因此也无法做出判断。 他的哥哥阿尔方索则将我们叔叔詹姆斯超凡的精力和活力与贝蒂的语言天赋完美结合在一起。他是一个很好的读者、听者和观察者,他能记住他所接触过的所有事情。他可以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谈论任何热点话题,不故弄玄虚,并总是以一种直接、深刻而且轻松的氛围,以最舒服的方式处理各种问题。不过,要是需要什么建议的话,对他可别有什么指望,因为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议,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建议可以提。但听他谈话总是一件乐事,因为他说话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而且总是以一种迷人的、生动的语调来讲。 迪斯雷利太太说古斯塔夫英俊,我不知道我是否同意她的说法。他是雅各宾一系中唯一能以其炯炯有神的、柔和的、湛蓝色的大眼睛来夸这个口的人。在他幼年的时候,他的眼睛长得并不特别漂亮,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中其他人的眼睛没有什么不同,而现在他的眼睛已经看不到儿时的任何痕迹,除了一种人们或许可能会叫做忧郁的气质外。他的眉毛长得很精致,眉形很好,淡淡的很清爽;他有一头深棕色的缎子般的头发;他的鼻子不是鹰钩鼻;他的嘴巴很大,然而并不能以能言善辩来赞誉它,最多只能说它温和敦厚,而且它既不暴露对感情的理解,也不显示感情的深度。古斯塔夫人显得精瘦,他风度翩翩,举手投足间透着高贵的气息。我希望能在神龛上看到他的画像暗指结婚。——译者注。 她的愿望只实现了一半:9年后,她看到立在神龛上的是阿尔方索的画像,摆在了她女儿莉奥诺拉画像的旁边。在那个时候,她早已经改变了她对新郎的看法。现在的阿尔方索似乎是“一个10~15年来操纵着世界运转的男子汉,他已经完全厌倦了那种花天酒地般的生活,他不会尊重,也不会爱他的妻子,而是要求妻子全身心地去服侍他,像奴仆一样地去服侍他”。然而,她的结论是,这样可能“更好——一个已经没有了激情的男人,感觉上已经没有任何好奇,也没有任何深沉,应该更会是一位安全的丈夫,而妻子更有可能在履行她做妻子责任的过程中感受到幸福。她醒悟到这一点的时候会很痛苦,但这种痛苦不会持久”。无论如何,她的女儿“攀上了世界上的某个重要的位置,应该不会想要从自己梦寐以求的罗氏朝廷走下来,而去当一个卑微的普通人的妻子”。她的这种担心从这对小夫妻草草了事的蜜月中得到了证明,这个事情还引起了媒体的负面评论。这番感慨毫无疑问基于夏洛特自己的经历,它向我们揭示了这样婚姻安排的根本特质。 以“父母之命”作为决定性因素这样一种原则当然还是不应该太过分。夏洛特没有能为她的另一个女儿留住阿尔方索的兄弟一事表明,父母在孩子们的配偶选择方面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安瑟尔姆的女儿朱莉也拒绝了她的堂兄威廉•卡尔的求婚,以及那些亲缘关系更远一点的亲戚,比如纳撒尼尔•蒙蒂菲奥里的求婚。另一方面,她最终“选择”的阿道夫又完全是由他的父亲以及未来岳父所主导,他们花费了数月来起草这份婚姻契约;尽管这其中的谈判主要涉及单列给新娘的资产数目,以便给她某种方式的财务独立,但这不应该被错误地看成是某种形式的女权至上倾向。因此,纳特和他的妻子希望在安瑟尔姆的女儿汉娜•玛蒂尔德与威廉•卡尔结婚的时候,为汉娜•玛尔德购买1万英镑的公债。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自己女儿的这种折磨也不是没有节制,当老阿姆斯洛在妻子去世后不久即宣布他想与自己的孙侄女、人见人爱的朱莉(当时还不到20岁)再婚时,这种情况就显而易见了。家族里的其他人在医生们的支持下团结一致,反对他的这个图谋。不过我们现在无法弄清楚的是,他们的这种反对态度到底有多少是由于担心他的健康,又有多少是考虑到这件事中这位年轻女士的幸福,比如詹姆斯所担心的就是,如果对阿姆斯洛所提要求的拒绝太生硬,他有可能会从公司里退出他的资金,并娶一个外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3部——引言
书名: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3部
作者: [英] 尼尔·弗格森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动荡的年代
译者: 何正云
出版年: 2009-9
页数: 361
定价: 45.00元
丛书: 中信金融史
ISBN: 9787508616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