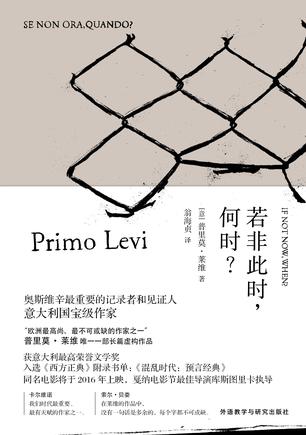“我们村没几口钟。教堂塔楼悬了一口,但是很多年前就停了,大概革命那阵子停的。我没听见过那钟响,我父亲也说没有听见过。连打钟人也没有时钟。” “那他怎么准点去打钟?” “他听无线电里的钟点,看日头看月亮。况且他也不是每个钟点都打,只打要紧的点儿。 打仗前两年,那钟绳儿绷断了。是顶上断了,梯子朽烂,打钟人又老,怕爬高儿去拴新绳子。所以,往后他要报点儿,就朝天开猎枪。一响、两响,或者三响四响。就这么着,一直到德国人来。他们缴了他的枪。村里就没了时间。” “那,你们那打钟人,夜里也打枪?” “不打,反正夜里他也不打钟。夜里大伙儿睡着,谁还听钟点。也就拉比一个人真的上心:他得有准确的时间,好晓得安息日什么时候开始结束。不过,他用不着那口钟,他有个落地大钟,还有个闹钟。那两个闹钟要是对上点,他就高兴。要对不上,你准能一眼瞧出来,因为他就不高兴了,拿戒尺打小孩的手指。我长大些后,他就叫我去给他拾掇那两个闹钟,对准了走。是了,我是修钟表的,执照什么的都有。所以征兵办公室就把我放在炮兵队。我的胸围正合适,分毫不多。我在家里弄了个作坊,不大,但样样齐全。我不光修钟表,几乎什么都能修,无线电、拖拉机,只要不坏得离谱,我都能给修好。我原先在公社农场当技工,我喜欢那活儿。余闲的时候,我才私下修钟表。也没那么多钟表可修。不过每个人都有管猎枪,我也会修枪。你要想知道那个村的名字,我告诉你,叫作斯特列尔卡,耶和华才晓得还有多少村庄叫这名字的。我该说曾经叫作斯特列尔卡,因为那村早就没了。村里人一半散在森林、郊野,一半在一大坑里。那坑也不挤,因为很多村里人之前就死了。是的,在坑里。他们自己掘的坑,斯特列尔卡村的犹太人。不过,坑里也有基督徒。这下,犹太人跟基督徒没有两样了。我跟你老实说,眼下跟你说话的人,我,门德尔,修钟表的,公社农场修拖拉机的,是有老婆的人,我老婆也在那坑里。我们没有孩子,我觉得这倒蛮走运。我还得告诉你,我会反复念叨,我以前经常诅咒那个没了的村子,因为村里有鸭子山羊,有基督教堂、犹太会堂,偏偏没有电影院。可是现在回想起来,那里简直是伊甸园,要是能让时间倒退,回到从前,就算让我砍下一只手掌,我也情愿。” 列昂尼德静静听着,不敢插话打岔。他已脱下靴子,解开缠在脚上的破布条,把靴子和布条搁在太阳下晒。他卷起两根烟,一根自己抽,一根递给门德尔,接着掏出火柴,却都潮了,划了三根,第四根才划着。门德尔坦然自若地打量他:中等身量,手脚精瘦劲健,却不粗壮; 头发又黑又直,椭圆的面庞晒得黝黑,那张脸虽然布满蓬乱的胡须,却不碍眼,鼻子短挺,两眼微凸,黑眸炯炯的。那对眼睛,叫门德尔看得移不开视线。而那对眼睛起初有些局促,接着睁眼凝视,然后目光游移,眼底满是索求。那是债主的眼睛,门德尔暗自忖想,或是自觉有所亏欠的人的眼睛。可是,又有谁不觉得自己有所亏欠呢。 门德尔问道:“说实话,你怎么走到这里来的?” “凑巧。我看见粮仓。也因为你的脸。” “我的脸跟别人的有什么两样?” “就是了:就是因为没有两样,”这大个儿小伙子勉强干笑两声,“跟无数的脸一样,让人看着觉得信得过。你不是莫斯科人,不过,你要是走在莫斯科城里,外国人会叫住你,向你问路。” “那他们就错大了。我要是能认路,就不会耽在这里了。听着,我可什么也帮不了你,不管你的肚皮还是精神。我叫门德尔,门德尔是梅纳赫姆的简称,意思是‘安慰者’,可我从没安慰过谁。” 他们闷声抽了几分钟烟。门德尔从兜里掏出小刀,拾起地上的一口碗。他不时往碗上啐口水,在碗沿磨刀。他时时验看刀锋,在拇指甲上试探。磨利之后,他开始削指甲,如同扯着一把锯子似的拿着小刀。削完十根指头后,列昂尼德又给他递去一根烟。门德尔推辞了。 “不了,谢谢。我不该抽烟。不过,能找到烟草的时候,我就抽。一个大男人,给逼得活得像头狼似的,还能怎么着?” “为什么不该抽烟?” “肺不好。或者支气管,我也说不准。周围整个世界都塌了,还搞得抽烟不抽烟果真当紧似的。成,把那烟给我。我是秋天来的,这可能是我第三次抽到烟。那边有个村子,离这里四公里路,叫作瓦楞艾孜。周围一圈都是林子,村里人蛮好,但他们没有烟草,连盐都没有。你要是有一百克盐,他们能拿出一打鸡蛋跟你换,或者整只鸡。” 列昂尼德沉默片时,似在做决定,接着他立起身,光脚走进粮仓,拿了背包回来,探手在包里翻找。他掏出两包粗盐,递给门德尔,淡淡地说道:“拿着。二十只鸡,要是你说的价格没错的话。” 门德尔伸手抓过那两包盐,拿在手掌里掂量,露出肯定的神色:“哪里来的?” “从很远的地方来。夏天里,部队发的腹带对我没有用了,盐就是拿那个换的。纵是在野草和人都在死去的时候,物物易换也不会消失的。有些地方有盐,有些地方有烟草,还有些地方什么都没有。我也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六个月来,我逐日过活,不定地走,却不晓得是往哪里去。就这么走,只为了走。我走,因为我走。” “那,你是从莫斯科来?”门德尔问。 “我从莫斯科来,也从数百个地方来。我从一所学校来,我在那里学会记账,学会了,立马又忘光。我从卢比扬卡监狱来,因为十六岁时我偷了东西,他们把我关了八个月。我偷了一块手表,所以啊,你看,我们其实是同行。我从弗拉基米尔的伞兵训练学校来,因为你要是会管账,他们就送你去做伞兵。我从斯摩棱斯克城附近的拉普捷沃来,他们在那里把我空投到德军中间。我从斯摩棱斯克的劳动营来,因为我逃脱了。我是一月里逃出来的,之后,每天就尽是走。请原谅,老伙计,我实在累了,脚痛,身上热,想睡会儿。不过,我想先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跟你说过了,我们在瓦楞艾孜附近,那是个村子,离布良斯克城有三天脚程。挺安静的地方。铁路离这里有三十公里,林子又密,山路不是淌烂泥浆,就是扬灰土,或者积雪,看季节吧。德国人不喜欢这种地方,他们来这里,就只为缴牲口,而且也很少来。走,我们去洗洗。” 列昂尼德站起身,开始穿靴子,但门德尔阻止道:“不是,不去河里。得小心。再说,河也很远。就在这里,粮仓后头。”他给列昂尼德看一架小装置:一间木板构成的小亭,亭子顶上立着一只波纹钢板水箱,在太阳下把水晒热,一只烧陶土做的小炉灶,冬天热水用的。还有只莲蓬头,门德尔在番茄罐头上戳孔,接上铁管,安在水箱上。“都是我做的。一个钱也没有花,也没人帮忙。” “村里人知道你在这里?” “知道,也不知道。我尽量不去村里,每次去,都是从不同方向走去。我替他们修机器,不说话,拿面包鸡蛋作报酬,然后走人。我半夜离开。我想从来没人跟踪过我。你先洗,把衣服脱了。我没有肥皂,至少眼下还没有,你将就用灶灰。在那边罐头里,掺了河沙的。总好过没有,况且,他们说,这东西杀虱子,可比部队发的药皂管用。对了,你——” “没有,我没有。不用担心。这几个月来,我都是独个走的。” “你先洗,把衣服脱下,把衬衫给我。犯不着见怪。你可能睡过干草堆、粮仓,虱子可是个耐心的物种:它们能等。我们也是。换句话说,在人和虱子之间应该有着明确的区别。” 门德尔内行地查看他的衬衣,一条一条线缝地扒开看:“是的,是洁食,一准错不了。就算有虱子,我也照样欢迎你; 但是没有虱子,我就更高兴。你先冲澡,我早上洗过了。” 他又仔细打量来客精瘦的身体:“你怎么没行割礼?” 列昂尼德避而不答:“你怎么知道我也是犹太人?” “就算跳进十二条河,也洗不掉意第绪口音,”门德尔答道,背诵着谚语,“不管怎样,欢迎你。因为我厌倦一个人了。你要是喜欢,就住下。就算你是莫斯科人,受过教育,从耶和华才晓得的什么地方逃出来,偷过手表,不肯跟我讲你的故事,你还是我的客人。碰到我,算你走运。我也该跟亚伯拉罕那样,在屋上安四扇门,每堵墙上安一扇门。” “为什么四扇?” “那样的话,过路人就不会找不到门了。” “你从哪里学来这些故事?” “《塔木德》,或者也叫《米德拉什》。” “那你不也是受过教育的?” “很小的时候,我跟刚才跟你提起的那位拉比学习。但他现在也在那坑里。我差不多全忘光了,只记得谚语和童话了。” 列昂尼德沉默片刻,然后说道:“我不是不想跟你说我的事。我只是说,我累了,很困。”说罢,他打个呵欠,走向冲澡间。
若非此时,何时?——一九四三年•七月(节选)
书名: 若非此时,何时?
作者: [意] 普里莫·莱维
出版社: 三辉图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译者: 翁海贞
出版年: 2016-1
页数: 319
定价: 42.00
装帧: 平装
丛书: 三辉书系:普里莫·莱维作品
ISBN: 9787513567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