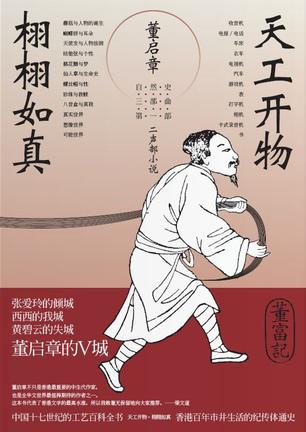栩栩的学校生活比她想像中困难,但那不是关乎学科上的问题。栩栩完全不关心学业成绩,反正课堂上教的都是她不大懂的沉闷东西。她的挫败感,来自和同学的相处。上学后一个月,她还没有成功交到一个朋友。这和她的预期相距太远了。同学们都像有意回避她,冷待她,但又无时不在注视她,窥察她。这使她觉得自己是个怪物,浑身不自在。连那个看来友善的窗前小男生也不知为什么和她保持距离,常常一下课就不见了他的踪影。有时又无故缺课,望过去那位子空空的,只有尘粒在阳光中无聊地飘荡。栩栩想起就生气,觉得这小子一定是害怕别人的眼光,不敢和她交往。冇胆鬼!没用的家伙!娘娘腔!她在心里暗骂道。有时她不免怀疑,男生是从别的班级溜进来的,说不定他念的是中二或者中三。又说不定,其实是有易服癖的女孩子装的。栩栩也知道那红发滑轮女生在留意着她。每天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也会不经意地碰见她在身旁滑过,而且总是回过头来盯着自己。这女孩总是独来独往,从来不跟任何人说话,老师和同学对她也视若无睹。这反而令栩栩产生同感。栩栩觉得红发女生的盯视没有敌意,就算有敌意,她也愿意用善意去化解,所以她坚持每次也向她微笑,无论她的反应是如何冷淡。但意愿和决心还不足够,栩栩还要了解法则。这里是人物世界,人物世界自有它的法则。 更令栩栩沮丧的是,连老师也对她抱不信任的态度。要不就是像数学老师一样总是为难她,要她解答那些完全弄不懂的演算题,要不就是像生物老师一样,当她不存在似的,明知她举手发问却装作看不见。当然栩栩还未搞通她念的是文科还是理科。有一次,她还在走廊上给一个不认识的老师截停检查。这个男老师个子不高,剃了个陆军装,穿一身棕色猎装,手臂粗壮,皮肤黑实,却架一副斯文的金丝眼镜。他的右腕是一条像椅脚一样粗的藤条,一看就猜到是训导主任之类的人物。也许他从前是个猎人,手部是猎枪,加入教育界之后才改装作藤条。训导老师叫栩栩站直,问了她的班级,狐疑地上下检视她的全身。他用一双尖锐的小眼在她的脸上寻找线索,然后着她伸出双手,掌心向上打开。栩栩突然有一刻惶恐,以为他要用那可怕的武器向她脆弱的手掌施以痛击。但他只是拿左手捏了捏她的手指。不觉痛楚,指骨也没有给捏碎。倒是那根粗大的藤条,却撩了撩她的裙襬,又在她的腰部和臀部揩擦了几下。然后,训导主任就毫无表情地打发她走开。也许,训导主任只是试探她一下,但栩栩却涨红了脸。她觉得被冒犯了,但又不知怎样说出来。她整天也挥不去那腰身被硬物触碰的感觉,但那明明不过是一根藤条,又不是他的手,那又怎算被侵犯呢?可是,对人物来说,手和作为手的藤条又有什么分别?给一个男人的藤条或手碰过为什么又会产生这样的委屈感? 栩栩后来把这件事和妈妈说了。栩栩妈妈很忙,而且总在晚上才开始出外工作,但间中也会在栩栩下课回家之后和她出外上班之前有短暂的见面和交谈。不过,她们从不一起吃晚饭,通常妈妈给她准备好吃的东西就会出门,有时候甚至只是留下买晚饭的零钱。栩栩和妈妈说话的时候,妈妈总是在衣柜镜子前挑衣服。妈妈的衣服很多,而且都是鲜艳夺目的,但栩栩从不知道妈妈干什么工作要穿这样夸张的衣服。那些衣服尺码非常大,因为妈妈像河马一样肥胖。栩栩从未见过真正的河马,但她却想到这个比喻,而且仿佛了解河马的肥胖程度。如果问她河马有多胖,她会答,像妈妈一样胖。这不失为获得知识的方法之一种。奇怪的是栩栩却是非常地瘦,和妈妈没有半点相像之处。有时候她也会想像,自己老了会长得像妈妈一样胖,或者妈妈年轻时曾经和自己一样瘦,但两者同样不可思议。她也没有妈妈年轻时的照片或什么作证据。妈妈也从来不说关于工作的事。这属于栩栩从来也不知道的事情之一。也许是从来没问过,也许是问过而得不到答案,又或许是忘记了答案。她好像忘记了很多事情,例如从前自己究竟是怎样和妈妈相处。她怎样也想不起妈妈照顾自己,带自己去玩的片段,想不起自己的童年。她和妈妈好像才相处了一个月的时间,和她上学的时间相等。有时候栩栩不禁觉得,自己不过是寄养在这家里的。妈妈似乎没有做过什么一个妈妈该做的事。但问栩栩一个妈妈应该做些什么,栩栩又说不出来。所以,结果一切问题也不是问题,因为栩栩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也许,这样对她来说好些。栩栩不知道,她毕竟是个彻头彻尾的人物,而人物和真人不同。真人必定有过去,无论她记得与否,但人物却不一定。没有交代的记忆和经历,也可以等于并未发生。这是人物法则之一。同理,只要一经说出,就等于发生了。这是颇为神奇的情况。 妈妈听栩栩说到训导主任的事,反应却出乎意料地强烈,不停追问着:他碰了你吗?他怎样碰你?碰了哪里?栩栩再三把事实复述,妈妈却好像还是听不懂似的,甚至吵着要到学校找那人算账,又嚷着转校什么的。从妈妈的反应,栩栩猜想母性的一项表现就是为着女儿有没有给人碰过这问题而发狂。但给碰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委屈感吗?反而是栩栩开始觉得妈妈有点小题大作了,尝试反过来安抚她说:他只不过是用藤条碰了碰我的腰,这里,这样轻轻一碰罢了,又不是用手摸我。妈妈竟然说:藤条就是他的手啊!有什么分别?你看,这不就是我的手吗?说罢,妈妈就开动了她右手的按摩器,两个像轮子般的塑料东西上下左右地转动着,继续训斥道:傻女!这东西就是手,看见吗,手就是这东西,你还不懂得这就是我们人物的道理吗?栩栩沉默不语,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这是人物法则之二。人物就是人物,不是人,也不是物,也不是非人非物,并且不能分开身上属于人的部分,和物的部分。妈妈察觉到女儿的反应,也沉默下来。她心中的气慢慢消了,但又不知该说些什么,仿佛也不太习惯当妈妈的角色,只有把女儿单薄的身体抱在怀中,拿按摩器在她垂下的双肩上轻轻揉搓着。房子里只有按摩器转动的声音,像午后爬行的蜗牛。栩栩突然觉得很疲倦,倚在妈妈那软沙发一样的怀里,半合上眼睛。她像说梦话似地问:妈妈,为什么我和别人好像有什么不同的?我是不是个人物?妈妈,我是什么造的?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不是你生的吗?为什么我身上没有别人都有的东西?为什么,我不记得以前的事?妈妈没有立即回答她,只是继续按摩她的肩,然后是她的手臂,和她的腿,一边喃喃地像催眠似地低语着:你这个傻瓜,我也不知为什么会养了个像你这样的女儿,这是谁的安排呢,你看看,你的身体是那么的真实,这样的腰,这样的手臂,这样的腿,简直像真人一样,叫人怎样相信呢,但你要相信妈妈的话,你是个不折不扣的人物,你终有一天会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构造,知道自己的来由,妈妈暂时不能说得太多,这会对你不好,这些东西是要留待自己去领会的,如果真的有人不信你,你就告诉他,你心口里有一个八音盒,这就是你的东西,知道吗?栩栩其实不知,她仿佛在做梦,在迷迷糊糊间点点头,无力地笑。 栩栩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天黑了,妈妈已经出门。栩栩疑惑着妈妈是不是真的说过那番话。她坐在镜子前,解开上衣钮扣。她尝试把耳朵贴到胸口上,但这当然不可能。她差点扭断自己的脖子。于是她唯有用手指在胸口上东按按西按按,探测里面有没有异物,又拼命呼吸空气,收扩胸腔,然后又拿硬面包捶打自己的肋骨,但也敲不出半声音乐来,更不用说确认体内藏着什么八音盒了。妈妈的话是真的吗?妈妈是真的吗?她咬了硬面包一口。至少面包是真的。很硬。 栩栩认为被排挤不是自己的错。她相信自己是个外向的女孩,内心充满善意,随时准备和别人交朋友。她觉得这是她自己个性,是自己一手掌握的事情。个性是不需要他人赋予的,不受他人的影响和摆布,也不必得到他人的认同。但她不知道,个性是人物法则之三。栩栩慢慢就会知道,人物必会因着各自的特征而有它特定的个性,而这个性会反过来变成人物的限制。这是个必须的学习过程,也是个痛苦的学习过程。也许,学习本身必然就是痛苦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及得上无知的快乐。 栩栩同时觉得十分孤独。一个外向而孤独的女孩,滋味异常难以言喻。每天在床上醒来,张开眼,就像第一天一样,她就确切地知道只有她自己一个明了此刻自己的感受。那就是栩栩所理解的自己。穿着校服裙,踩着单车,在起伏的路上平衡着身体,让脸庞和四肢的皮肤迎向河道上暖和的风和日渐干燥的阳光的快慰,也不会有人能分享。沿途看到的景色,无论美丑,也只属于她眼睛里的投影。就算是那个笨蛋天使般的小男生或者每天回头盯视的红发女孩,也不会体会到她心底的孤寂。她每天坐在课室的人堆里独自坚持着无用的微笑。小息的时候坐在间中坠落雀屎的树下啃咬硬面包。这些画面只有她自己一一自我欣赏。自觉让她倍感孤单,但这同时也是解除孤单,自我陪伴的方法。她尝试闭上眼,倾听自己心中的八音盒,有时好像真的听到,有时又像什么也没有。 那天,正当栩栩在学校礼堂后面的一个比较清静的角落里闭着眼睛,把自己的心跳想像成八音盒的叮叮咚咚的时候,却听见身后发出一个像打碎玻璃一样尖刺的声音。她的八音盒差点给吓坏了。后面就是毗邻学校的废车场,两者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围栏。那声音就是在围栏的另一边传来的。栩栩悄悄凑近木板的间隙,隐约窥见废车场的一角光景。在一辆破烂的旧双层巴士旁边聚拢了一群学生,看清楚原来是栩栩的同班同学。班里叫马尼的眼睛镶着一对厚厚放大镜片的女生,正站在巴士上车口的梯级上,挥动着一副凹透镜眼镜,向下面的人宣示着什么重大的事情。这时她大概看不见任何东西,因为她的放大眼只适宜看半尺以内的事物,而平时得配戴凹镜眼镜来矫正视力。在班上,马尼总是出其不意地向栩栩凑过来,鼻子差不多要碰上她的脸,用她那双看久了要教人晕眩的大眼上上下下地搜索。这绝对算不上是礼貌的举动。因为马尼的声音尖厉,所以栩栩在围栏后面听得很清楚,她在说:我敢肯定,她不是个人物!我看得一清二楚,没有东西可以瞒得过我马尼的眼睛,她的皮肤绝不可能是假的,那样嫩滑得可厌的皮肤!她绝对不是个人物,她是人!真正的人!说罢,马尼仰脸向天,仿佛藉此加强言辞的效果。栩栩担心阳光会在马尼的放大眼里聚焦。也许她歇斯底里的脑袋就是那样给烧坏的了。围拢的人们议论纷纷,但没有人提出异见。看来大家也同意马尼的说法。班里称为化妆帮的女孩群体的头头,即是那个叫做小磨的指甲刀女生,提出说:也许该给她检验一下,证明她的身分,如果不是人物的话,就好好教训她一顿,然后把她赶走!她的随从唇膏手艳艳,平时没精打采,这时却立即张着泥色的大口附和说:对啊,绝不能容忍可恶的人类生活在我们中间,要把她赶出去!其他人开始此起彼落地喊好。马尼得意洋洋地在巴士梯级上舞动双手,带领大家喊着公民教育宣传片的口号:“人物法则,不容有失!”也许因为太忘形,又没戴上凹镜,马尼突然摔了一跤,滑倒下来。 这时有人在栩栩肩上拍了一下,一只指尖镶满细薄吉他扫子的手把她向后拉。她及时止住了惊叫,发现原来是红发女孩。对方示意栩栩跟她走,拐了个弯来到安全的地方,女孩才小声说:我不知道你是人不是,但你最好小心点,你刚才已经听见他们说什么吧,小磨那帮人什么也做得出,千万别惹她们,她们会对你不利,到时没有人能帮你!你自己当心点!记住,这里是人物的世界!人物世界有人物世界的法则。说罢,女孩轻轻推了栩栩的肩膀一下,转身离去。栩栩连忙追问道:喂!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你在班里总是不出声,也没有人和你说话?你想不想交个朋友?红发女孩回头,说:我和你一样,在班里并不存在。栩栩问:哪你叫什么名字?对方说:苹果,不是苹果。栩栩再问:是还是不是?她说:不是,不是苹果。女孩说完,一低头就从后巷的杂物堆间滑走了。 不是苹果的好意提醒结果还是没用。栩栩当天放学就在校门给小磨那帮人钉上了。她们共五个人,把栩栩胁持到废车场去,在旧巴士车厢里,对她进行审问。小磨扭着栩栩的右手,亮出指甲锉,在栩栩细长的手指间轻轻磨磋着,一边说:大眼妹马尼说得没错,你们看,这么幼滑的手,怎会不是真的?真令人讨厌死了!除非,可以割开来看看里面藏的是什么东西啦!说着,指甲锉的尖端画向栩栩的手腕,皮肤浅浅地随着压力凹陷下去,仿佛随时也会破开来。栩栩咬着牙,死也不要叫痛。小磨瞅着栩栩的神情,突然收回指甲锉,朗声笑出来,说:来,剪碎她的裙子,看看她里面是什么东西!你们猜,会不会在肚脐这里有个夹万锁匙孔?还是,再往下一点?其他人也附和着大笑起来。栩栩想挣脱,立即就给按回去。小磨换上剪刀,在栩栩的鼻尖前晃动着,邪气地笑起来,说:看!还有这双眼睛,像珍珠的一样的眼睛,真教人妒忌啊!同伴们,告诉你们,我们天天拼命妆扮自己,也及不上这双珍珠眼睛呢!世界真是不公平!栩栩闭上眼,想辩解说,她胸口里有个八音盒,但她说不出口,因为这连她自己也不敢肯定。 小磨把刀锋移向栩栩的胸口,挑起水手领带,正要剪下去之际,不知是谁却在大家身后喊说:你们看不到她头上的意大利面吗?这声音听似柔弱,却明显以很大的力气喊出。女生们都停了手,回头看个究竟。躺在车厢椅子上的栩栩看见一个天使般的孩子站在巴士门闸内,长着手指笔的双手有点紧张地抓着门柱,洁白的男生恤衫和女儿气的肤色仿佛萤放着奇妙的亮光。小磨扭着脖子向闯入者骂道:小鬼你是谁?别多管闲事,不然把你一起宰掉!小男生吸了口大气,指着自己的头发,再用那柔和而坚定的声音说了一遍:你们不知道,她的头发是意大利面吗?根据人物法则,头发是意大利面也算合法吧!唇膏手艳艳弹了弹栩栩的辫子,说:这像意大利面?骗三岁小孩就可以!小男生坚持说:不信的话你剪一截给我。女生们相望了一下,小磨不耐烦地骂了句粗话,霍一声地把栩栩辫子末端剪了下来,向男生递出去。小男生步步为营地走近,伸出笔手抓住了那束碎发,二话不说就塞进口里,咀嚼了几下,好像在品尝着的样子,然后把几丝金黄色的东西吐在掌心里。就是这个!他说。黑色的头发变成金黄色面条,这真是难以置信。虽然事实摆在眼前,但大家也不服气。粉团面女生还嗤笑了一下,说:这么幼,是意大利面吗?男生把面条用笔尖挑起来,举半空中。垂下的面丝像柔滑的发,说:意大利面不是只有通心粉或者螺丝粉的啊,这叫做天使发幼面,Angel Hair,你们没有听过吗?小磨真的给激怒了!虽然好像真的从栩栩头上拿下意大利面来,但她还是要把她的厌恶和愤怒发泄出来。她命令说:天使又怎样?看我剪光她的头发来煮面吃!其他人立即听命把栩栩按下去。 看着女生们的野蛮行为,小男生真的着急了。要动手的话,他看来未必是五个凶恶女生的手脚,而且他完全不懂得打架。他无助地在空气中挥动着双手的笔枝,甚至不敢拿它们做临时武器。这时在窗子外面突然爆出一声怒吼,像强烈的气流一样把车厢摇撼着。大家瞬即静了下来。栩栩躺在那里,也不知发生什么事,只见恶女们突然退开,乖乖站直。不一会,一个黑影伴随着沉重的脚步声从门闸那边慢慢移过来。栩栩仰起脸,看见那是穿棕色猎装的训导主任。训导主任似乎有洞察任何事情的能力。他不用作出调查,就仿佛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一言不发,颤动着金丝框眼镜后面那双看不见眼珠的小眼,塌着嘴角,用右腕那根粗大的藤条仿似是有点温柔地抬高女生们的下巴,让他更清楚地看到她们的脸面。然后,又不发一言地转过身来,看着已经在椅子上坐直的栩栩。他非常仔细地端视她,然后抬起藤条,用前端轻轻碰了碰她给剪短了的右边辫子,用低沉的声音问:没事吧?栩栩瞪着眼睛,身子已在发抖,不懂答他。他也没等她回答,向那五个女生说:你们跟我来。那五个人像中了咒似的排成一列,跟着训导主任下车。当中有人一边走一边已经忍不住惊慌地哭起来。但那肯定不是小磨。 栩栩过了好一会才敢舒气,发现上天派来解救她的小神仙缩在另一边的椅子上。她说了声谢谢。小男生只懂耸肩。她心想,真是个蠢蛋,什么也不懂说。但她口里还是感激:你叫什么名字?他说:小冬。她想,这名字很熟。又问:你懂变法术的吗?你怎样可以把我的头发变成意大利面?他又耸肩,说:只要你把它想像成意大利面,它就是意大利面了。栩栩不明白,用手抚着自己的发辫,问:什么?难道这也是人物的法则?男生点点头说:也可以这样说!你把它想像成通心粉、螺丝粉、或者贝壳粉也可以,好像你用蝴蝶饼做耳朵一样。栩栩摇摇头,觉得这人的说话莫名其妙。叫小冬的男生就催她说:走吧,快点离开这里! 他们蹑足走出废车场的时候,天色已深蓝。晚风吹过一堆堆的废铁间,发出像兽的喘息一样的低鸣。栩栩觉得,兽在入夜后就会醒来。在一辆开篷跑车的车头盖上趴着那五个女生,校服裙掀到屁股上,暮色中苍白的大腿上布满不知是血污还是什么质料的斑痕。训导主任在砂地上沉默地来回踱步,仿似心血来潮地突然停下,向其中一个目标抽击。远远可以听见藤条破空的声音,和皮肉上的一下钝响,然后就是荒凉骇人的惨叫。 栩栩不期然抓紧小冬的手臂。她不知道,自己的右腕给小磨的指甲锉割开了小小的破口,但没有流血。 栩栩的学校生活比她想像中困难,但那不是关乎学科上的问题。栩栩完全不关心学业成绩,反正课堂上教的都是她不大懂的沉闷东西。她的挫败感,来自和同学的相处。上学后一个月,她还没有成功交到一个朋友。这和她的预期相距太远了。同学们都像有意回避她,冷待她,但又无时不在注视她,窥察她。这使她觉得自己是个怪物,浑身不自在。连那个看来友善的窗前小男生也不知为什么和她保持距离,常常一下课就不见了他的踪影。有时又无故缺课,望过去那位子空空的,只有尘粒在阳光中无聊地飘荡。栩栩想起就生气,觉得这小子一定是害怕别人的眼光,不敢和她交往。冇胆鬼!没用的家伙!娘娘腔!她在心里暗骂道。有时她不免怀疑,男生是从别的班级溜进来的,说不定他念的是中二或者中三。又说不定,其实是有易服癖的女孩子装的。栩栩也知道那红发滑轮女生在留意着她。每天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也会不经意地碰见她在身旁滑过,而且总是回过头来盯着自己。这女孩总是独来独往,从来不跟任何人说话,老师和同学对她也视若无睹。这反而令栩栩产生同感。栩栩觉得红发女生的盯视没有敌意,就算有敌意,她也愿意用善意去化解,所以她坚持每次也向她微笑,无论她的反应是如何冷淡。但意愿和决心还不足够,栩栩还要了解法则。这里是人物世界,人物世界自有它的法则。 更令栩栩沮丧的是,连老师也对她抱不信任的态度。要不就是像数学老师一样总是为难她,要她解答那些完全弄不懂的演算题,要不就是像生物老师一样,当她不存在似的,明知她举手发问却装作看不见。当然栩栩还未搞通她念的是文科还是理科。有一次,她还在走廊上给一个不认识的老师截停检查。这个男老师个子不高,剃了个陆军装,穿一身棕色猎装,手臂粗壮,皮肤黑实,却架一副斯文的金丝眼镜。他的右腕是一条像椅脚一样粗的藤条,一看就猜到是训导主任之类的人物。也许他从前是个猎人,手部是猎枪,加入教育界之后才改装作藤条。训导老师叫栩栩站直,问了她的班级,狐疑地上下检视她的全身。他用一双尖锐的小眼在她的脸上寻找线索,然后着她伸出双手,掌心向上打开。栩栩突然有一刻惶恐,以为他要用那可怕的武器向她脆弱的手掌施以痛击。但他只是拿左手捏了捏她的手指。不觉痛楚,指骨也没有给捏碎。倒是那根粗大的藤条,却撩了撩她的裙襬,又在她的腰部和臀部揩擦了几下。然后,训导主任就毫无表情地打发她走开。也许,训导主任只是试探她一下,但栩栩却涨红了脸。她觉得被冒犯了,但又不知怎样说出来。她整天也挥不去那腰身被硬物触碰的感觉,但那明明不过是一根藤条,又不是他的手,那又怎算被侵犯呢?可是,对人物来说,手和作为手的藤条又有什么分别?给一个男人的藤条或手碰过为什么又会产生这样的委屈感? 栩栩后来把这件事和妈妈说了。栩栩妈妈很忙,而且总在晚上才开始出外工作,但间中也会在栩栩下课回家之后和她出外上班之前有短暂的见面和交谈。不过,她们从不一起吃晚饭,通常妈妈给她准备好吃的东西就会出门,有时候甚至只是留下买晚饭的零钱。栩栩和妈妈说话的时候,妈妈总是在衣柜镜子前挑衣服。妈妈的衣服很多,而且都是鲜艳夺目的,但栩栩从不知道妈妈干什么工作要穿这样夸张的衣服。那些衣服尺码非常大,因为妈妈像河马一样肥胖。栩栩从未见过真正的河马,但她却想到这个比喻,而且仿佛了解河马的肥胖程度。如果问她河马有多胖,她会答,像妈妈一样胖。这不失为获得知识的方法之一种。奇怪的是栩栩却是非常地瘦,和妈妈没有半点相像之处。有时候她也会想像,自己老了会长得像妈妈一样胖,或者妈妈年轻时曾经和自己一样瘦,但两者同样不可思议。她也没有妈妈年轻时的照片或什么作证据。妈妈也从来不说关于工作的事。这属于栩栩从来也不知道的事情之一。也许是从来没问过,也许是问过而得不到答案,又或许是忘记了答案。她好像忘记了很多事情,例如从前自己究竟是怎样和妈妈相处。她怎样也想不起妈妈照顾自己,带自己去玩的片段,想不起自己的童年。她和妈妈好像才相处了一个月的时间,和她上学的时间相等。有时候栩栩不禁觉得,自己不过是寄养在这家里的。妈妈似乎没有做过什么一个妈妈该做的事。但问栩栩一个妈妈应该做些什么,栩栩又说不出来。所以,结果一切问题也不是问题,因为栩栩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也许,这样对她来说好些。栩栩不知道,她毕竟是个彻头彻尾的人物,而人物和真人不同。真人必定有过去,无论她记得与否,但人物却不一定。没有交代的记忆和经历,也可以等于并未发生。这是人物法则之一。同理,只要一经说出,就等于发生了。这是颇为神奇的情况。 妈妈听栩栩说到训导主任的事,反应却出乎意料地强烈,不停追问着:他碰了你吗?他怎样碰你?碰了哪里?栩栩再三把事实复述,妈妈却好像还是听不懂似的,甚至吵着要到学校找那人算账,又嚷着转校什么的。从妈妈的反应,栩栩猜想母性的一项表现就是为着女儿有没有给人碰过这问题而发狂。但给碰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委屈感吗?反而是栩栩开始觉得妈妈有点小题大作了,尝试反过来安抚她说:他只不过是用藤条碰了碰我的腰,这里,这样轻轻一碰罢了,又不是用手摸我。妈妈竟然说:藤条就是他的手啊!有什么分别?你看,这不就是我的手吗?说罢,妈妈就开动了她右手的按摩器,两个像轮子般的塑料东西上下左右地转动着,继续训斥道:傻女!这东西就是手,看见吗,手就是这东西,你还不懂得这就是我们人物的道理吗?栩栩沉默不语,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这是人物法则之二。人物就是人物,不是人,也不是物,也不是非人非物,并且不能分开身上属于人的部分,和物的部分。妈妈察觉到女儿的反应,也沉默下来。她心中的气慢慢消了,但又不知该说些什么,仿佛也不太习惯当妈妈的角色,只有把女儿单薄的身体抱在怀中,拿按摩器在她垂下的双肩上轻轻揉搓着。房子里只有按摩器转动的声音,像午后爬行的蜗牛。栩栩突然觉得很疲倦,倚在妈妈那软沙发一样的怀里,半合上眼睛。她像说梦话似地问:妈妈,为什么我和别人好像有什么不同的?我是不是个人物?妈妈,我是什么造的?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不是你生的吗?为什么我身上没有别人都有的东西?为什么,我不记得以前的事?妈妈没有立即回答她,只是继续按摩她的肩,然后是她的手臂,和她的腿,一边喃喃地像催眠似地低语着:你这个傻瓜,我也不知为什么会养了个像你这样的女儿,这是谁的安排呢,你看看,你的身体是那么的真实,这样的腰,这样的手臂,这样的腿,简直像真人一样,叫人怎样相信呢,但你要相信妈妈的话,你是个不折不扣的人物,你终有一天会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构造,知道自己的来由,妈妈暂时不能说得太多,这会对你不好,这些东西是要留待自己去领会的,如果真的有人不信你,你就告诉他,你心口里有一个八音盒,这就是你的东西,知道吗?栩栩其实不知,她仿佛在做梦,在迷迷糊糊间点点头,无力地笑。 栩栩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天黑了,妈妈已经出门。栩栩疑惑着妈妈是不是真的说过那番话。她坐在镜子前,解开上衣钮扣。她尝试把耳朵贴到胸口上,但这当然不可能。她差点扭断自己的脖子。于是她唯有用手指在胸口上东按按西按按,探测里面有没有异物,又拼命呼吸空气,收扩胸腔,然后又拿硬面包捶打自己的肋骨,但也敲不出半声音乐来,更不用说确认体内藏着什么八音盒了。妈妈的话是真的吗?妈妈是真的吗?她咬了硬面包一口。至少面包是真的。很硬。 栩栩认为被排挤不是自己的错。她相信自己是个外向的女孩,内心充满善意,随时准备和别人交朋友。她觉得这是她自己个性,是自己一手掌握的事情。个性是不需要他人赋予的,不受他人的影响和摆布,也不必得到他人的认同。但她不知道,个性是人物法则之三。栩栩慢慢就会知道,人物必会因着各自的特征而有它特定的个性,而这个性会反过来变成人物的限制。这是个必须的学习过程,也是个痛苦的学习过程。也许,学习本身必然就是痛苦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及得上无知的快乐。 栩栩同时觉得十分孤独。一个外向而孤独的女孩,滋味异常难以言喻。每天在床上醒来,张开眼,就像第一天一样,她就确切地知道只有她自己一个明了此刻自己的感受。那就是栩栩所理解的自己。穿着校服裙,踩着单车,在起伏的路上平衡着身体,让脸庞和四肢的皮肤迎向河道上暖和的风和日渐干燥的阳光的快慰,也不会有人能分享。沿途看到的景色,无论美丑,也只属于她眼睛里的投影。就算是那个笨蛋天使般的小男生或者每天回头盯视的红发女孩,也不会体会到她心底的孤寂。她每天坐在课室的人堆里独自坚持着无用的微笑。小息的时候坐在间中坠落雀屎的树下啃咬硬面包。这些画面只有她自己一一自我欣赏。自觉让她倍感孤单,但这同时也是解除孤单,自我陪伴的方法。她尝试闭上眼,倾听自己心中的八音盒,有时好像真的听到,有时又像什么也没有。 那天,正当栩栩在学校礼堂后面的一个比较清静的角落里闭着眼睛,把自己的心跳想像成八音盒的叮叮咚咚的时候,却听见身后发出一个像打碎玻璃一样尖刺的声音。她的八音盒差点给吓坏了。后面就是毗邻学校的废车场,两者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围栏。那声音就是在围栏的另一边传来的。栩栩悄悄凑近木板的间隙,隐约窥见废车场的一角光景。在一辆破烂的旧双层巴士旁边聚拢了一群学生,看清楚原来是栩栩的同班同学。班里叫马尼的眼睛镶着一对厚厚放大镜片的女生,正站在巴士上车口的梯级上,挥动着一副凹透镜眼镜,向下面的人宣示着什么重大的事情。这时她大概看不见任何东西,因为她的放大眼只适宜看半尺以内的事物,而平时得配戴凹镜眼镜来矫正视力。在班上,马尼总是出其不意地向栩栩凑过来,鼻子差不多要碰上她的脸,用她那双看久了要教人晕眩的大眼上上下下地搜索。这绝对算不上是礼貌的举动。因为马尼的声音尖厉,所以栩栩在围栏后面听得很清楚,她在说:我敢肯定,她不是个人物!我看得一清二楚,没有东西可以瞒得过我马尼的眼睛,她的皮肤绝不可能是假的,那样嫩滑得可厌的皮肤!她绝对不是个人物,她是人!真正的人!说罢,马尼仰脸向天,仿佛藉此加强言辞的效果。栩栩担心阳光会在马尼的放大眼里聚焦。也许她歇斯底里的脑袋就是那样给烧坏的了。围拢的人们议论纷纷,但没有人提出异见。看来大家也同意马尼的说法。班里称为化妆帮的女孩群体的头头,即是那个叫做小磨的指甲刀女生,提出说:也许该给她检验一下,证明她的身分,如果不是人物的话,就好好教训她一顿,然后把她赶走!她的随从唇膏手艳艳,平时没精打采,这时却立即张着泥色的大口附和说:对啊,绝不能容忍可恶的人类生活在我们中间,要把她赶出去!其他人开始此起彼落地喊好。马尼得意洋洋地在巴士梯级上舞动双手,带领大家喊着公民教育宣传片的口号:“人物法则,不容有失!”也许因为太忘形,又没戴上凹镜,马尼突然摔了一跤,滑倒下来。 这时有人在栩栩肩上拍了一下,一只指尖镶满细薄吉他扫子的手把她向后拉。她及时止住了惊叫,发现原来是红发女孩。对方示意栩栩跟她走,拐了个弯来到安全的地方,女孩才小声说:我不知道你是人不是,但你最好小心点,你刚才已经听见他们说什么吧,小磨那帮人什么也做得出,千万别惹她们,她们会对你不利,到时没有人能帮你!你自己当心点!记住,这里是人物的世界!人物世界有人物世界的法则。说罢,女孩轻轻推了栩栩的肩膀一下,转身离去。栩栩连忙追问道:喂!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你在班里总是不出声,也没有人和你说话?你想不想交个朋友?红发女孩回头,说:我和你一样,在班里并不存在。栩栩问:哪你叫什么名字?对方说:苹果,不是苹果。栩栩再问:是还是不是?她说:不是,不是苹果。女孩说完,一低头就从后巷的杂物堆间滑走了。 不是苹果的好意提醒结果还是没用。栩栩当天放学就在校门给小磨那帮人钉上了。她们共五个人,把栩栩胁持到废车场去,在旧巴士车厢里,对她进行审问。小磨扭着栩栩的右手,亮出指甲锉,在栩栩细长的手指间轻轻磨磋着,一边说:大眼妹马尼说得没错,你们看,这么幼滑的手,怎会不是真的?真令人讨厌死了!除非,可以割开来看看里面藏的是什么东西啦!说着,指甲锉的尖端画向栩栩的手腕,皮肤浅浅地随着压力凹陷下去,仿佛随时也会破开来。栩栩咬着牙,死也不要叫痛。小磨瞅着栩栩的神情,突然收回指甲锉,朗声笑出来,说:来,剪碎她的裙子,看看她里面是什么东西!你们猜,会不会在肚脐这里有个夹万锁匙孔?还是,再往下一点?其他人也附和着大笑起来。栩栩想挣脱,立即就给按回去。小磨换上剪刀,在栩栩的鼻尖前晃动着,邪气地笑起来,说:看!还有这双眼睛,像珍珠的一样的眼睛,真教人妒忌啊!同伴们,告诉你们,我们天天拼命妆扮自己,也及不上这双珍珠眼睛呢!世界真是不公平!栩栩闭上眼,想辩解说,她胸口里有个八音盒,但她说不出口,因为这连她自己也不敢肯定。 小磨把刀锋移向栩栩的胸口,挑起水手领带,正要剪下去之际,不知是谁却在大家身后喊说:你们看不到她头上的意大利面吗?这声音听似柔弱,却明显以很大的力气喊出。女生们都停了手,回头看个究竟。躺在车厢椅子上的栩栩看见一个天使般的孩子站在巴士门闸内,长着手指笔的双手有点紧张地抓着门柱,洁白的男生恤衫和女儿气的肤色仿佛萤放着奇妙的亮光。小磨扭着脖子向闯入者骂道:小鬼你是谁?别多管闲事,不然把你一起宰掉!小男生吸了口大气,指着自己的头发,再用那柔和而坚定的声音说了一遍:你们不知道,她的头发是意大利面吗?根据人物法则,头发是意大利面也算合法吧!唇膏手艳艳弹了弹栩栩的辫子,说:这像意大利面?骗三岁小孩就可以!小男生坚持说:不信的话你剪一截给我。女生们相望了一下,小磨不耐烦地骂了句粗话,霍一声地把栩栩辫子末端剪了下来,向男生递出去。小男生步步为营地走近,伸出笔手抓住了那束碎发,二话不说就塞进口里,咀嚼了几下,好像在品尝着的样子,然后把几丝金黄色的东西吐在掌心里。就是这个!他说。黑色的头发变成金黄色面条,这真是难以置信。虽然事实摆在眼前,但大家也不服气。粉团面女生还嗤笑了一下,说:这么幼,是意大利面吗?男生把面条用笔尖挑起来,举半空中。垂下的面丝像柔滑的发,说:意大利面不是只有通心粉或者螺丝粉的啊,这叫做天使发幼面,Angel Hair,你们没有听过吗?小磨真的给激怒了!虽然好像真的从栩栩头上拿下意大利面来,但她还是要把她的厌恶和愤怒发泄出来。她命令说:天使又怎样?看我剪光她的头发来煮面吃!其他人立即听命把栩栩按下去。 看着女生们的野蛮行为,小男生真的着急了。要动手的话,他看来未必是五个凶恶女生的手脚,而且他完全不懂得打架。他无助地在空气中挥动着双手的笔枝,甚至不敢拿它们做临时武器。这时在窗子外面突然爆出一声怒吼,像强烈的气流一样把车厢摇撼着。大家瞬即静了下来。栩栩躺在那里,也不知发生什么事,只见恶女们突然退开,乖乖站直。不一会,一个黑影伴随着沉重的脚步声从门闸那边慢慢移过来。栩栩仰起脸,看见那是穿棕色猎装的训导主任。训导主任似乎有洞察任何事情的能力。他不用作出调查,就仿佛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一言不发,颤动着金丝框眼镜后面那双看不见眼珠的小眼,塌着嘴角,用右腕那根粗大的藤条仿似是有点温柔地抬高女生们的下巴,让他更清楚地看到她们的脸面。然后,又不发一言地转过身来,看着已经在椅子上坐直的栩栩。他非常仔细地端视她,然后抬起藤条,用前端轻轻碰了碰她给剪短了的右边辫子,用低沉的声音问:没事吧?栩栩瞪着眼睛,身子已在发抖,不懂答他。他也没等她回答,向那五个女生说:你们跟我来。那五个人像中了咒似的排成一列,跟着训导主任下车。当中有人一边走一边已经忍不住惊慌地哭起来。但那肯定不是小磨。 栩栩过了好一会才敢舒气,发现上天派来解救她的小神仙缩在另一边的椅子上。她说了声谢谢。小男生只懂耸肩。她心想,真是个蠢蛋,什么也不懂说。但她口里还是感激:你叫什么名字?他说:小冬。她想,这名字很熟。又问:你懂变法术的吗?你怎样可以把我的头发变成意大利面?他又耸肩,说:只要你把它想像成意大利面,它就是意大利面了。栩栩不明白,用手抚着自己的发辫,问:什么?难道这也是人物的法则?男生点点头说:也可以这样说!你把它想像成通心粉、螺丝粉、或者贝壳粉也可以,好像你用蝴蝶饼做耳朵一样。栩栩摇摇头,觉得这人的说话莫名其妙。叫小冬的男生就催她说:走吧,快点离开这里! 他们蹑足走出废车场的时候,天色已深蓝。晚风吹过一堆堆的废铁间,发出像兽的喘息一样的低鸣。栩栩觉得,兽在入夜后就会醒来。在一辆开篷跑车的车头盖上趴着那五个女生,校服裙掀到屁股上,暮色中苍白的大腿上布满不知是血污还是什么质料的斑痕。训导主任在砂地上沉默地来回踱步,仿似心血来潮地突然停下,向其中一个目标抽击。远远可以听见藤条破空的声音,和皮肉上的一下钝响,然后就是荒凉骇人的惨叫。 栩栩不期然抓紧小冬的手臂。她不知道,自己的右腕给小磨的指甲锉割开了小小的破口,但没有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