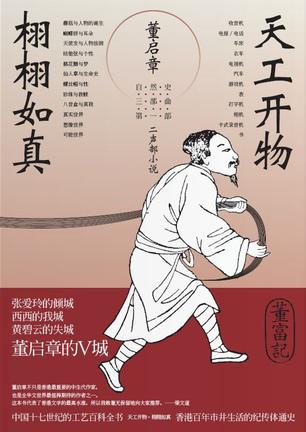栩栩第一天上学没有迟到。她穿了簇新的校服裙,挂了个布袋,里面装了入学证明、文具和午餐吃的硬面包。那是一条浅灰色的一件式校服裙,领口打深灰色水手领带,没有腰带,穿在身上松松的,让她看来有点稚气。要画出来的话,就是一个锐角三角形身子,火柴枝手脚,上面加一张圆圈脸,再在圆圈左右两边添上孖辫子,和辫子尾端的蝴蝶结。当然,不能漏掉圆圈脸上的弯弯嘴巴。那是栩栩决心挂上的微笑。她在临出门前,对着镜子,做出弯弯嘴巴的微笑,然后和自己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笑。所以,从坐上轻型电车,穿过市中心,来到市郊的桥头下车,栩栩也自觉到自己的嘴巴在微微弯着的模样。栩栩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有太强的自觉,仿佛在一直照着镜子,一直在心里注视着一个自己一样。 栩栩在桥前站下车,越过路轨来到桥头。给晨光灼热的地面冒起隐隐的暖流,掀动了她的裙裾,仿佛把身子轻轻承托起来。她迈开一高一低的大步,空空的布袋在她胁下晃动。她没有带书,因为还未有书单。她的侧腰很清楚地感觉到布袋里的硬面包的形状,她竟然为这个而感到快意。桥下的河水涨满而沉静地流向市镇中心。水一定是从山区那边来,她想,最后会流入市区另一面的海湾。她有点奇怪,她好像很熟悉这个地方,但又像今天才第一次在这里生活。水道下面有人站在浅水处用鱼网捞鱼,远远看去那圆篮形鱼网就像是那人的手部,但也许是由于水面反射的刺眼鳞光造成的假象。那究竟是手还是鱼网?其实栩栩在电车上已经察觉到自己和其他乘客有点不一样,但她只是以微笑来打消心里的疑惑,只是向自己说:无论如何,这一定是个正常的世界。正如她醒来发现自己,发现阳光,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 过了桥再沿着水道旁的小路走到尽头,就是学校所在。栩栩盘算着,如果有一辆单车,从家里大概不用十分钟就回到学校。栩栩觉得自己是懂得踩单车的,但她记不起踩单车是怎样的感觉。她抬起头望向远处。沐在晨光中的浅灰色校舍加倍地暴露着它的残旧,和小路旁边的废车场仿佛连成一体。废车场里层层堆栈的锈铁像沉睡的猛兽,却在人冷不防的时候闪烁出剌眼的反光,在视野里烧出青花花的斑点。栩栩低下头,嘴角还是微笑着,心里却隐隐觉得这景象似曾相识。她的额角开始冒出汗来了。 路上拥簇着穿着相同校服的同学,男的穿单调的白色短袖恤衫和灰长裤,女的和栩栩一样穿一件过浅灰校服裙。栩栩留意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想向别人显示她的善意,但大家只顾着低头默默前行,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异样。在人群中,栩栩的确异样。只要顺着栩栩的目光,就会看见,路上的人也有着和栩栩颇为不同的身体构造。有人晃摆着由乒乓球拍造成的双手,一边走路一边纯熟地左右传打乒乓球,像在练习某种杂技。有人的嘴巴生成哨子的模样,喘气时吹出轻微的颗粒状的尖锐鸣声。有人的脑袋是个圆身玻璃花瓶,里面放满了彩色透明玻璃珠子,还用水栽种着茂盛的万年青,下垂的茎叶像一把浓密的绿发,但代价是必须走得很慢,和有很好的平衡感。有一个男生差不多连校服也穿不上,腹部的恤衫钮扣也爆开了,露出胀胀的牛皮鼓肚子,书包在鼓沿上敲出一下一下的闷响。栩栩还未弄明白眼前的一切,但令她更奇怪的是,她并没有对身旁人们的模样感到大惊小怪,反而觉得一切最自然不过,仿佛她早就接受了这才是常态。倒是她自己在途人中显得古怪而突兀。她偷偷用手隔着裙子捏了捏自己的大腿,想起刚才睡醒时在床上的触觉,不期然想到,在这层肌肤下面,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构造。她既然生活在这里,她不可能和其他人不同。她记得入学证上“人物身分”一栏明明印着“确认”。至于“人物资料”一栏,则有性别:女;出生地:V镇;年龄:十七岁。但十七岁之前的学校生活,栩栩全无印象。她不记得自己以前的同学和老师,不记得自己学过什么,不记得学校是个做什么的地方,也不记得穿校服裙的感觉。一切是那么的新鲜,但又那么理所当然。 栩栩身后突然响起一阵惊叫。一个脚下踏着滑轮溜冰鞋的女生从后高速冲前,把人群驱散,有一个走避不及的低年班男生还给推倒在地。不,栩栩立刻就看出,这个女生不是穿着滑轮溜冰鞋,她的双脚就是底部装有一排滑轮的鞋子。这完全符合周围的人物的身体特征。那个倒地的男生矮矮胖胖,左手是个塑料水壶,右手则是个金属食物盒。水壶和食物盒自然不能胜任手的功能,男生只有趴在地上笨笨的没法把身体支撑起来,旁人却都视而不见,没有帮他一把。栩栩见状就上前扶他。这时滑轮女生突然煞住,转过头来。栩栩站起来,发现自己正和那女生相对而视。栩栩尝试向对方友善一笑。对方枣红色的头发像给风吹乱,散落在脸上和颈旁,校服裙明显经过改短,袒露着的整条腿白白地晃亮,直至没入红色的滑轮溜冰鞋鞋筒。她在背上斜挂着红色电吉他,左手拉着胸前的吉他带子,右手垂着,微微张开的五指不知是戴满了尖尖的薄片还是蓄满长指甲。这怎样看也不像是上学应有的装扮。红发女生上下打量着栩栩,仿佛把她身上的每个部分也检视了一遍,然后晃了晃脑袋,甩了甩零乱的头发,用尖长的指端挑开绞在一起的发丝,目光却一直盯着栩栩不放。栩栩开始觉得有点不自在了,但又说不出是为什么。她决不收回笑容,有点不自然地抿着嘴,回避地左右望望。半晌,那女生才慢慢转身滑走了,过了不远又回头看了她一眼。栩栩和自己暗笑了一下,再迈开步向校门前进。她开始觉得旁人都在以奇怪的目光注视自己。 那种目光甚至在校长眼中出现,虽然那只是极短促的一瞬间。校长室空旷得有点过分,加上那张以乒乓球桌充当的办公桌,看起来更像个室内运动场。光线照明却明显不良,若非早晨阳光刚好从窗子射进,斜斜投落在球桌上,栩栩一定会很难看清楚校长的样子。校长是个大个子,像那种喜爱懒洋洋地躺在大石块上晒太阳的巨型海狮,伸着一个吸尘机模样的嘴巴,嘴沿长满胡须一样的毛刷,刷毛上沾满了看来像饼干碎屑的颗粒。校长的眼睛却是一双感应器,透过眼镜投射出混浊的红色光线。他拿着栩栩的入学证明书,摘下厚厚的眼镜,从裤袋里抽出皱巴巴的手帕擦了擦,戴回,又再向文件扫描一遍。然后,他抬头端详着栩栩,两点小萤火虫似的红光在她的额上移动着,沿着眼睛,鼻子,嘴巴,停在她弯起的嘴角,再到达下巴,脖子,落到她的胸口却移到旁边去,在她纤细的手臂上爬行,令人看着也觉痕痒。栩栩就在这时看到校长眼中的奇怪闪烁。她心里有点害怕,保持微笑的嘴角开始歪斜,胸口有点紧束,就垂下眼,盯着乒乓球桌。她发现一列细小的黄蚂蚁正沿着桌边的白线横过阳光照明地带,作九十度拐弯,进入阴影区,顺着球桌中央分隔线向着校长跟前的一个金属罐进发。 正当栩栩看得入神,校长突然打破沉默,声音出乎意料地年轻和响亮,说:栩栩,文件没问题,你可以正式入学了,你喜欢读哪一班?中四,中五,还是中六?文科还是理科?栩栩连忙抬起头,看见校长的眼光变成温和的淡红色。她不懂怎样回答,她不知道选择班级是这么随便的。校长见她没说话,就说:那就暂时加入中六甲文科试试吧,还是和同龄同学一起上课较好,希望程度跟得上啦。栩栩不明所以,但还是滚着眼睛笑着点点头。校长不知为何突然朗声大笑,笑声仿佛要把天花板剥落的石灰像雪花般震下来。他把文件交还给栩栩,打开面前的罐子,拿出一块蝴蝶饼,递给栩栩,说:请你吃吧,当是入学礼物,不过,千万别说出去啊!说罢,把饼罐鬼鬼祟祟地藏到桌子下面去。栩栩拈着饼,不知该不该立刻当面吃掉。她觉得应该提醒校长蚂蚁的威胁,于是指着桌子上的蚁迹,说:校长,看看这个。校长摘下眼镜,凑近桌沿细察,两点红光立刻锁定了蚂蚁的位置,忽然从口里发出刷的一声,吸尘机嘴巴往桌面一扫,就把蚂蚁吸干净了。他捋了捋胡子,掸走残余的蚁尸,瞇着眼看看四周,自言自语地说:这间学校迟早要给蚂蚁吃光了。 校长亲自带栩栩到六甲班的课室,向同学作了介绍,嘱咐大家好好相处。栩栩被安排坐在前面最近黑板的空座位上。这通常是最不受欢迎的位置,但栩栩没所谓。她坐下之前不忘向同学点头微笑,而且立即发现在上学途中遇到的那个红发女孩正坐在角落里,斜斜瞟着她。老师是个前额光秃的中年男子,眼镜片翻到镜框上去,样子趣怪,左手是一排各式尺子,有金属长尺、胶尺、角度尺、三角尺等等,右手则是一个巨型圆规,一端是有点吓人的粗大针脚,另一端是钳子,可以夹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黑板上画满数式和几何图案。栩栩没有书,悄悄看看四周,同学桌上也没有书。大家也在忙着做自己的事情,有人在玩掌上游戏机,有人在肚子里的多士炉烘面包,有人在看另一个同学脸上的小型电视机。红发女孩坐在最后,栩栩没法转身看她在做什么。她倒察觉到,一个坐窗边的男生有着笔形手指,托着头向着本子在沉思,五枝笔管贴着脸庞,笔尖没入久未修剪的乱发里。男生个子瘦小,样子稚气,年纪仿佛比同班同学稍幼,但也很难说定。因为体格纤小,皮肤白嫩,眼睛被长长的睫毛盖着,头发又长,所以要不是穿着男生校服,栩栩还以为是个女生。斑斑日光透过树叶投下来,给他的发沿镶上薄薄的金边,连在他头顶空气中悠转着的尘埃,也像仙子撒下的金粉,让他看起来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精灵,或者投影机投射在墙上的没有实质的幻影。栩栩想,像他多好,可以安静地浸沉于白日梦里。男生不经意地抬头望过来,又或者他其实知道栩栩在看他。总之,他和栩栩的目光短促地碰了一下,然后是他首先避开,低头继续他的神游。栩栩觉得他很眼熟,但又不知道哪里见过。回头看看另外这边,有几个女生专注地对着镜子在化妆。栩栩不知道她们忙些什么,也许她们一天到晚也在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有一个用右手的指甲刀给左手修甲,一个用粉扫在干白得像面粉团的脸上擦个没完,另一个提着细长的眉笔手指在额头上描着弧形,看起来有点像黑板上的几何图案。坐栩栩旁边的女生左右手分别是五枝唇膏,像十个不同颜色的指头。她正小心翼翼地在唇上涂一种灰色的唇彩,嘴巴像吃了碳一样乌乌的。栩栩低声地问旁边这个同学:对不起,请问这不是文科班吗?为什么会教数学的?那女孩抬眼打量了栩栩一下,没精打采地张开黑碳口说:是啊!为什么呢?我也想知道!然后又继续向着镜子涂唇膏。栩栩坐正身子,望着黑板上的符号,扁了扁嘴。 小息的钟声一响起,同学们就在数学老师的带头下,像拔掉塞子的洗手盆里的污水一样,不消一刻就溜个光光。栩栩本来还想抓住一两个态度较友善的同学交个朋友,现在给遗弃在空空的课室里,心里有点沮丧。正想从布袋里掏出硬面包来咬两口发泄一下,发现校长送她的蝴蝶饼还在那里。蝴蝶饼已经断成两半,看起来像两只耳朵。栩栩试着把它们放在自己的耳朵上。这时后面突然传来一下笑声。栩栩连忙回头,看见原来还有一个同学留在课室里。是那个坐在窗前的貌似女生的小男孩。栩栩装作生气地问:有什么好笑?对方说:没什么。她又问:你留在这里做什么?刚才不是大家也溜光了吗?对方耸耸肩,没答话。她再问:你几多岁?样子这么小,你是念中六的吗?对方又耸耸肩。她决定不客气了,说:你为什么穿男生校服,你那么像女孩子!对方也只是耸耸肩。栩栩没好气,把蝴蝶饼充当耳朵,放在脸面两侧,向着那人做了个鬼脸,自己却忍不住笑了出来。对方也笨拙地笑了,嘴巴横向拉开像一条直线,突然又像想起什么似的,抬起食指位置的原子笔,低头在本子上慢慢写起来。手上另外四枝笔提在半空,随势上下摆动,像鸟拍翼。栩栩走近,问他:写什么?他却把本子的内容遮挡着,有点紧张地说:没什么。栩栩就说:你只懂说三个字的吗?想了想,又说:请你吃一半,好不好?说罢,把半块蝴蝶饼递给他。他迟疑了半晌,然后伸出两枝笔手指,一下子就把饼灵巧地夹着,说了声:谢谢。栩栩笑了,伸出手指算了一下,说:懂说四个字了!不阻你啦,小朋友!再见!她扬扬手,咬着另一半蝴蝶饼,径自走出课室去。栩栩自作聪明地暗想,打破僵局,见好就收,这样对方就会加倍想和她说话。而且,他欠了她半块蝴蝶饼。她下决心,她要在学校交到朋友。她喜欢被人喜欢的感觉。她不要和别人不同,不要被别人看成异类。 栩栩第一天上学没有迟到。她穿了簇新的校服裙,挂了个布袋,里面装了入学证明、文具和午餐吃的硬面包。那是一条浅灰色的一件式校服裙,领口打深灰色水手领带,没有腰带,穿在身上松松的,让她看来有点稚气。要画出来的话,就是一个锐角三角形身子,火柴枝手脚,上面加一张圆圈脸,再在圆圈左右两边添上孖辫子,和辫子尾端的蝴蝶结。当然,不能漏掉圆圈脸上的弯弯嘴巴。那是栩栩决心挂上的微笑。她在临出门前,对着镜子,做出弯弯嘴巴的微笑,然后和自己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笑。所以,从坐上轻型电车,穿过市中心,来到市郊的桥头下车,栩栩也自觉到自己的嘴巴在微微弯着的模样。栩栩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有太强的自觉,仿佛在一直照着镜子,一直在心里注视着一个自己一样。 栩栩在桥前站下车,越过路轨来到桥头。给晨光灼热的地面冒起隐隐的暖流,掀动了她的裙裾,仿佛把身子轻轻承托起来。她迈开一高一低的大步,空空的布袋在她胁下晃动。她没有带书,因为还未有书单。她的侧腰很清楚地感觉到布袋里的硬面包的形状,她竟然为这个而感到快意。桥下的河水涨满而沉静地流向市镇中心。水一定是从山区那边来,她想,最后会流入市区另一面的海湾。她有点奇怪,她好像很熟悉这个地方,但又像今天才第一次在这里生活。水道下面有人站在浅水处用鱼网捞鱼,远远看去那圆篮形鱼网就像是那人的手部,但也许是由于水面反射的刺眼鳞光造成的假象。那究竟是手还是鱼网?其实栩栩在电车上已经察觉到自己和其他乘客有点不一样,但她只是以微笑来打消心里的疑惑,只是向自己说:无论如何,这一定是个正常的世界。正如她醒来发现自己,发现阳光,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 过了桥再沿着水道旁的小路走到尽头,就是学校所在。栩栩盘算着,如果有一辆单车,从家里大概不用十分钟就回到学校。栩栩觉得自己是懂得踩单车的,但她记不起踩单车是怎样的感觉。她抬起头望向远处。沐在晨光中的浅灰色校舍加倍地暴露着它的残旧,和小路旁边的废车场仿佛连成一体。废车场里层层堆栈的锈铁像沉睡的猛兽,却在人冷不防的时候闪烁出剌眼的反光,在视野里烧出青花花的斑点。栩栩低下头,嘴角还是微笑着,心里却隐隐觉得这景象似曾相识。她的额角开始冒出汗来了。 路上拥簇着穿着相同校服的同学,男的穿单调的白色短袖恤衫和灰长裤,女的和栩栩一样穿一件过浅灰校服裙。栩栩留意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想向别人显示她的善意,但大家只顾着低头默默前行,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异样。在人群中,栩栩的确异样。只要顺着栩栩的目光,就会看见,路上的人也有着和栩栩颇为不同的身体构造。有人晃摆着由乒乓球拍造成的双手,一边走路一边纯熟地左右传打乒乓球,像在练习某种杂技。有人的嘴巴生成哨子的模样,喘气时吹出轻微的颗粒状的尖锐鸣声。有人的脑袋是个圆身玻璃花瓶,里面放满了彩色透明玻璃珠子,还用水栽种着茂盛的万年青,下垂的茎叶像一把浓密的绿发,但代价是必须走得很慢,和有很好的平衡感。有一个男生差不多连校服也穿不上,腹部的恤衫钮扣也爆开了,露出胀胀的牛皮鼓肚子,书包在鼓沿上敲出一下一下的闷响。栩栩还未弄明白眼前的一切,但令她更奇怪的是,她并没有对身旁人们的模样感到大惊小怪,反而觉得一切最自然不过,仿佛她早就接受了这才是常态。倒是她自己在途人中显得古怪而突兀。她偷偷用手隔着裙子捏了捏自己的大腿,想起刚才睡醒时在床上的触觉,不期然想到,在这层肌肤下面,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构造。她既然生活在这里,她不可能和其他人不同。她记得入学证上“人物身分”一栏明明印着“确认”。至于“人物资料”一栏,则有性别:女;出生地:V镇;年龄:十七岁。但十七岁之前的学校生活,栩栩全无印象。她不记得自己以前的同学和老师,不记得自己学过什么,不记得学校是个做什么的地方,也不记得穿校服裙的感觉。一切是那么的新鲜,但又那么理所当然。 栩栩身后突然响起一阵惊叫。一个脚下踏着滑轮溜冰鞋的女生从后高速冲前,把人群驱散,有一个走避不及的低年班男生还给推倒在地。不,栩栩立刻就看出,这个女生不是穿着滑轮溜冰鞋,她的双脚就是底部装有一排滑轮的鞋子。这完全符合周围的人物的身体特征。那个倒地的男生矮矮胖胖,左手是个塑料水壶,右手则是个金属食物盒。水壶和食物盒自然不能胜任手的功能,男生只有趴在地上笨笨的没法把身体支撑起来,旁人却都视而不见,没有帮他一把。栩栩见状就上前扶他。这时滑轮女生突然煞住,转过头来。栩栩站起来,发现自己正和那女生相对而视。栩栩尝试向对方友善一笑。对方枣红色的头发像给风吹乱,散落在脸上和颈旁,校服裙明显经过改短,袒露着的整条腿白白地晃亮,直至没入红色的滑轮溜冰鞋鞋筒。她在背上斜挂着红色电吉他,左手拉着胸前的吉他带子,右手垂着,微微张开的五指不知是戴满了尖尖的薄片还是蓄满长指甲。这怎样看也不像是上学应有的装扮。红发女生上下打量着栩栩,仿佛把她身上的每个部分也检视了一遍,然后晃了晃脑袋,甩了甩零乱的头发,用尖长的指端挑开绞在一起的发丝,目光却一直盯着栩栩不放。栩栩开始觉得有点不自在了,但又说不出是为什么。她决不收回笑容,有点不自然地抿着嘴,回避地左右望望。半晌,那女生才慢慢转身滑走了,过了不远又回头看了她一眼。栩栩和自己暗笑了一下,再迈开步向校门前进。她开始觉得旁人都在以奇怪的目光注视自己。 那种目光甚至在校长眼中出现,虽然那只是极短促的一瞬间。校长室空旷得有点过分,加上那张以乒乓球桌充当的办公桌,看起来更像个室内运动场。光线照明却明显不良,若非早晨阳光刚好从窗子射进,斜斜投落在球桌上,栩栩一定会很难看清楚校长的样子。校长是个大个子,像那种喜爱懒洋洋地躺在大石块上晒太阳的巨型海狮,伸着一个吸尘机模样的嘴巴,嘴沿长满胡须一样的毛刷,刷毛上沾满了看来像饼干碎屑的颗粒。校长的眼睛却是一双感应器,透过眼镜投射出混浊的红色光线。他拿着栩栩的入学证明书,摘下厚厚的眼镜,从裤袋里抽出皱巴巴的手帕擦了擦,戴回,又再向文件扫描一遍。然后,他抬头端详着栩栩,两点小萤火虫似的红光在她的额上移动着,沿着眼睛,鼻子,嘴巴,停在她弯起的嘴角,再到达下巴,脖子,落到她的胸口却移到旁边去,在她纤细的手臂上爬行,令人看着也觉痕痒。栩栩就在这时看到校长眼中的奇怪闪烁。她心里有点害怕,保持微笑的嘴角开始歪斜,胸口有点紧束,就垂下眼,盯着乒乓球桌。她发现一列细小的黄蚂蚁正沿着桌边的白线横过阳光照明地带,作九十度拐弯,进入阴影区,顺着球桌中央分隔线向着校长跟前的一个金属罐进发。 正当栩栩看得入神,校长突然打破沉默,声音出乎意料地年轻和响亮,说:栩栩,文件没问题,你可以正式入学了,你喜欢读哪一班?中四,中五,还是中六?文科还是理科?栩栩连忙抬起头,看见校长的眼光变成温和的淡红色。她不懂怎样回答,她不知道选择班级是这么随便的。校长见她没说话,就说:那就暂时加入中六甲文科试试吧,还是和同龄同学一起上课较好,希望程度跟得上啦。栩栩不明所以,但还是滚着眼睛笑着点点头。校长不知为何突然朗声大笑,笑声仿佛要把天花板剥落的石灰像雪花般震下来。他把文件交还给栩栩,打开面前的罐子,拿出一块蝴蝶饼,递给栩栩,说:请你吃吧,当是入学礼物,不过,千万别说出去啊!说罢,把饼罐鬼鬼祟祟地藏到桌子下面去。栩栩拈着饼,不知该不该立刻当面吃掉。她觉得应该提醒校长蚂蚁的威胁,于是指着桌子上的蚁迹,说:校长,看看这个。校长摘下眼镜,凑近桌沿细察,两点红光立刻锁定了蚂蚁的位置,忽然从口里发出刷的一声,吸尘机嘴巴往桌面一扫,就把蚂蚁吸干净了。他捋了捋胡子,掸走残余的蚁尸,瞇着眼看看四周,自言自语地说:这间学校迟早要给蚂蚁吃光了。 校长亲自带栩栩到六甲班的课室,向同学作了介绍,嘱咐大家好好相处。栩栩被安排坐在前面最近黑板的空座位上。这通常是最不受欢迎的位置,但栩栩没所谓。她坐下之前不忘向同学点头微笑,而且立即发现在上学途中遇到的那个红发女孩正坐在角落里,斜斜瞟着她。老师是个前额光秃的中年男子,眼镜片翻到镜框上去,样子趣怪,左手是一排各式尺子,有金属长尺、胶尺、角度尺、三角尺等等,右手则是一个巨型圆规,一端是有点吓人的粗大针脚,另一端是钳子,可以夹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黑板上画满数式和几何图案。栩栩没有书,悄悄看看四周,同学桌上也没有书。大家也在忙着做自己的事情,有人在玩掌上游戏机,有人在肚子里的多士炉烘面包,有人在看另一个同学脸上的小型电视机。红发女孩坐在最后,栩栩没法转身看她在做什么。她倒察觉到,一个坐窗边的男生有着笔形手指,托着头向着本子在沉思,五枝笔管贴着脸庞,笔尖没入久未修剪的乱发里。男生个子瘦小,样子稚气,年纪仿佛比同班同学稍幼,但也很难说定。因为体格纤小,皮肤白嫩,眼睛被长长的睫毛盖着,头发又长,所以要不是穿着男生校服,栩栩还以为是个女生。斑斑日光透过树叶投下来,给他的发沿镶上薄薄的金边,连在他头顶空气中悠转着的尘埃,也像仙子撒下的金粉,让他看起来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精灵,或者投影机投射在墙上的没有实质的幻影。栩栩想,像他多好,可以安静地浸沉于白日梦里。男生不经意地抬头望过来,又或者他其实知道栩栩在看他。总之,他和栩栩的目光短促地碰了一下,然后是他首先避开,低头继续他的神游。栩栩觉得他很眼熟,但又不知道哪里见过。回头看看另外这边,有几个女生专注地对着镜子在化妆。栩栩不知道她们忙些什么,也许她们一天到晚也在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有一个用右手的指甲刀给左手修甲,一个用粉扫在干白得像面粉团的脸上擦个没完,另一个提着细长的眉笔手指在额头上描着弧形,看起来有点像黑板上的几何图案。坐栩栩旁边的女生左右手分别是五枝唇膏,像十个不同颜色的指头。她正小心翼翼地在唇上涂一种灰色的唇彩,嘴巴像吃了碳一样乌乌的。栩栩低声地问旁边这个同学:对不起,请问这不是文科班吗?为什么会教数学的?那女孩抬眼打量了栩栩一下,没精打采地张开黑碳口说:是啊!为什么呢?我也想知道!然后又继续向着镜子涂唇膏。栩栩坐正身子,望着黑板上的符号,扁了扁嘴。 小息的钟声一响起,同学们就在数学老师的带头下,像拔掉塞子的洗手盆里的污水一样,不消一刻就溜个光光。栩栩本来还想抓住一两个态度较友善的同学交个朋友,现在给遗弃在空空的课室里,心里有点沮丧。正想从布袋里掏出硬面包来咬两口发泄一下,发现校长送她的蝴蝶饼还在那里。蝴蝶饼已经断成两半,看起来像两只耳朵。栩栩试着把它们放在自己的耳朵上。这时后面突然传来一下笑声。栩栩连忙回头,看见原来还有一个同学留在课室里。是那个坐在窗前的貌似女生的小男孩。栩栩装作生气地问:有什么好笑?对方说:没什么。她又问:你留在这里做什么?刚才不是大家也溜光了吗?对方耸耸肩,没答话。她再问:你几多岁?样子这么小,你是念中六的吗?对方又耸耸肩。她决定不客气了,说:你为什么穿男生校服,你那么像女孩子!对方也只是耸耸肩。栩栩没好气,把蝴蝶饼充当耳朵,放在脸面两侧,向着那人做了个鬼脸,自己却忍不住笑了出来。对方也笨拙地笑了,嘴巴横向拉开像一条直线,突然又像想起什么似的,抬起食指位置的原子笔,低头在本子上慢慢写起来。手上另外四枝笔提在半空,随势上下摆动,像鸟拍翼。栩栩走近,问他:写什么?他却把本子的内容遮挡着,有点紧张地说:没什么。栩栩就说:你只懂说三个字的吗?想了想,又说:请你吃一半,好不好?说罢,把半块蝴蝶饼递给他。他迟疑了半晌,然后伸出两枝笔手指,一下子就把饼灵巧地夹着,说了声:谢谢。栩栩笑了,伸出手指算了一下,说:懂说四个字了!不阻你啦,小朋友!再见!她扬扬手,咬着另一半蝴蝶饼,径自走出课室去。栩栩自作聪明地暗想,打破僵局,见好就收,这样对方就会加倍想和她说话。而且,他欠了她半块蝴蝶饼。她下决心,她要在学校交到朋友。她喜欢被人喜欢的感觉。她不要和别人不同,不要被别人看成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