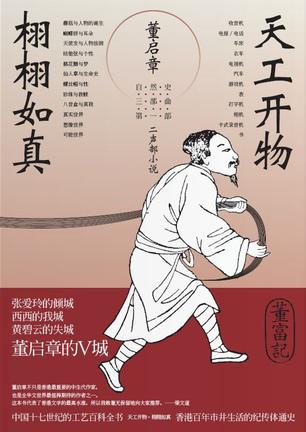栩栩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全身赤裸着。她迷迷糊糊地在单薄但温暖的被子里转侧了一下身体,擦过皮肤的空气抚扫出难以言喻的实在感,就像被丰润的流质包围着,充满着一样。抬起手臂遮挡着晨光,嘴角不自觉地勾起愉悦的形状。双臂支撑着身体坐起来,掀开被单,阳光瞬间盖下,呵烘着那瘦削的自己,泛着纯洁的光亮的自己。那就是自己啊。栩栩这样想,竟然觉得不可思议。她伸手摸了摸在床上直着的修长的腿。两腿间温热,有薄薄的汗。是真的呢。她想。 栩栩不记得自己昨晚为什么没有穿睡衣,或者什么时候脱下。她也不记得做过什么梦没有。一切就像从未发生过的那样新鲜。她耸起左肩,侧过脸嗅了嗅,皮肤有新鲜蘑菇的气味。她至少知道蘑菇这种又白又滑又香的小东西。想不到她生命里首先知道的少数事情之中,包括蘑菇的气味。但她不知道蕈菌类的生命稍纵即逝。 在栩栩少女的胸口上坠着一颗哑银色钢螺丝帽。钢螺丝帽呈六角形,拇指指甲大小,用细银链穿过帽洞,挂在脖子上。它的坚硬感和粗糙感,跟幼嫩的肉躯很不协调,在阳光下分外剌眼。栩栩用右手掌心把螺丝帽覆盖着,轻轻按在左胸口的肌肤上,用心跳来感受着那微冷的抵触。栩栩没有思索这东西的来由,她只凭直觉知道,在那隐隐发麻的一刻抵触中,自己真的活着。 就只是一刻的麻刺。然后钢螺丝帽慢慢变暖,不再异样,和肌肤融为一体。 睡衣摊开在床边,像在等待着穿它的身体。是条浅蓝碎花背心棉裙子,透薄的质料,像穿上夏日浅滩的清凉波浪。栩栩让身体钻进睡裙里,坐在床沿,望望四周。是那仿似熟悉的残旧小房间,和墙角上开始剥落的墙纸。墙纸上褪色的星星和月亮图案,仿佛在晨光中恢复了一点光彩。窗外还有鸟鸣。只要不看出去,就可以把这里想像作整个世界。但栩栩不用看也知道,窗外是乱糟糟的楼房,破落混杂的旧区街道。没有碧海,没有蓝天,没有星和月。也没有蘑菇。这个地区,就只有大清早最宁静,因为经过一整晚的喧嚣,谁都累倒了。大概只有她发现,早上有温暖的阳光和零星的鸟语。栩栩转头看看窗外,白花花的光,把灰黑都蒙住了。这很好。 栩栩自动地站起来,拉开睡房门。门是从里面上了锁的,但从里面一拉就开。她也没记起为什么要锁上门睡觉,但却觉得理所当然。狭小阴暗的客厅里没有人,只有赤裸脚掌压过松脱的地板的声音,和像按琴键般的上上落落的触觉。折台上放着隔夜硬面包,和一张纸条。栩栩捡起纸条,就在房门透进来的光线下,看到上面写着:“栩栩:记着今早是第一天,不要迟到,入学的文件在饭桌上,学校地址也在上面,上次告诉过你,你懂得去吧,本来第一天该陪你去,但晚上有工作,走不开,不能赶回来,很对不起。你要学懂照顾自己。桌上有面包。吃一份做早餐,带一份回学校吃。雪柜里有牛奶。今天晚上见。妈妈字。” 对啊,原来今天开始上学,而且,妈妈留下字条了。栩栩想。这至少肯定了两个事实。她玩味着“第一天”这三个字。 在浴室里,站在镜子前,栩栩端看着那张圆圆的脸,幼丝般垂在肩上的乱发,瘦削如竹枝的颈和手臂。那是自己的脸没错,理应感到熟悉,或者明白到,原来如此。她向它动了动嘴唇,轻若无声地说:栩栩,早晨啦!刚才纸条上明明写着给栩栩,那叫栩栩就没错。她也没有怀疑过,觉得必然如是。正如她没有怀疑过有一个妈妈,和妈妈在桌上留下字条给她。 栩栩。栩栩。她耳窝里早已植入这名字。 她看见镜子中的自己弯着嘴巴笑了。她决定,以后无论任何情形,栩栩都必须微笑。那是栩栩第一个自己做的决定。 她知道,这是栩栩的第一天。但她不知道为什么。她不知道,那是因为,这是故事的开始。在故事开始前,栩栩并不存在。栩栩诞生于第一个句子: 栩栩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全身赤裸着。 如果作者喜欢的话,栩栩还可以诞生第二次,第三次。但作者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正如真实生命一样,栩栩只可以活一次。否则,栩栩就不再是如真了。 栩栩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全身赤裸着。她迷迷糊糊地在单薄但温暖的被子里转侧了一下身体,擦过皮肤的空气抚扫出难以言喻的实在感,就像被丰润的流质包围着,充满着一样。抬起手臂遮挡着晨光,嘴角不自觉地勾起愉悦的形状。双臂支撑着身体坐起来,掀开被单,阳光瞬间盖下,呵烘着那瘦削的自己,泛着纯洁的光亮的自己。那就是自己啊。栩栩这样想,竟然觉得不可思议。她伸手摸了摸在床上直着的修长的腿。两腿间温热,有薄薄的汗。是真的呢。她想。 栩栩不记得自己昨晚为什么没有穿睡衣,或者什么时候脱下。她也不记得做过什么梦没有。一切就像从未发生过的那样新鲜。她耸起左肩,侧过脸嗅了嗅,皮肤有新鲜蘑菇的气味。她至少知道蘑菇这种又白又滑又香的小东西。想不到她生命里首先知道的少数事情之中,包括蘑菇的气味。但她不知道蕈菌类的生命稍纵即逝。 在栩栩少女的胸口上坠着一颗哑银色钢螺丝帽。钢螺丝帽呈六角形,拇指指甲大小,用细银链穿过帽洞,挂在脖子上。它的坚硬感和粗糙感,跟幼嫩的肉躯很不协调,在阳光下分外剌眼。栩栩用右手掌心把螺丝帽覆盖着,轻轻按在左胸口的肌肤上,用心跳来感受着那微冷的抵触。栩栩没有思索这东西的来由,她只凭直觉知道,在那隐隐发麻的一刻抵触中,自己真的活着。 就只是一刻的麻刺。然后钢螺丝帽慢慢变暖,不再异样,和肌肤融为一体。 睡衣摊开在床边,像在等待着穿它的身体。是条浅蓝碎花背心棉裙子,透薄的质料,像穿上夏日浅滩的清凉波浪。栩栩让身体钻进睡裙里,坐在床沿,望望四周。是那仿似熟悉的残旧小房间,和墙角上开始剥落的墙纸。墙纸上褪色的星星和月亮图案,仿佛在晨光中恢复了一点光彩。窗外还有鸟鸣。只要不看出去,就可以把这里想像作整个世界。但栩栩不用看也知道,窗外是乱糟糟的楼房,破落混杂的旧区街道。没有碧海,没有蓝天,没有星和月。也没有蘑菇。这个地区,就只有大清早最宁静,因为经过一整晚的喧嚣,谁都累倒了。大概只有她发现,早上有温暖的阳光和零星的鸟语。栩栩转头看看窗外,白花花的光,把灰黑都蒙住了。这很好。 栩栩自动地站起来,拉开睡房门。门是从里面上了锁的,但从里面一拉就开。她也没记起为什么要锁上门睡觉,但却觉得理所当然。狭小阴暗的客厅里没有人,只有赤裸脚掌压过松脱的地板的声音,和像按琴键般的上上落落的触觉。折台上放着隔夜硬面包,和一张纸条。栩栩捡起纸条,就在房门透进来的光线下,看到上面写着:“栩栩:记着今早是第一天,不要迟到,入学的文件在饭桌上,学校地址也在上面,上次告诉过你,你懂得去吧,本来第一天该陪你去,但晚上有工作,走不开,不能赶回来,很对不起。你要学懂照顾自己。桌上有面包。吃一份做早餐,带一份回学校吃。雪柜里有牛奶。今天晚上见。妈妈字。” 对啊,原来今天开始上学,而且,妈妈留下字条了。栩栩想。这至少肯定了两个事实。她玩味着“第一天”这三个字。 在浴室里,站在镜子前,栩栩端看着那张圆圆的脸,幼丝般垂在肩上的乱发,瘦削如竹枝的颈和手臂。那是自己的脸没错,理应感到熟悉,或者明白到,原来如此。她向它动了动嘴唇,轻若无声地说:栩栩,早晨啦!刚才纸条上明明写着给栩栩,那叫栩栩就没错。她也没有怀疑过,觉得必然如是。正如她没有怀疑过有一个妈妈,和妈妈在桌上留下字条给她。 栩栩。栩栩。她耳窝里早已植入这名字。 她看见镜子中的自己弯着嘴巴笑了。她决定,以后无论任何情形,栩栩都必须微笑。那是栩栩第一个自己做的决定。 她知道,这是栩栩的第一天。但她不知道为什么。她不知道,那是因为,这是故事的开始。在故事开始前,栩栩并不存在。栩栩诞生于第一个句子: 栩栩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全身赤裸着。 如果作者喜欢的话,栩栩还可以诞生第二次,第三次。但作者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正如真实生命一样,栩栩只可以活一次。否则,栩栩就不再是如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