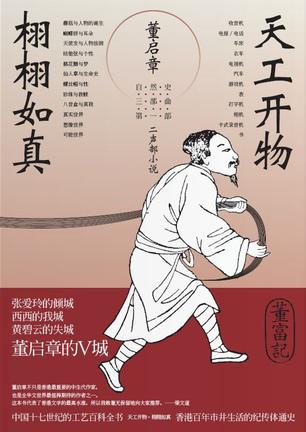独裁者 我和这本书的作者是同代人,这本书又是一部本城的文学作品。虽然这部作品因缘际遇在隔岸出版,但是据作者所说,他希望能由一位本城的同代作家执笔作序,所以就向我发出邀请。不过,我把这邀请理解为挑战。既然要把这本书作为一个挑战来响应,那么我将要说的话极可能是不中听的,但我相信作者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他早就知道,我和他的文学立场一直也存在差异。所以,我也不得不对他的勇敢表示敬佩。可是,敬意还敬意,要说的话也始终是要坦率地说出来的。在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互相忽视的文学界里,我们都失去了真诚之心。因此,这也可以说是个良机,去考验作者是不是的确具有实现真诚之心的勇气。 也许说到真诚并不恰当。要说真诚,我们能判断谁不是真诚的吗?我们既能真诚地互相关怀,但也能真诚地互相攻击。也许我们要求的其实是完整性——integrity——而当中也包含了正直和诚实。可是真正的完整性是多么的困难,甚至近乎无可企及。我们都难免于自我分裂,自相矛盾。在布满碎形裂片的汪洋中,我们浮游泅泳,寻找自我的,或同时是彼此的喻象——figure。在喻象当中,我们找到了至少是暂时性的,想像性的统一体。据我理解,这本书所标志的就是对这统一体的追求,和对其不可得的焦虑和失落。 直截了当地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是一本自我的书。作者企图通过主人公的家族承传和个人成长的叙述,来确立自我的形象。最终显现出来的是无限的自我膨胀,竟然到了一个除自我之外并无外部真实的地步。也因而没有他人的存在。所有“他人”——包括叙事者所创造的“人物”栩栩,以至他“真实”的父祖辈和成长伙伴们——几乎都只是包含在自我的想像中的角色。而他口中的“历史”——无论是对象史,家族史,还是地区史——也必然陷入了自我的偏见里。这偏见无关乎他的“史观”进步或正确与否,而在于本身角度的局限。要知道,每一个独裁者当初也必然曾经是个颠覆者,反权威者。而他的颠覆力往往只是建基于以一个更强劲的自我来推翻另一个已然疲弱和败坏的自我而已。就算作者表面上摆出许多反省的姿态,时刻装出商量和自我怀疑的语气,结果其实于事无补。在我们的文学中,这种伪反省可谓特别丰富。尤其是在关于“人物”栩栩的部分,作者在“作者-人物关系”的老话题上做文章,导引出哀怨而近乎滥情的结局,最后也不过是在自我的想像世界内部打转。自我的文学最终几乎都是造成思想短路。 我得承认,当我读到作者自称根据“滥情的美学”创造出来的情节和场面,我的确无法免于动容,但我也立即对自己的动容感到羞愧。我为自己产生的同情而羞愧,因为我竟然不自觉地被卷进作者的自我中。于是我不得不加倍警惕,以及加强对这自我的批判。读者可能会认为我说得过于苛刻。可是,难道我们不应该把要求的门坎提得高些吗?难道我们应该让一个作家轻易蒙混过去吗?也许有人会认为,在今天文学作品已经受尽冷落的年头,有人还旷日持久地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就算没功也有劳吧。那应该加以鼓励和肯定,而不是吹毛求疵,重手打击吧。我却绝对不会这样想。因为姑勿论有多少人在看,一部作品也是时代的象征,并背负着时代的责任。作品的缺憾也同时征表着时代的缺憾。这是不能敷衍了事的。当然,我真心地盼望作品能在严厉的批评中站得住脚,那表示当中还有什么是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能带来真正的启示。 作者在书中忧虑的,其实就是“无用”的想像和写作,如何能响应现实世界和现实人生的问题吧。于是就出现了“想像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分裂和对立,以及利用前者吸纳和创造后者的虚妄想法。就课题本身,也不能算是新鲜的,但当中的提问,却是恒常迫切和有效的。这牵涉到艺术行为的根本意义。创作和现实的关系其实从来没有割裂过。在艺术史中历来只是以不同的形态呈现,而所谓艺术形式和思潮的更替,也不过是两者关系的理解的重整。就算是声称“为艺术而艺术”的流派,其理念本身也无可避免地以对待现实的否定态度为依归。见诸小说这种形式,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的,无可否认是写实主义的那种对真实世界“实然”呈现的信念。而如果作者的使命感高度确切化,则会滑入宣示“应然”的说教窠臼。现在这本书的作者所标举的,却是可以称为“或然”的角度。所谓“所有的可能世界”,不就是相对于“实然”和“应然”的一种未完成的展望吗?而在“文字工场的想像模式”里,这些可能的展望不也同时是已经实现的吗?所以,据我理解,小说的“可能世界”是既未成形但又已经确立的,是既存在于想像但又实践于体验的。作者试图通过“可能”,来联系现实和想像。不过,“艺术作为一种可能体验的创造”并不是新观点。这本书稍为显出新意的,在于它把创作者的自我置放于多重的“可能”的中心,造成自我膨胀,也同时难免于自我分裂。“可能”于是就成为了时间,成为了体验的本质。它成为了主题,也成为了形式。 这本书的局限也正正在这里。它把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变成主题,但结果问题还是没法解答,或者取巧地省却了回答的必要。这就是自我的文学的必然困局和虚假性。“可能世界”可以是出路,但也可以是封闭回路。回到之前的说法,就是:究竟作者能不能达到完整性和一致性?这种完整性和一致性并不是指作品内部写得工工整整,时地人三元素统一的那种古典律的要求。它是指艺术和现实人生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就这样的问题,我自己也在思索和挣扎中,所以我丧失了批评的资格。或者,我根本就没有资格评论同代人的这本书,因为跟他一样,我自己也是个陷于自我而不能自拔的独裁者。我那自觉的“独裁者”称号并未能让我免于责难。 就这个我和同代人也无法回答的问题,让我暂且引述他人的见解,作为思考的踏脚点。俄国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在二十四岁的早慧之年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里,对艺术和人生表达了别具洞察力的看法。 艺术家和个人幼稚地,通常是机械地结合于一身;个人为了逃离“日常生活的困扰”而遁入艺术创作的领域,暂托于“灵感、甜美的声音、和祈祷”的另一个世界。结果如何呢?艺术变得过于自信,愚莽地自信,以及夸夸其谈,因为它无须对生活承担责任。相反,生活当然无从攀附这样的艺术。“那太高深哪!”生活说。“那是艺术啊!我们过的却只是卑微庸碌的生活。” 当个人置身于艺术,他就不在生活中,反之亦然。两者之间并没有统一性,在统一的个人身上也没有内部的互相渗透。 那么,是什么保证个人身上诸般因素的内在联系呢?只有责任的统一性。我必须以自身的生命响应我从艺术中所体验和理解的,好让我所体验和理解的所有东西不致于在我的人生中毫无作为。可是,责任必然包含罪过,或对谴责的承担。艺术和生活不单必须互相负责,还应该互相承担罪谴。诗人必须记着,生活的鄙俗平庸,是他的诗之罪过;日常生活之人则必须知道,艺术的徒劳无功,是由于他不愿意对生活认真和有所要求。 艺术与生活不是同一回事,但应在我身上统一起来,于统一的责任中。 在原文里,“责任”一词和“回应性”等义,即英文的answerability。 我必须就自己也身为一个作者,也即是一个独裁者的角度,去承认我和本书的作者所共同犯下的错误。从这个角度看,就等于说这本书是我自己所写的一样了。我们在彼此的自我的喻象里,找到虚幻的,暂时的一致性。至于真正的完整,也许,还要期望于自我的崩解,和对他人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