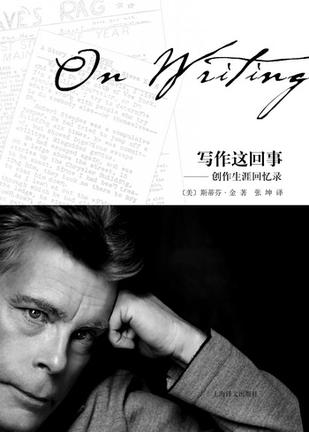修辞立其诚。 --塞万提斯 骗子发达。--匿名 斯蒂芬·金引述的塞万提斯的这句话英文作:Honestysthebestpolicy,与我们《易经》中的说法不谋而合。--译者(正文注释大多为译者所加,不再一一注明。)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也许是在1992年,但日子过得顺的话,人总是很难记清楚时间)我参加了一个主要由作家组成的摇滚乐队。"摇滚余孽"是凯茜·卡门·歌德马克创立的,她是一位旧金山出版家,也是位音乐家。乐队的首席吉他手是大卫·贝里,贝司手是雷德利·皮尔森,键盘手是芭芭拉·金索尔沃,罗伯特·福尔古姆演奏曼陀林,我负责节奏吉他。我们还有三位女歌手,人称甜筒三人组,通常是由凯茜、塔德·芭尔提姆丝,还有谭恩美共同组成。 当时乐队只打算做个一锤子买卖--我们想在全美书商大会上演出两场,逗大伙乐乐,用那三四个钟头的时间重温一番我们虚度的青春岁月,然后就各走各路。 结果不然,我们的乐队一直也没有彻底解散。我们发现我们都很享受一起演奏,不想退出,再说我们还有特邀萨克斯手和鼓手(还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位音乐领袖,艾尔·库伯,他是我们乐队的中心人物),做出来的音乐听起来还不错。会有人愿意花钱来听我们演奏。当然不会很贵,像U2或者E大街乐队那种票价,但是也许照老话说,出个天桥价儿还是有人肯的。我们乐队出去巡演,还写了本书(我太太给配的照片,情绪上来还给我们伴舞,她还经常情绪高涨),直到现在还时不时演一场,有时候叫"余孽",有时候叫"雷蒙·波的腿儿"。乐手来来去去--专栏作家米奇·阿尔本取代了键盘手芭芭拉,艾尔后来没有再跟乐队一起演奏,因为他跟凯茜处不来--可我们的核心人物一直在:凯茜、恩美、雷德利、大卫、米奇·阿尔本,还有我……再加上鼓手乔什·凯利和萨克斯手艾拉斯莫·鲍罗。 我们在一起是为了音乐,也是为了互相做伴。我们彼此都很喜欢,喜欢有机会偶尔能谈谈我们真正的工作,就是人人都告诉我们不要放弃的我们的全职工作。我们是作家,我们从来不问彼此写作的灵感从何而来,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 一天晚上,我们在迈阿密海滨的演出之前,一起吃中国菜,我问恩美在每次作家讲话之后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有没有什么问题从来没人问起过--当你站在一群狂热粉丝读者面前装腔作势,仿佛自己并非凡俗人物的时候,一直没有机会回答的问题。恩美顿了一下,认真考虑了半晌才回答说:"从来没人问过语言的问题。" 对于她的话,我怀有深刻的感激之情。一年以来,也许更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想要写一本小书,谈谈写作,却一直压制住了这个想法,因为我不信任自己的动机--为什么我会想谈写作?我凭什么认为自己有资格谈写作? 简单回答就是,一个像我这样卖出了许多小说的人对于写作一定有话说,值得说,但简单的回答并非总是正确。山德士上校卖出了那么多炸鸡,可我猜大概没几个人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如果我斗胆想告诉大家如何写作,我觉得必须有更站得住脚的理由,而不仅仅是我的书广受欢迎这么简单。换句话说,我不想写出一本书,哪怕是像这样很薄的一本小书,却落得个结果,感觉自己要么是个文学臭屁王,或者是个先验主义的混账。市场上这种书已经够多了--这种作家也够多了,谢谢,免了。 但恩美说得对:从来没人问起我们的语言。他们会问德里罗,问厄普代克,问斯塔隆,可他们决不会向流行作家提出这样的问题。可我们这些普罗大众也在意语言,虽说方式卑微,但我们仍然热切关注写故事的艺术和技巧。接下来,我就想把这一切简单明了地写下来,写写我怎么会做了这一行,现在对写作了解多少,我是怎么写的。关于我的全职工作,关于语言。 这本书献给谭恩美,是她用简单直率的方式告诉我,可以写这么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