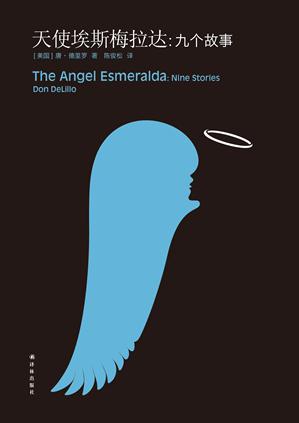关于福尔默的一点说明。他不再把地球描绘成图书馆里的地球仪或一张地图的实体,像一只凝视深层空间的宇宙之眼。这最后一条是他在意象创造方面最具雄心的尝试。战争已经改变了他看待地球的方式。用词典里严肃的术语来说,地球是由陆地和海洋构成的,是凡人的栖居之所。他不再将它视为(有盘旋的风暴、明亮的海洋、呼吸热气、烟雾和色彩)可用生动的语言来描绘、能闲来把玩或者思忖的对象。 在二百二十公里外,我们看到轮船的航迹和更大型的机场。冰山、闪电、沙丘。我指出熔岩流和冷心涡流。我告诉他,爱尔兰海岸边的银带是海面的浮油形成的。 这是我第三次执行轨道飞行任务,福尔默是第一次。他是个工程方面的天才,通讯和武器方面的天才,而且可能也是其他各方面的天才。作为太空任务专家,我很乐意当负责人。(专家这个词,在科罗拉多控制中心的标准用法里指的是并无专长的人。)我们的飞船主要是为搜集情报而设计。量子燃烧技术的改进使我们不用每次发射火箭就可以经常调整轨道。当我们摆向又高又宽的轨道上时,整个地球就成了我们的心灵之光,用来监视任何无人和可能出现的敌对卫星。我们紧贴着轨道飞行,状态舒适,仔细打量那些无人之境的地表活动。 核武器的禁止让世界上的战争变得安全了。 我尽量不去思考宏大的问题,或者陷入杂乱的抽象思索。但有时我也会突然产生这种冲动。地球轨道使人变得有些像哲学家了。我们怎么克制得住呢?我们能看到地球的全貌,我们在这里拥有特权般的视野。当我们希望配得起这种经历时,会不自觉地认真思考诸如人类的境况这种话题。像这样飘浮在大陆上空,能看到世界的边缘,让人觉得与宇宙一体。看到这条如同圆规画的弧线一样清楚的线条,知道它就是通往大西洋暮光的转折处,通向沉淀物卷流和海藻床,一条岛链在朦胧的海面上闪闪发光。 我告诉自己这只是景色而已。我想把我们在这里的生活看成平常事,就像家务安排一样,因住房短缺或春季峡谷洪水而造成的不太可能但尚且可行的安置。 福尔默完成系统检查清单后就去他的吊床休息了。他二十三岁,一个脑袋长、头发短的男孩。他一边把东西从私人物品包中取出,放到旁边的维可牢平台以便更仔细地察看,一边谈论明尼苏达州北部。我的私人物品包里有一枚1901年的银币。这是不怎么需要说明的。福尔默的物品包里有毕业照、瓶盖,还有他家后院里的小石子。我不清楚这些东西是他自己挑的,还是他父母因担心他在太空的生活缺少人性时刻而硬塞给他的。 我们的吊床能带来人性时刻,我觉得,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科罗拉多控制中心事先安排成这样的。我们要吃热狗和杏仁脆条,并抹上唇膏,这是睡前待办清单中的项目。我们在发射台前穿着拖鞋。福尔默的橄榄球运动衫也是人性时刻。特大号,紫色和白色,网状涤纶面料,印着79号,大个子的号,衣服底色并无任何特殊之处,这衣服让他显得背有点驼,身材长得不太正常。 “每到星期日我还是会沮丧。”他说。 “我们在这儿有星期日吗?” “没有,但是他们那儿有,而且我仍然能感觉得到。我永远能觉察到什么时候是星期日。” “你为什么会感到沮丧呢?” “星期日的悠缓。有关刺眼的阳光,温热的草坪的气味,教堂的礼拜,亲戚们穿着上好的衣服相互拜访。这一整天似乎没有尽头。” “我也不喜欢星期日。” “它们过得很慢,但不是懒散的慢。要么又长又热,要么又长又冷。在夏季,我奶奶自制柠檬水。这是惯例。一整天的生活似乎是预先安排好的,而且惯例从不改变。而太空轨道上的惯例则不同。它让人感到惬意。它让我们的时间有形体和实质。那些星期日是无形的,虽然你很清楚会发生什么、谁会前来拜访、大家会说什么。往往大家都没开口,你就已经知道每个人会说些什么。我是当中唯一的小孩。人们看到我都很开心。我常想躲起来。” “柠檬水有什么不好?”我问。 一颗战争侦测无人卫星报告:在轨道多洛雷斯区发现高能量的激光活动。我们取出我们的激光组件,花了半个小时研究它们。激光发射的程序相当复杂,而且控制台只有联合操作才能运行,所以我们必须极其小心地演练预先设定的几套措施。 关于地球的一点说明。地球是白昼和黑夜的保留地。它包含了合理而平衡的变化,自然的醒和睡的过程,或者对那些被剥夺了这种潮汐变化的人来说,看起来是这么回事。 因此福尔默关于明尼苏达州星期日的话才让我感到有趣。他仍然能感觉到,或声称他感觉到,或者认为他感觉到,那种地球上固有的节奏。 对于失去了这种节奏的人来说,似乎事物以它们特定的物质形态存在是为了揭示某些重大数学真理中隐藏的简单特性。地球向我们揭示了昼与夜中简单而绝妙的美。正是在那里包含并融合了这些观念上的事件。 福尔默穿着短裤和吸力木底鞋,活像个高中游泳运动员,几乎没有毛发,一个没成型的男人,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残忍的审视中,自己毫无办法,双臂交叉地站在一个充斥着回声和氯气味道的地方。他的声音里含有一点愚蠢。它太直接,是从口腔上部发出的低沉的声音, 有点逼人去注意,有点吵。福尔默在我面前从未说过什么蠢话。只是他的声音让人感觉很愚蠢,严肃而直率的低音,一种音调和气息都没有变化的声音。 我们在这儿并没有束缚感。飞行舱和宇航员休息区设计得很贴心。食物堪称美味。此外,还有书籍、录像带、新闻和音乐。我们要做手动检查清单、口头检查清单上的事,还有模拟发射,做这些事时既不乏味也不草率。要说的话,我们的工作状态一直都在提高。唯一的危险是对话。 我尽量使我们的对话仅限于日常话题。我特意只谈论一些小事、一些常规的事。对我来说这是明智之举。在目前的情况下,将我们的谈话限定在熟悉的话题、无关紧要的小事上,似乎是很合理的策略。我想建立起一个日常谈话的框架。但福尔默有不时提出宏大话题的倾向。他想谈论战争以及战争中的各种武器。他想讨论全球战略,全球侵略。我告诉他,既然他已不再将地球视为一只宇宙之眼,他是想把它看作一个游戏盘或者计算机模型了。他一本正经地看着我,希望能跟我来场理论上的辩论:是应该采取有选择的基于太空的攻击,还是采取持久的海陆空协同作战。他引用专家的观点,提到出处。我该说些什么呢?他会说战争已经让人们失望了。战争已经拖到第三个星期了。有一种它已耗尽了力气、走到了尽头的感觉。他从我们定期接收到的新闻报道中得出这个结论。播音员的声音里似乎暗示着对于某事的失望、疲惫,以及些许的怨恨。对于这一点,福尔默可能是对的。我自己也从播音员的语气里、从科罗拉多控制中心的呼叫声中听出了这一点,尽管我们接收到的新闻都已经被审查过,我觉得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知道的消息,鉴于我们的特殊情况,所处的位置暴露而敏感。年轻的福尔默用他那直接、听起来有些愚蠢却敏锐得不可思议的方式,说人们并不像以往那样享受这场战争了。过去,他们将战争视为一种升华,一种周期性的激情,他们享受其中,并获取力量。我之所以反对福尔默的观点,是因为他通常跟我有一样的信念,而这些正是我隐藏在内心深处且最不愿承认的。这些想法从他那温和的脸上,从他那真诚而洪亮的嗓音中传出,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紧张和不安。而当它们没被说出来时,我从未如此。我希望这些话能够保密,永远埋藏在内心最深的黑暗之处。福尔默的坦率暴露了一种痛苦。 很快就能察觉出一场战争与先前战争的那些令人怀念的联系。所有的战争都能回溯至过去。战船、飞机、整个军事行动都以古代的战役、更简单的武器命名,我们认为它们是因更为高贵的意图而起的冲突。例如,这艘侦查截击舰名叫战斧II。我坐在发射台,看着一张福尔默的祖父的照片,照片上的他还是个小伙子,穿着松垮的咔叽军装,戴着薄薄的钢盔,站在光秃秃的地上,肩膀上挎着一支来复枪。这就是一个人性时刻,它让我想起战争除了别的之外,也是一种形式的渴望。 我们的飞船与指挥站对接,补给食品,更换录音带。他们告诉我们,战争进行得还不错,虽然他们似乎并不比我们知道得多。 然后,我们就分离了。 这次操作堪称完美,我感到高兴而满意,恢复了与最接近于外部世界的人性接触,交换了俏皮话和男人间的粗话,交换了声音,交换了新闻和谣言—流言、抱怨、小道消息。我们装载了西兰花、苹果汁、水果鸡尾酒、奶油糖果布丁。此时我感到有种回家的情感,收好各种颜色的罐装食物,一种富足安宁的感觉、一种消费者实在的舒适感油然而生。 福尔默的T恤衫上印有“题字”这个词。 “人们希望卷入比自己更宏大的事件当中,”他说,“他们以为那会是一种共有的危机。他们能感受到一种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命运。就像一场袭击了整座城市的暴风雪—只不过持续数月、数年,把每个人都卷了进去,产生一种仅是怀疑和恐惧的同感。陌生人相互交谈,停电后只能在烛光下吃饭。战争会使我们所说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变得高尚起来。曾经事不关己的事会变得与己相关。曾经孤立的也会变为共有的。然而,当共同的危机感结束得比所有人预料的都要早时,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开始意识到这种同感在暴风雪中会持续得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