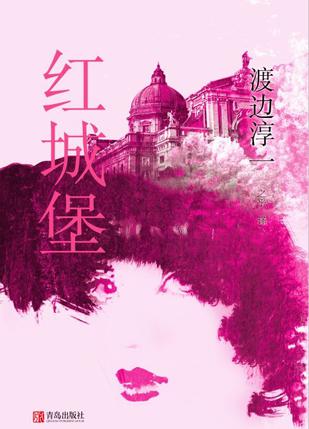石屋子里剩下了我一个人,我突然感到口干舌燥,渴得要命。这无疑是第一次进城堡,心情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的缘故。于是我端起桌上那个老鹰形状的水壶,往杯子里倒了些水,端起来喝了一口。
刚才还透着些夕阳亮光的窗口,现在已显得漆黑一片了,屋里的四角,各有一盏灯将那石墙照得比刚才那夕阳光下还要亮堂。不过,比起平常的房间,这灯还是不太亮,四盏从天花板上吊下的灯,除了灯下一圈,别的地方就不能看清书本上的铅字了。为什么不装上一盏稍微漂亮些的水晶吊灯呢?我自己问着这么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一声钝浊的声音响起,将我的思路打断,面前墙上随即豁开一扇窗,屋里一下子显得非常明亮了。
由于正面的墙上突然开出一扇窗来,那亮光使我有些按捺不住地从贵妃榻上探起了身子朝那窗中看去。
瞬间,我的目光凝住了似的不能活动了。
展现在我眼前的是现实?还是梦幻?是电影?还是幻灯?或是一张绘画?我真的有些无法区别了。
这石头墙壁隔开的窗子的那边,刺眼的光芒中能看到下面是一间房子,这房间的中央,站着一位全身裸体的女人。她此时手脚张开,整个人形成一个“大”字,腹部下面的部分也暴露无遗。
说老实话,我迄今为止还没有看见过一个女人如此地张手开脚的样子。再仔细看,那女人的两手是分别被左右两边天花板上垂下的两根绳索缚住的,她的双脚也是被地板上的两个铁圈锁住的。
猛一看去,我不由赶紧将目光转向了别处,这实在是我不忍心看那女人的样子,更是不能相信这竟是现实中存在的事实,就像偷看到了不能看的东西那样感到惊恐不安。
“啊”女人发出了叹声,我猛地扑向了石墙上的窗户,死死地盯着那屋里的女人看去。
确确实实,我现在看到的不是什么电影或绘画,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那女人双手被吊在空中,垂下的头和腰部分明还在微微地晃动着。
奇怪的是,我盯着那女人看了许久,却还没能看出她就是月子。月子浑身真正地一丝不挂,只有眼睛被一条白布蒙住了。我之所以一下子认不出她来,实在只能说我的眼睛和头脑,受这突然的刺激还没有清醒过来。
终于,我头脑有些清醒时,是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音乐以后,同时那女人嘴里发出了一声“啊”的呻吟。
音乐传了过来,这一瞬间,我的眼睛、耳朵以及五官的感觉才恢复了正常。再紧凑着窗户看去,发现那女人身材瘦瘦的,并不太高,与欧洲女人相比显得相当的娇小,头发是黑色的,被绳子吊起了双手,两腋形成深深的窝窝,胸前的乳房很是丰满而富有弹性,腰际线条清晰,平滑的小腹下方那一丛油亮的青丝惹人心跳。整个身子虽已不是少女了,可还是隐藏着某种未成熟的稚气,而且富有某种高贵的气质。
我终于察觉到了,但由于我所处的屋子光线太暗,窗那边的强烈光线一下子照得我眼花缭乱,所以我眼里最初的月子全身只感到一种超乎寻常的苍白,看到的并不是什么裸体的女人,而是月光下一尊玉立的宝石……
我这样形容着那房里的女人,嘴里禁不住喃喃地叫了起来:“月子。”
那真的是月子,那细腻的肌肤,那白得显得青苍的肌肤,只有月子才具有。想起刚认识月子时,她曾经不无自豪地说她由于生下来时肌肤白得似透明的月光似的,所以才取名为月子。我是从来没有看到过月子的这种形象,迄今为止曾无数次地请求她让自己看看她的裸体,可不管是在洗澡时或者还是睡觉时,她都不允许我看她的身体。只是在新婚那天,与月子洞房之夜,初次看到她那晶莹透白的胸脯,一下子有些发怔,惹得她赶紧用衣被将自己捂住,以后就再也不让我看到了。
而且最近一年来,她又变本加厉地拒绝与我同床共枕,我实在忍耐不住央求她,哪怕只让我看看,她也只是一个劲地叫着“讨厌”,十分冷酷地置我的满腔热忱于不顾。
然而,此时此刻,就是这位月子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全身一丝不挂地站在房子的中央,而且她那显得十分傲气的尖鼻子,她那薄薄的可爱的小嘴巴,她那垂头丧气、白如凝脂的颈脖子,一切的一切都无法再隐藏,全部彻彻底底地暴露得无遮无掩。还有她那身子,丰满的乳房,细细的腰,圆滑似少年的屁股,平滑的小腹,再下面那绒绒的毛,甚至于她那微微颤抖着的胯下,都无法逃过我的眼睛。
这样的时刻,我是乞求了多少时候了呀!这样的情憬,我是憧憬了多少次数了呀!我曾无数次地臆想着,为了发泄,只能依靠自慰。然而现在我终于如愿以偿了,由于家庭条件的悬殊差别,月子从一开始就瞧不起我,我总有一天要将她剥得精光,任我观赏,这愿望我现在终于实现了。
我又一次为这城堡的坚固与巨大而感动。不愧为中世纪建造的城堡,有厚厚高高的围墙,还有深深宽宽的濠沟阻隔,才能使我这祈盼已久的宿愿得以实现。

红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