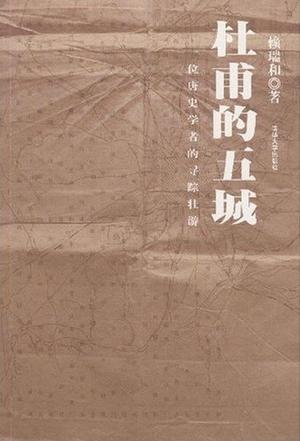第二年五月底,夏天还没来,我又迫不及待地开始我第三次的中国大陆行了。为了这次旅程,我甚至还提前请了假。暑假还没到,一改完期末的学生考卷,第二天就从香港直飞到了昆明。这一行,准备在中国的大地,走上几乎两个月,也是我所有旅程中时间最长的一次。 到了昆明,不免随俗到西山龙门、滇池、石林去玩了几天,也到市郊的云南师范大学去,寻访了当年西南联大的旧址。那一排低矮简陋的小教室,默默立在校园内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真难想象,当年那么多知名的学者、诗人、小说家和物理学家,曾经在那里待过长长的八年抗战。闻一多的一座雕像,也竖立在校园内。 前往石林途中,经过蒙自,小说家沈从文当年住过的地方。又经过宜良,那里的烤鸭据说以松木熏烤,很有点名气的。可惜不知怎的,我下车去观赏了一会烤鸭的烧烤过程,见到一只只肥肥油油的鸭子,竟嫌它油腻,而且想到一个人若买下一整只,恐怕也吃不了。结果,我居然不想买,没有买。如今回想起来,我和宜良烤鸭就只有看的缘分,没有吃的福分了,空留下无限的遗憾。对于这道没有尝过的宜良烤鸭,也无从多说了。说到昆明的吃,唯一可以告慰的是,我去吃了过桥米线和田七炖鸡,都很美味。 然而,我来云南,到底不是为了吃。我是为了寻访一通南诏的石碑而来的。 云南大理市最吸引我的,不是甚么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也不是崇圣三塔,而是鲜少人知道的《南诏德化碑》。出发前,读过一些资料,知道这通唐碑,如今依然竖立在大理市的太和村内,但却没有更多的详情了。毕竟,太和村太小了,地图上也没有标出。我不知道它位于何处,该怎么去。心想,到了大理再想办法吧。 到了大理的第二天早上,随着当地的一个旅游团,先去苍山和洱海玩了几乎一整天。下午四点多返回市区时,和驾驶那辆小面包车的司机谈起,想不到竟问对了人。他知道太和村在哪里。 "就在进城的大路边。待会回市区的时候,我把车停在路边,让你下车。你一个人再往上走一小段路,就到了。" 就这样,我在一个阳光十分明丽的下午,来到了太和村口。司机放我下车后,我沿着一条小路,走进村里。村内尽是稻田和农舍,默默浴在下午的阳光中。走了约十分钟,来到一个高坡上。苍山就矗立在这个高坡后面,形成一道天险。我站在高地上,回过头来,洱海便在我前面不远。一山一湖,保护着这个太和村。难怪一千多年前,唐代南诏国的太和城,就建筑在这个坚固可守的好地方。 南诏是唐朝后期的主要外敌。我在普林斯顿念研究所时,正巧我的一位美国"师兄",是专门研究南诏史的,而我自己研究唐代的军事与边防制度,不免也得留意这个西南边界上的南诏国。而今站在这个太和城遗址上一看,感觉到苍山和洱海是如此的贴近,真可以体会到唐代在这儿用兵之艰苦了。怪不得唐室对南诏,总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在这块高坡上,有一个小小的园子,园里有一座碑亭,亭里头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南诏德化碑》了。碑亭旁边,有一个小小的长方形池塘,不知是甚么用途。五六个顽皮的小孩,正在嬉水,扑通扑通地跳进池中游泳。碑亭附近有青青的绿草,修剪得还很整齐。下午温馨的太阳,照在这一块古老的土地上,照在这一群年轻顽皮的小孩半赤裸的身上,照在池塘的水上,形成一种动人的光影。有一种很抒情的,田园的韵味。 孩子们见到我背着相机到来,玩得更起劲、更疯癫了。拿起相机,想给他们拍照,他们却又害羞起来了,互相推让,有的还跑开去。我走到碑亭处,隔着窗往里望,《德化碑》高高的竖立在里头。这儿见不到售票处,也见不到有甚么人在看守,仿佛很荒凉的样子。但小孩说,有管理员,他在园里的后头宿舍睡觉。有一名小孩还自告奋勇地说:"我去替你叫,我去替你叫。"说完就真的立刻跑开去叫了。 不一会,管理员来了。他衣着破旧,又瘦又黑,抽着烟,不像是看守一通历史名碑的人,倒更像是一所破和尚庙的庙祝。然而,和他一谈之下,他却友善极了,热情得很,话很多,似乎这里很少访客,连这位守碑人都感到寂寞无比,一有访客便兴奋不已。 他打开碑亭的门。《德化碑》黑压压的一大块巨石,发出一种无比威严的光彩。它默默地立在这个太和城遗址上,已经超过一千二百多年了。碑身严重风化,凹凸不平,原本刻着的三千八百多字,现在只剩下几百字了。而即使是这些残余的几百字,也字迹模糊,难以阅读了。我绕着石碑走了一圈,再用手轻轻触摸它的碑身,觉得自己仿佛就像在触摸一块南诏和唐代的历史,那么具体而真实。 这通《德化碑》,可说大有来头,因为它是一通建国纪念碑,在公元七六六年,由当时的南诏国王阁逻凤竖立的,记录了南诏国建国初期的一系列重大史事。它在唐代南诏关系史的意义,自然非常深重。而且,由于泰国人的祖先,据说就来自南诏,所以连泰国学者,或研究泰国古代史的人,都对这通唐碑深感兴趣。守碑人告诉我: "几个月前,就有一位泰国女教授来参观。当她知道碑还存在,没有在文革中被毁,感动得很,几乎快哭了。" 此碑如今只剩下寥寥几百字,但幸好在清代,王昶等金石学家,早在他们所编的碑文集,如《金石粹编》中,记录了大部分的碑文。一般人作研究,其实也不必实地访碑,只要查阅那些碑文集就可以了。我是因为对石碑有一种莫名的"激情",所以才专程来的,也因此才有眼福,亲眼见到这通中国最高最大的石碑之一。 大理师专的周佑先生,曾经注释过《德化碑》的碑文,并把它译成白话文,出了本小册子。访碑过后,守碑人问我知不知道这小册子,他说他正好在代售。我说不知道,便跟他买了几本,准备送给我那些研究唐史的同行好友,也算是此行一个难得的纪念品。这个译注本,由大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出版,但似乎全由自己负责发行,外头书店是买不到的。最后,守碑人还陪我走了一小段路下山,到大路边去等车,等路过的车子回返大理城。不一会,车子来了,我上了车,看着这位守碑人转过身,低着头,在夕阳下慢慢走回太和故城去。 我和南诏史迹,除了这通《德化碑》外,竟还有另一段意料之外的因缘。 从大理到丽江,途中得经过一个小县,叫剑川。它原本不在我的行程上,然而我却意外的,有缘在这个小镇停留了一天,还见到了中国一个极罕见的石窟:石钟山石窟。它根本就位于偏荒的深山丛林之中,但它也是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游完大理后,第二天一早,我乘了一辆长途汽车,原想前往丽江。车上无事,随手翻看一张在大理时买的云南省地图,竟见到一段介绍石钟山石窟的文字。这才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石窟,也是第一次见到旅游资料的介绍。看来,这石窟不怎样为世人所知,可能是因为交通不便吧。 最吸引我的是,这一段介绍短文,无意中提到石窟的第二窟为《阁逻凤出行图》。这位阁逻凤,当然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南诏国王。我昨天刚在大理见到的那通《南诏德化碑》,便是他竖立的。没想到,他的雕像竟还遗留在人间。 在普林斯顿,我那位专门研究南诏史的"师兄",还曾经用英文出版过一本专书,叫《南诏国和唐代的西南边疆》(此书有林超民的中译本,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我对南诏史发生兴趣,一方面固然因为那是唐史和唐代边疆史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也可说是因为和这位师兄有这点因缘。可是当年在研究所读他写的那本书,却好像从来没有见他提过甚么石钟山石窟,或这幅《阁逻凤出行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不禁十分好奇起来了。 再细读那段文字。原来,那石窟就在大理自治州剑川县城西南约二十五公里的地方。我赶紧查看地图,发现剑川位于大理西北约七十五公里,就在通往丽江的路上,待会车子应当会经过那里的。我不禁心动起来,心想不如干脆就半路在剑川下车,先去寻访这个石窟,再去丽江吧。反正,我一个人旅行,有的是时间。 我问了问车上邻座的一位大理老农夫。他说,确有这么一个石窟。他们乡下人在初一十五或甚么大节日,有时还会集体包车去那里拜神。然而,他说:"你一个人恐怕不好去,没车去。" "那该怎么去呢?" "你先在剑川县城下车,再看看城里有没有拖拉机肯载你去吧。" 拖拉机?这倒是个全新的经验。当时,我还没有乘坐过拖拉机,但是拖拉机的功用,我已经在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中见识过了。那位带点"野性"的马缨花,不就经常乘坐拖拉机,去私会她的情人吗?那仿佛是很浪漫的一种交通工具。我不禁也跃跃欲试了。 于是车子一开到剑川县城,我就跳下车去。剑川汽车站后面,正好有一家小旅社,好像是个体户经营的,连名字也没有。这名个体户,也负责经营车站的小餐厅,样子看来还很老实。旅社的房间很小,很简陋,像临时搭建的工地宿舍,全用木板盖成,每个床位每晚只要人民币三元。我心想,剑川是个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的小县城。这家旅社不知是否可以招待我?看来还是尽量不暴露我的"外宾"身份为妙。所以,正要办理住宿登记时,我对那名年轻的男子说,"登记免了吧。"没想到,他居然答应了:"好吧,免了,没关系。"就把房门的钥匙交给我,让我自行保管了。可见剑川县和外界之隔绝,连住宿登记都可免了。这也是我几年来,跑遍整个中国大地,唯一没有办理住宿登记的一晚。 午饭后,走到菜市场去,寻找拖拉机上石钟山石窟。正巧,有一辆手扶拖拉机,就停在马路上等生意上门。 "去不去石钟山石窟?"我问司机。 "去,去。你多少个人?" "就我一人,请问多少钱?" "一个人,来回一趟,收四十块吧。" 我心想,二十五公里的路,来回一趟,不算贵,于是说好。 这名年约二十岁的司机,把车上放着的一些蔬菜、谷物,运到不远的一个摊位后,就载着我上路了。起先,车子还在县城唯一的柏油马路大街上行驶时,平稳极了,但一到了城郊的黄泥路上,我才知道不妙。这种拖拉机颠得很,避震能力很差。我甚至怀疑,它可能根本就连避震系统都没有。人坐在上头,骨骼真的会被震痛。我在车斗左边的架上坐了一会,终于受不了摇晃和震动,干脆站了起来,才发现站的姿势最理想,最不怕颠。于是,我就站在车斗上,双手紧紧握着车斗前头的一根横铁条,仿佛站在开篷的吉普车上,像国庆日大人物经过阅兵台那样地站着,上石钟山去了。 上石钟山的路很简陋,似乎才刚开辟不久,还是石子黄泥路,不过已可容许小轿车通行了。走在这样的路上,拖拉机每碰到一块石头,便要大颠一次。结果二十五公里的路程,我们走了足足三个多小时,越过一个又一个的山头才到,中途还得停下来休息了好几次。没想到,这石窟建在如此荒凉的山上。要不是它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想恐怕连那条简陋的小路,也根本不会有的。 石钟山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它静悄悄的,藏在深山中,没有甚么游客,幽静极了。比起敦煌和云冈石窟那种人头涌涌的盛况,石钟山真是冷清得很。那天下午,就只有我一个访客。负责售票开门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在悠闲地阅读一本《法学概论》。"我准备考大学。"他说。能够在这么安静的环境中读书,我还真有点羡慕他的福气。不过,他说,山区交通不便,他每个月只能下山一次。山里的伙食也不好。"菜得自己种,肉每星期才能吃一次。" 石钟山石窟是唐代南诏时期到宋代大理国时期开凿的。当年,徐宏祖霞客先生曾经到过这附近,可惜据他的《徐霞客游记》所说,他走错了路,竟没有见到这些石窟。其实,山上的石窟也并不多,比起敦煌和云冈少得多了。目前只发现十六个,八个在石钟寺,余下的在附近狮子关和沙登村,但精华全在石钟寺的那八窟。其中,最吸引我的是第一、第二和第八窟。 第一窟的南诏王异牟寻朝议图,和第二窟的阁逻凤出行造像,都是很罕见的,雕刻得极为华美精致,而且更难得的是,居然保存得那么完美。这些石窟连照片也不多见。太珍贵了,管理员也不容许我拍照。难怪外界几乎不知道云南有这么一个精彩的石窟。据管理员说:"来参观的,绝大部分是研究中国艺术史和南诏史的专家。" 第八窟更特殊,刻的是一个巨型的女性生殖器,白族人称之为"阿央白"。据说,这种雕刻是一种母系社会的遗迹,在中国难得一见。然而,我回到香港后,见到一位文物专家宋伯胤写的一篇文章《记剑川石窟》(《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七年第四期),他却对这雕刻有些生疑。他说,"这个雕品,传是'女生殖器'。据我观察,虽不敢肯定不是,但有两点怀疑:第一,它不是原来就雕成的,很可能是莲座上的雕物被人打凿掉以后的结果;第二,若果它是原来雕成的一个极有意义的崇拜物,那末为甚么要把崇拜物雕得这样粗糙,把崇拜物的座子,石窟两壁以及窟外的装饰又雕得那样细致,这是不可理解的。"说得也是。 参观过石窟后,又乘坐手扶拖拉机下山去了。下山的路固然比较好走,但也一样的颠晃。这一天,总共坐了六个多小时的拖拉机,双手紧抓着车斗上的那条横铁,虎口都被震得酸痛了,连双臂也被太阳晒黑了。然而,这真是一段难忘的旅程,也让我多结了一段南诏缘。而且,可以更深刻地体念到了,张贤亮笔下的马缨花,当年乘坐这种拖拉机去私会情人,行程该是多么的艰苦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