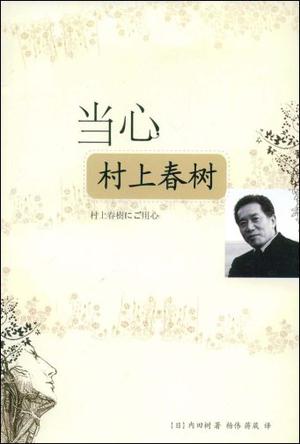杨伟(四川外语学院日语系教授,四川外语学院日本学研究所所长) 1949年出生的村上春树绝对称得上日本文学史上的奇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挪威的森林》一举成名以后,不到二十年即成为被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阅读得最多的日本现代作家。 如果说村上是日本文坛上的创作怪才,那么,本书《当心村上春树》的作者内田树则是百分之百的评论怪才。毋庸置疑,当“四月一个晴朗的早晨”,百分之百的评论怪才与百分之百的创作怪才碰撞在一起,想必迸出的火花一定会光芒四射,甚至四处飞溅,弄不好还会“灼伤”路人的眼睛。所以,怪不得要“当心村上春树”,就如同得当心内田树一样。 内田树比村上春树小一岁(注意一个也许很无聊的细节,村上春树与内田树都有一个“树”字),1950年出生于东京,中学时曾参加 SF迷俱乐部,还曾是披头士音乐的迷恋者。高二时的学习成绩处于全年级最末位,并因所谓品行不良受到退学处分,从而进入爵士乐茶店打工。(哇,SF的幻想世界、披头士音乐、爵士乐茶店——莫非是另一个村上?)1969年报考京都大学法学部惨败,当了一年“浪人”,于1970年考入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文科,于 1975年毕业于法文专业(奇怪,日本学法文出身的人就是牛,不只有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太宰治、野间宏等人,在评论界也大有一领风骚之势),其指导教官是日本赫赫有名的文学评论家菅野昭正。大学时代因受畏友竹信悦夫的影响而立志研究列维纳斯,后进入东京都立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同时与朋友一起创办翻译公司,取得巨大成功,以至于即便在他撰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可以优哉游哉地坐享这家上市公司的大笔利润分成。(细心的读者,不,即使不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上述经历都断片性地出现在本书的描述里。) 现在他既是神户女子学院大学文学部的教授,也是合气道六段、居合道三段、杖道三段的武道家,成为大学合气道部当之无愧的顾问。其专业方向是法国文学、法国现代思想、犹太教思想,还有电影符号学和身体技法论(武道论),让人惊异于他是如何把风马牛不相及(至少在我们这些庸人看来是如此)的诸多研究荟萃于一身的。 作为犹太思想研究者,他2006年出版的《私家版•犹太文化论》因受到评审委员养老孟司的激赏获得第六届小林秀雄奖。(似乎也是他迄今为止获得的唯一奖项,不过,单凭这点,也比在国际上名声大噪,但在日本国内却与重要文学奖无缘的村上要幸运几分。)作为关注“格差社会”的思想家,他2007年出版的《下流志向》成为轰动日本的畅销书。他还曾出版过《街头的中国论》(2007年)和《街头的美国论》(2005年)。作为结构主义和电影符号学研究者,他出版过《电影的结构分析——从好莱坞电影中学到的现代思想》(2003年)、《可以躺着学习的结构主义》(2002年)。作为关注身体的武道家,他出版了《通过身体来阅读时代——武术的立场》(2006年)、《身体的主张》(2005年)、《死亡与身体——交流的磁场》(2003年)等等。(哎呀,还有老长一串书名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从上述书名中就不难看出,“私家版”、“街头”、“躺着学习”、“身体”等构成了其关键词语。从这些书名中还可以发现一个最大的特点:其论述的不少话题颇具理论性,甚至是艰深而古板的,而选择的角度却是个体的、重视身体性的、另类的,换言之,是非主流的、脱学院派的。(尽管他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在日本文部省挂了号的、以在校园里教书育人和著书立说为天职的大学教授。)如今他被称为最擅长于将生硬晦涩的思想嚼碎后再传达给读者的“日本大叔”。(这也缘于他写过一本名叫《大叔式的思考》的著作。)他使以往深奥的学术思想迅速下放到图书市场,能够做到通俗易懂而又灵光四射,时而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时而又强调感性捕捉,甚至还带着点无厘头的意味,很有种评论界“潮人”的感觉,特别是其独特性的重复性叙述受到了年轻人的热烈追捧,结果让学界同仁又是不齿,又是嫉妒,颇有点近似于村上春树在日本文坛上遭人厌弃和妒忌的感觉。(怪不得本书的一个重要论题就是:“为什么日本很多主流评论家不喜欢村上春树?”莫非内田如同身受,所以颇有心得,能够得出“私家版”的独到见解?)不过,这并不妨碍内田的著作本本畅销,成为出版界和媒体上的红人。而他在网上开通的博客更是人气爆棚,到2008年6月,其点击率已经超过了一千四百万人次。 就是这样一个怪才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新书《当心村上春树》。而且,他延续其特立独行而又不失搞怪的风格,犹如最珍重的一大劳作一样,把出书的日子跟自己的生日精确地算到了一起。也许是这个算法很奏效吧,这本书出版不久即加印了三次。还好,这次为他“摇旗呐喊”的除了一帮“内田迷”以外,还有部分学者和评论家,尤以少壮派为甚。东京大学副教授河合祥一郎写道:“装饰该书的开卷语乃是假想村上春树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贺词。特别有趣的是其对日本评论家否定村上文学的反驳。因为村上文学发出的是只有那些被挑选出来的人才能听到的泛音,所以评论家越是说什么也听不见,就越是强化了村上文学读者那种‘被选中的收信人’的感觉。其中充满了令人扑哧发笑或是不胜感佩的洞察,让人觉得终于找到了村上文学的解读方法。” 此外,几乎所有的读者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该书的魅力就在于充满了与过往的村上春树论截然不同的新鲜阐释。换言之,是在众多所谓正规的学院派评论或是“公家版”评论中难得一见的崭新的村上春树论。就在各种故作正经的村上春树论层出不穷,并有可能成为评论家们各自意识形态的临时容器时,内田版村上春树论的价值或许就在于他的脱意识形态性,换句话说,就在于其一贯强调的“身体性”,从而成为了“划时期的文学论”。为纪念该书出版而举行的内田树与柴田元幸的谈话就取名为“用身体来阅读村上春树”。而在本书中也有两篇分别题为《美妙的故事会直接作用于身体》和《用身体来阅读》的文章,且分别引用了村上春树一段意思相近的话语:“说得极端点,对于小说而言,所谓的意义……并非那么重要吧。或者说,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意义与意义如何有机地相互呼应。如果用音乐来打个比方,那就像是‘泛音’一样的东西……作为一种物理现象,包含着泛音的声音会长久而深远地残留在身体里。”换言之,我们应该不是用“大脑”,而是用“身体”来阅读村上春树。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回到文学的原点去感受故事本身,感受共鸣,清楚地听到村上文学所发出的“泛音”,而不是噪音。 内田借助“泛音”这一音乐术语,来阐释村上文学在读者中拥有大批铁杆拥趸的原因,那就是因为村上春树是个深谙制造泛音技巧的作家,让忠实的读者们萌生一种“被选中的收信人”的感觉。而村上“完全不受评论家们的好评”这一文坛事实愈发强化了读者们的信心:“那么,我现在聆听着的这个泛音,是唯有我才能听到的。”于是,内田树就以这样一种方式独辟蹊径地来解读着村上文学俘获读者的秘密。 此外,该书还以“‘父亲’的缺位”、“扫雪工”等为关键词来引领我们走进村上文学的迷宫。 内田树注意到村上文学有着一个重要的格局,那就是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没有“父亲”。而在内田看来,作为韩流先锋的电视剧《冬季恋歌》也是一个“父亲缺位”的爱情故事。而不管是韩剧,还是村上文学,之所以赢得一种普遍性、大众性抑或世界性,就是因为故事中父亲的缺位。内田写道,“父亲” 存在于世界各地,无论在何处都发挥着同样的机能。不过,在每个地方都以“不同的形态”显现,并散发出“不同的气味”。可一般的作家都误以为与自己争执不休的那个“父亲”,也就是众人的“父亲”,可遗憾的是,于他而言的“父亲”,仅仅是他个体世界中的“父亲”,因此,即使凝聚了全部技巧去描述自己与“个体父亲”之间的纠葛,亦无法赢得文学的世界性。而村上文学却以父亲的缺位克服了这种局限性,穿越了国境,并悄然设问道:“在‘父亲’缺位的世界里,被放逐到没有地图、没有指针、没有革命纲领、没有‘政治性的正确行为规范’手册等这样一种一无所有的状态中,尽管如此,我们能否在这样的状态下成就‘某种善的事物 ’?”(见本书《“父亲”的缺位》一文) 在内田看来,村上春树是给出了肯定答案的。那就是做一个“扫雪人”。“一旦下雪,人们就会明白,尽管‘扫雪’并不是谁的义务,然而,这工作若是没有人干,最终大家都会非常为难。说来,这工作几乎没机会得到好处。可恰恰是多亏了这些不为人知的‘扫雪’人,世间不利的胚芽(比如,脚下一滑,摔坏了头盖骨之类的厄运)才得以被摘除少许。我想,这就属于那种‘一点点积累世间善行’的工作吧。”(见本书《村上春树与冷酷魔境》一文)为了保护所爱之人免受“用老虎钳糟蹋猫爪的邪恶力量”(见村上春树《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扫雪人默默地接受了这项工作,也并不奢望什么特别的报酬和褒奖。也正因为有人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清扫积雪”这一日常性的努力,才总算在一个没有“父亲”的世界上阻止了“超越常规的邪恶力量”的渗透。在内田看来,这就是村上文学反复讲述的、能够触动所有人心弦的“根源性的故事”。 人们总是把小说分为“富于现实性的小说”和“充满幻想色彩的小说”这两个大类,而村上的小说却冷不防把这两者捏合在了一起,在日常性与非日常性之间不知不觉地架起了桥梁。内田认为,将宇宙规模的神话与日常生活的细节融合得天衣无缝,这便是村上文学最大的魅力所在。人们之所以阅读村上文学,是“正因为他让我们感受到,平凡的日常工作本身就是宇宙论戏剧的演绎‘现场’,所以,人们阅读村上春树之后,方能打起精神,去做大扫除,去熨衣服,或是去给朋友打电话。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见本书《After dark till dawn》一文) 村上文学的热潮与消费社会的关联性常常成为评论家所探讨的对象。显然,消费社会的急速发展给大都市罩上了空虚和倦怠的空气,以至于人们在当今这个“父亲”缺位的社会里备感不安,催生了迷惘的年轻一代。村上文学中弥漫的失落感恰好代言了找不到生活目标和航海图的人们的迷惘。但正如村上文学反复讲述的那样,世间充满了邪恶的力量。面对随时可能入侵的邪恶力量,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扫雪,做没有回报的工作,或是当在麦田里玩耍的孩子们遭遇危险时悄悄出手相救。而村上文学的孩子们(不管是什么国籍)就是从这里找到了克服失落感的妙方,发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虽然确实平淡无奇,但却在某个地方与灵魂的配电盘连在了一起。 内田就是这样来感受并言说着村上文学的魅力和世界性。他毫不含糊地坦陈自己对村上文学的喜爱,以至于本书被不少人称之为“写给村上文学的公开情书”。正是这种坦白让他摒弃了评论家惯常保持的自矜和冷静,而以一个村上读者的鲜活身份诉说着从中听到的泛音,以及那些美妙故事作用于他的身体所产生的生理反应。不过,如果以为这就是内田的全部,那无疑是被内田“骗婚”了。正如他的一本书名《我的身体有一个好用的脑袋》(2003年)所表达的那样,他以身体为前提,也运用着聪慧的大脑。他在冷静的评论家和疯狂的村上文学迷这双种身份之间走着钢丝,在感性和知性之间来回游弋,并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否则,他就不可能向我们发出村上式的泛音,而只能传送出质朴但是单调的基音了。正如村上春树是依靠将日常性与非日常性这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赢得读者一样,内田树是依靠将身体与脑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成为评论怪杰的。 显然,内田树的村上文学论提供了一种接近村上文学本质的解读方法。不过,即便它非常有效,甚至可能是村上迷最容易共鸣的解读方式,却也只能是无数方法中的一种。而且这种方法是以其他方法的复数存在为背景,才彰显其独特价值的。不注意到这一点,也许就有可能陷入另一种偏激或迷失。所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要当心内田树,就像得“当心村上春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