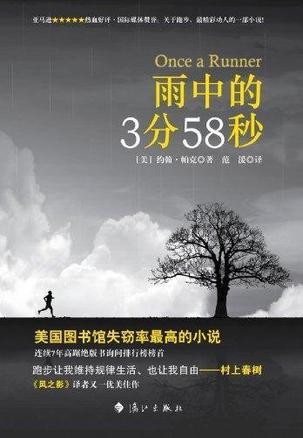黑夜能让跑者的感受更敏锐,也更能深刻体会孤独,还有一种在单独行动时产生的低调兴奋。 卡西迪随着黑夜的节奏奔跑着,啪哒、啪哒,在街灯凝视之下,那是他愉快而孤独的奔跑节奏。在这漆黑的地方,他成了无名氏,在肯斯维尔高低起伏的丘壑之间或上或下,偶尔穿插着狗群的吠叫,以及爸妈们要求把薯泥传给餐桌上其他人的咆哮…… 路人大概以为他神志恍惚,然而,他对周遭的幽暗背景却一清二楚:冬季花卉的清香,栎木的洁净清爽,铁兰潮湿且刺鼻的味道。还有各种声响,比如傍晚的低俗电视节目及孩子们的争吵。他是一颗探索宇宙的黯淡流星。黑夜能让跑者的感受更敏锐,也更能深刻体会孤独,前进的步履似乎更快捷,迫切感油然而生,还有一种在单独行动时产生的低调兴奋。 只是,他那无限绵延的空想,偶尔会被某个从雪佛兰里探出头来大喊的笨蛋打断:“嘿!跑步的!”卡西迪通常会立刻甩手示意别招惹他,对方若不理会,表达不悦情绪的脏话就出口了。多年来,他一直努力让自己对这些人无动于衷。如今,他的做法改成了反击。那些路人非常惊讶,没想到一个跑者(通常是个性温和的人,不是吗?)竟会如此凶悍。他不能够理解,何以故意招惹跑者乃人之天性。不过,他现在明白,这样的人性根深蒂固、难以应付,而且举世皆然。曾经有个英国作家描述自己遭受街头顽童奚落的经验:“嘿!你们快看看那个跑步的人,他没穿衣服哩!”有些小鬼还朝他身上扔东西。在卡西迪的路跑经验当中,有人喜欢朝着他大喊:“一、二、三、四……”,然后极尽讪笑之能事,非要把跑步和当兵的经验联想在一起不可。 有一次,当他正在进行两百米的加速冲刺时,偏偏就碰上一群讨厌至极的无赖,居然毫无预警地把车停在故障的红绿灯前,硬是挡住了路口。他们自以为安全无虞,只要把车窗摇上,车门关紧就行了,没想到,一脸惊慌失措的他们眼睁睁看着卡西迪爬上车子,攀越车顶,跑步并未因此而中断。 练跑时,他一向无畏无惧,总觉得自己轻易就陷入激动的情绪。他经常思忖,如果有人拦下他并向他挑衅,他该怎么应付。他猜想自己一定会先稍微激怒他们,故意激他们反击。他会先静观其变,稍微保持一段距离,然后逐步向他们挑衅。他们或许会跟上大约八百米,如果他诱引他们的本事很好。或许他们的自尊心会起作用,因为误判情势而产生的傲慢,往往带来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肖特曾经靠着一双飞腿在新墨西哥州的山丘上击退一群恶少,虽然刚跑完二十五公里的他当时早已筋疲力尽。你得密切注意那些征兆,卡西迪心想,那些你再熟悉不过的征兆:疼痛、迷惑和空白,最后濒临绝望。他会营造成一个挑战,让这群人忘了当初的目的为何,一股傻劲儿地追上来,就为了让这个小子,让这个……这个……(接着,他们会恍然大悟)让这个跑者好看。 接着,他会转身去面对他们。就算是天皇老子也一样,他这样暗想着。就算对方是拳王阿里,也不例外,只要可以主导这场竞赛…… 卡西迪非常清楚,他可以带领这些强壮、勇敢的人进入从未有过的境界。在那个境界里,生与死在肌肉萎缩和心灵绝望的超现实幽谷里部分交叠。到了那里,一个人才开始明白,世间没什么好在乎的,只要能停下来(甚至死亡)就行了。在那里,所有的人终究要脱去光鲜亮丽的文明外皮,而皮下鲜红的血肉会让你知道——在欢乐与痛苦交集下根本没有秘诀存在。 简而言之,那都是长跑选手生命里的过客。在了解一切情况之后,如果他们执意坚持,他非常乐意奉陪。只是,他很确定,他们不会想这么做的。他们会带着辛苦得来的教训仓皇离去。 这天晚上,没有人拦下他。没有人语出威胁。没有人惊扰一个跑者在漆黑夜晚练跑的纯净时光。 卡西迪就这样飞越了暗夜。 “丹顿……”他对着话筒说道,“我有话跟你说。我现在人在宿舍,事情在电话里讲不清楚。你能不能到‘九○年代’跟我碰面?” “当然可以。你跑到哪里去了?我还以为你今天下午会跟我一起练跑。你今天练跑了吗?” “当然。我扎扎实实地跑了十五公里!喂,我今天下午必须去杜比的办公室一趟。出了点事情。你可以在十五分钟后跟我会合吗?” “可以啊!不过,我可不打算跟你们这些家伙一样,一整晚都坐在那里灌啤酒。我是有家室的人,而且……” “可以,可以,没问题。我得去冲个澡,才刚跑完回来,待会儿见了。” 平日的“九○年代”客人并不是那么多。老板弗里德看见丹顿进门,顿时欣喜若狂,立刻送上一大壶啤酒。那是他表达热情的方式,毕竟肯斯维尔并不常见奥运金牌选手。两位跑者挑了个在角落的雅座。 “你碰到什么麻烦?”丹顿开门见山,点唱机依旧幽幽轻唱着:“……岁月啊……洗涤了……看不见的伤口……” “你看过今天早上的报纸了吗?” “谁没看过啊?” “嗯……他们已经决定了,因为请愿书是我打字的,而且把签名寄出去的也是我,所以这整件事的构想,以及……呃……他们所谓的‘犯罪事实’,都是由我和另外一两个未被指名的共犯操纵的。” “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学校里的每个选手都快气疯了——” “我确信,他们真的就像外表看起来那样,笨得要死!自己在外头没本事……” “拜托,我觉得这整件事根本就没什么!” “没错!不过,杜比正经八百地跟我说,他不会怪我这样小题大作。他认为,要怪就要怪激进党,还有校园那些满脑子左派思想的教授,都怪他们把我的小脑袋变成这样。” “你觉得他是真的这么想吗?” “噢,他确实是这么想的。他一向就不是个随便说笑的人。而且,他还把事情跟军队联想在一起!‘在军队里,上级什么口令,你就做什么动作,否则你就吃不了兜着走。’诸如此类的事情。接着,他把事情扯到我的教授们头上去了。拜托!我在这里三年来碰到的都是十足的右派疯子和纳粹分子,而那个笨蛋居然认为我被一群思想左派的知识分子洗脑了。我那个讨厌的经济学教授居然说弗里德曼是个搞不清楚情况的煽动者!他妈的,如果哪天这个学校出现了一位真正优秀的好老师,他们大概会私下逼迫这个可怜的家伙把教材全换掉……” “好啦,你冷静一点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卡西迪揪着一张脸,大口喝完第二杯啤酒。他依然处在练跑后的口渴状态。 “他们打算从严处理。真正引起众人注目的部分,显然是一群足球队员在那份该死的请愿书上签了名。杜比显然也因为这件事被普利曼找去训了一顿。我想,这件事如果没有牵扯到足球队员的话,他们顶多会说我们这些田径队员满脑子激进思想罢了。反正我们绝大部分是个人项目,没有什么团队的……” “照你这么说,倒是很有道理的。” “而且,我已经开始感受到有人正在暗地里蠢蠢欲动了。” “你想太多了。”自动点唱机唱着:“……这里有人见过美好事物吗?……” “老杜提到,他认为类似这种事情在足球赛季一开始就在球员之间流传,否则,依他们球队过人的资质,他们怎么可能会交出四胜六负的成绩呢?你懂我的意思吧?” “什么话!”丹顿无法置信。“他们想把一蹋糊涂的成绩归罪于……” 卡西迪用力吐了一大口气。就外在而言,他身手敏捷,体魄强健,可以轻松跑上一百五十公里。然而,他却开始感受到有股令人窒息的重量正从他头上压下来。 我觉得自己好老,他这样暗想着。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想你不会比那次更苍老了。不过,那是好遥远的事了,在那片咸海里…… 丹顿坐在那儿,依旧不可置信地望着天花板。卡西迪告诉他:“丹顿,我觉得很闷。碰到这种蠢事真的很倒霉……” “嗯!我知道,但是你要坚强,千万不要因此乱了方寸……” 三天之后,一脸困惑的康瓦教练把卡西迪叫进了办公室,然后告诉他,他从此不得参加大学院校杯的田径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