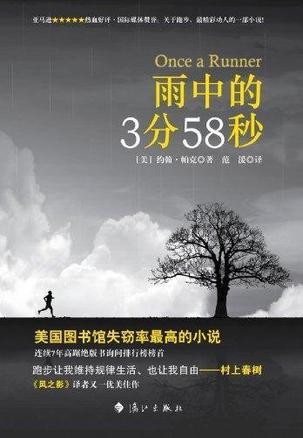那些能将标枪掷出二十米外,或者一跃就是两米高的过人精力,有时候也不是木板和泥浆能抵挡得住的。 杜比会馆是那种年代古老宽敞的木造建筑,似乎仍保存着原居住者多年前的油烟味。就像铺了老旧布料的安乐椅,有股霉味,但很舒适。 就像其他曾是私人住宅的建筑物,充斥着学子喧嚣的杜比会馆仍保有家庭般的温馨。屋内虽轰隆嘈杂,却远比现代住所传出的冷清的声音更让人愉悦。 此处曾是肯斯维尔市长海勒姆·杜比一家人的住处,近年来,这幢宽敞舒适的大房子已成为东南大学田径校队三十多位队员的住所。会馆所在地和校园只相隔两条街,屋内从早到晚不断传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噪音,有诡异的吶喊、刺耳的尖叫,偶尔也会播放着走调的流行歌曲,这些声响全都来自于那群生活以田径为中心的年轻人。毕竟大叫发泄总比真的出人命好多了。那些能将标枪掷出二十米外,或者一跃就是两米高的过人精力,有时候也不是木板和泥浆抵挡得住的。 屋墙颤动,接着就是一连串怪异的举动。 已经辞世多年的老杜比若见到这番情景,一定会乐得很。每逢周六晚上,老杜比总会狂饮一番,然后一把抱起他那花容失色的娇小妻子——一个大眼睛的美人胚子,芳名爱玛莉——骑着哈雷摩托车,来一趟足以吓跑放牧牛群的飚车之旅。 “小姑娘!”他会这样叫她。“咱们要去夜游啦!”他那双狂野的绿色眼眸仿佛一团火焰似的紧盯着她。 “啊……啊!”她发出惊呼。 这并不意味着老杜比会因此犯法,因为镇上大部分牛都是他的(外加一大片土地和好几笔敏感的抵押产权)。他就是一些老乡口中所谓“生命力旺盛的家伙”。老杜比是个粗犷直爽、精力充沛的人,很早就明白人生要把握当下、及时享受。他很明了一切事物总有灰飞湮灭的一天,而且一去不回。 他这辈子唯一惹的称得上的麻烦是有天晚上,他特别粗暴,砸毁了一些围栏,而且还一路狂吼到市中心,扬言要找“他妈的笨蛋算账”,后来,这个眼神哀伤的老家伙坐在警局问讯室里,满脸惊愕地四处张望着。 “警长,我发‘素’……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时候会做出这样的蠢事……”这是他被当场逮捕隔天清晨的真心忏悔。他双手捧着头,发丝蓬乱,头隐隐作痛。 “唉,老爸!”警长说道。“大家已经在闲言闲语了,而且是骂声连连。”警长“靴子”正是老杜比的长子。 “我一直搞不懂,”警长继续说道,“你为什么老是要拖着妈妈去做那些事?” 霎时,老杜比变得兴致勃勃。“为什么?”他大咧咧地喀喀笑个不停。“因为她就喜欢出去狂欢啊!” 老杜比来年当选市长,这个选举结果大概也反映了这座大学城的幽默感。他的选举政见是把坏蛋撵出这座城市,有意思的是,他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他落实政见,真的把坏蛋都撵走了。 老杜比的当选就像他生命中许多经历一样,根本就是上天硬塞给他的奖品。不过,老家伙心中有个深沉的伤痛,事关他的小儿子,这个在老杜比五十二岁、爱玛莉年近四十时才生的儿子,居然是个脑袋不太灵光的笨蛋。“靴子”曾经获得西点军校入学许可,谢里尔·安曾是乔治亚理工大学的校花(只是后来休学嫁给了一个足球球员)。这个就像孙子一样的小儿子努力想学会操作割草车的基本换档动作,老杜比焦急地看着,这样的情景让他心痛不已。当这个孩子和小他一半的表弟玩简单桥牌都招架不住时,老杜比只能跑到牧场上放声痛哭。 老杜比打定了主意。这个很有主张又很懂得反其道而行的人,决定帮助轻微智障的儿子得到其他孩子没有的东西:大学文凭。多年之后,因为如此不寻常的做法,老杜比被认为是很狡诈的人,为了达成不可能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对手中的强大权力用起来没什么良心顾虑。老杜比捐赠大笔财产给东南大学(当时新成立的昆虫学系正苦于没有基础设施),大方出让了担任市长七年期间居住的房子。这项捐赠包含了一般规范:“以此交换十美元和其他利益以及法律报酬……”但所谓的其他利益和法律报酬是什么,知道的人只有老杜比自己、他的律师以及当时被指派为校长的普利曼先生,也就是德高望重的佛罗里达高等法院现任大法官。当时,爱玛莉已经去世五年,而老杜比也希望离开繁杂的市中心返回农场,在那里他可以好好闻着粪肥和干草的味道,然后这样死去。他并没有提起一直在脑子里打转的想法——整修那辆心爱的老哈雷,当时那车就放在谷仓里,上头盖着防水帆布。 毫无意外,老杜比把农场搞得一团糟,甚至把工头也惹火了,他还买了五十五亩胡桃林。最后,他终于接受劝告,参加了旅行团的观光行程,玩遍墨西哥好几个城市。旅游归来后,他扯着大嗓门,聊着仙人掌的改造土地计划,还有意无意地提出了“进出口生意”的想法。 由于儿子学校课业顺利,老家伙总算能活着见到自己的儿子毕业了。儿子一脸茫然,头戴方帽,身穿学士服,笨手笨脚地跟着参加了“隆重的仪式”。昆虫学系几年后迁离杜比会馆,田径校队跟着搬进来。老杜比没多久就去世了,不过,据说这老家伙在通往上帝的路上还试图想爬出棺材哩! 老杜比,这个精力充沛的无赖,笨拙的恐怖分子,也是个技术高超的王牌大骗子,最后却成了蛮荒乡野的英雄。 而他生的最后一个男孩,那个脑筋迟钝的儿子迪克·杜比,靠着一张假文凭,在荼毒了无数可怜的昆虫之后,成了东南大学的美式足球总教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