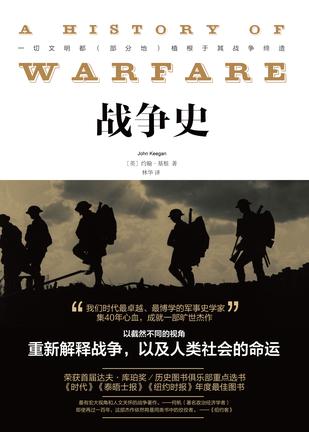我在本书的开头曾发问:“何谓战争?”现在书写完了,我希望能使读者认识到,对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战争也并非都属同样的性质。我还希望读者会对人注定要打仗,世界事务归根结底只能用暴力解决这样的思想产生怀疑。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因为我们所属的国家大多是经过征服、内战或独立斗争而产生的。而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伟大人物一般都是从事暴力的人,许多本身就是战士;即使没有亲身参加战斗,也明白暴力的用途,并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 20世纪频繁而激烈的战争也造成了普通男女观念的扭曲。在西欧、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战争影响到了大多数家庭的两三代,甚至三四代人。几百万儿子、丈夫、父亲和兄弟应征上战场,却再也没有回来。战争给全体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灵创伤,使他们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不再经历他们遭受过的苦难。然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有暴力发生,甚至残酷或无情的表现也不多见。维持世界运作的是合作的精神,不是对抗。大多数人每天在生活中都力求合群,尽力避免不和,减少分歧。睦邻被视为平民最可贵的美德,善良是最受欢迎的个性。 必须认识到,只有在自我克制的严格限制内,睦邻才能够发扬光大。我们心目中最宜居的文明社会是法治社会,即有警察管控的社会,而警察的工作是一种形式的强迫。我们接受警察,就等于默认人性有黑暗的一面,必须用强力予以遏制。不受遏制的人要受到惩罚,用来施加惩罚的工具就是强力。然而,尽管人有暴力的潜质,他同时也能够限制暴力的影响,哪怕没有强力对暴力的遏制。本书开头时对“原始”战争现象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为20世纪的战争都十分极端、十分残酷,所以现代人很容易认为战争趋向极端是不可避免的。在现代战争中, 温和有度或自我克制的名声不太好;人道主义停战或调解被讥讽地看作对极端痛苦的暂时缓解或掩饰。然而,“原始人”的行为证明,人在作战中有能力限制自己行为的性质及影响。原始人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使他和他的敌人免于战争的最坏结果。一种办法是豁免,即社会中的某些成员——妇孺老病——不参加战斗,也不受战争结果的影响。另一种办法是习俗,特别是有关选择战争的时间、地点、季节和由头的习俗。最重要的办法是仪式性的程序,它确定了战斗本身的性质,并要求在完成了确定的程序后,交战方承认得到了满足,并转而诉诸和解、仲裁和媾和。 前面说过,千万不要把原始战争理想化。它有可能突然变得十分暴烈,把所有的豁免、习俗和程式都抛在一边,使暴力迅速升级。即使交战双方遵守了各种限制,战争给战败方造成的物质影响也是令人伤心的。最重要的影响是逐渐迫使弱小的一方离开他们熟悉的家园,到条件严酷的地方去。这样的迁徙最终有可能破坏,甚至摧毁他们的文化,尽管文化方面对作战的限制通常起到了保护文化的作用。文化不能无限地自我维持,它很容易受到打击,而对文化打击最大的就是战争。 尽管如此,文化又是决定战争性质的首要因素,这方面亚洲的战争史提供了明证。让我们暂且称其为东方战争,以与欧洲战争相区别;它有其自身的特征。最首要的特征是避敌锋锐、拖延等待和迂回战术。考虑到阿提拉、成吉思汗和泰摩兰的军队作战时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凶猛无情,这些特征似乎全不适用。然而,看他们的行动要结合大背景。战马成为主要作战工具的3000年间,那种残酷的战争在欧亚战争史上并非经常性的特点,而是间隔很久才发生的异类情况。当然,在那3000年中,马背上的武士一直是一个威胁,但这个威胁一般是可以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通常采用的作战方法。他的作战方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避敌锋锐、拖延等待和迂回战术。马背上的武士从来都是远距离作战,使用投射性武器,而不是锋利的刀剑,遇到顽强抵抗时即撤军后退,靠消耗敌人的力气制胜,而不是硬碰硬地通过直接的较量打败敌人。 正因如此,防守方一般可以在和马背上武士居住的地区接壤的地方修建固定的防御工事,以此阻止他们的来犯。他们一旦离开居住的草原,首先就难以维持大群的马匹;如果再遇到像中国的长城和俄国的碉堡线这类拦路的障碍,他们就可能会完全丧失战斗力。尽管如此,一些马背上的武士最终还是成功地深入农耕地区,成为长期的统治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莫卧儿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还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在阿拉伯土地上大权在握的马穆鲁克。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成功的征服者也未能发展出创新性的治理艺术。他们仍然紧守着营帐、战马和弓箭的文化,即使住进了被他们打败的帝国首都的豪华宫殿,还保留了游牧民族酋长的生活方式。在遇到采用了新作战技术的力量的挑战时,他们文化上的僵化使他们无法有效地应付,最终只有被淘汰一途。 但具有矛盾意味的是,东方战争的一个因素赋予了它强大的目的感,同时又对战争的行为进行了自我设限,这个因素后来才传到西方。这就是意识形态和思想的因素。远在任何西方社会之前,中国人就已提出了战争的理论。儒家崇尚理性,他们的理想是社稷长存,江山永固,这促使他们寻求用法律和习俗来控制动武的冲动。但这个理想无法长期维持。内乱外患时时造成政权更迭,来自大草原的侵略经常是引起内乱的原因。尽管如此,中国人战争最持久的特点仍然是适度,目的是维护文化,不随外来征服者或内部革命一时的需要而改变。中国人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使来自大草原的侵略者实现了汉化,用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控制他们本性中的破坏倾向。 亚洲的另一个主要文明,伊斯兰文明,在战争中也表现出了克制。不过人们的印象却恰好相反。伊斯兰教被广泛视为号召征服的宗教,它最广为人知的一条教义就是穆斯林有义务对异教徒发动圣战。其实,穆斯林社会以外的人对伊斯兰征战的历史和圣战教义的确切性质都有所误解。伊斯兰国家对异族发动征服战的时代相对短暂,那个时代的结束不单单是因为伊斯兰国家的敌人学会了如何反抗,也因为伊斯兰国家内部就打仗是否合乎道德发生了分歧。这样的内部分歧造成穆斯林反对穆斯林,违背了穆斯林不得彼此作战的教义。面对这种情况,伊斯兰国家的最高权威采取的办法是把作战的职能交给专门为打仗的目的招募而来的武士,把他们变为附属的专业阶级;这样就解脱了大多数人的作战义务,使虔诚的穆斯林得以专注于关于圣战的训谕的“大”的方面而不是“小”的方面,这个“大”的方面是“对自己心魔的战争”。伊斯兰国家主要是从大草原的骑马民族中招募为自己打仗的战士,那些人因垄断了武器而夺取了权力,但他们拒绝调整自己的军事文化去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结果伊斯兰国家的战争最终变得几乎和中华文明内部的战争一样限制重重。在一个文化内部,作战行为受到限制只有好处。但一旦这个文化和另一个对东方传统所规定的行为限制完全不予承认的文化发生碰撞的时候,它面对敌人残酷无情的战术就丝毫没有准备,亦毫无招架自保之力。 伊斯兰国家遇到的那个文化正是西方文化。它由3个要素组成,一个是自身固有的,一个是从东方学来的,还有一个是它通过适应和试验获得的。这3个要素是道德、思想和技术。道德要素来自古希腊人。是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摆脱了原始作战方式的束缚,尤其是作战中对程式的尊重,采用了面对面你死我活的战法。这种对传统方法的背离始于希腊人彼此之间的战争,外部世界初次接触到这种战法时深为震惊。关于亚历山大大帝和仍保留着原始作战程式和马背上武士的躲避战法的波斯帝国的战争,阿里安做出了详尽的叙述;它既是真正的历史,也是文化差异的一个范例。大流士皇帝是真正的悲剧性人物,他所代表的文明面对亚历山大这样的敌人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占了上风后不肯罢手,用钱贿赂,派人说项都不管用;他们什么事都要放到战场上去解决;他们打起仗来似乎胜负比什么都重要,连个人安危都抛在脑后。大流士是被他的随从杀死的,他们希望把大流士的尸体留在那里让亚历山大看到,自己就可以逃过一劫。这极好地说明了权宜和荣誉这两种不同的战争道德之间的文化冲突。 徒步作战至你死我活的道德守则——这里必须说明是徒步作战,因为这一道德守则属于步兵,与骑兵作战无关——后来通过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传到了罗马。它一定也传给了条顿民族,罗马与条顿民族进行了一系列殊死决战,最后以失败告终;至于是如何传到条顿民族那里的,到现在仍然没弄清楚,也许会成为一个永远的悬念。然而,入侵罗马的条顿民族毫无疑问是采用面对面战法的。若非如此,他们肯定不可能打败罗马军队,尽管在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世纪,罗马的军队已经凋敝不堪。后来建立的各条顿王国取得的一个特殊成就是把面对面的步兵战法吸收入了马背上的作战。因此,西方的骑士和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同,作战时直冲敌人的大军所在,而不是远远地趁机突袭。他们在夺取圣地的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遭遇了阿拉伯人和马穆鲁克的军队,其间发现自己原来面对面的战法经常不能奏效;在和不把避免直接交锋视为耻辱的敌人作战时,冲锋不起作用。然而,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在中东的冲突导致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其意义非同小可。它解决了基督教徒一直以来关于战争是否合乎道德的困惑,因为它把圣战的道德观念传到了西方,给西方的军事文化注入了此前没有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的要素。 蕴含着个人荣誉概念的面对面的作战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要素就这样结合在了一起,剩下的只等加上技术要素就构成了完整的西方作战方式。到18世纪,火药革命已经被广为接受,火药武器也得到了完善,这个要素终于到来了。为什么西方文化对技术带来的变化热情接受,而亚洲文化却没有(而它的性质完全不是泥古不化的),这个问题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畴;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亚洲文化之所以没有适应技术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仍然遵守着一种军事克制的概念。军事精英坚持唯有他们才有权使用传统武器,无论他们的武器与其他地方新出现的武器相比是多么落伍。其实,这种坚持是一种非常合理的军备控制方法。西方世界抛弃了军备控制,走上了另一条路,结果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谓的真正的战争:它是政治的继续——克劳塞维茨视之为战争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内涵;它以作战为手段——克劳塞维茨所理解的作战就是面对面的战斗;它使用西方技术革命发明的武器——克劳塞维茨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 克劳塞维茨去世后的年代里,西方到处攻城略地。19世纪期间,亚洲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被西方置于统治之下,只除了中国人、日本人、泰国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属民;美洲、非洲和太平洋的原始部落面对西方的军队更是毫无胜算。只有尼泊尔和埃塞俄比亚这些偏僻难至的地方没有落入西方帝国的手中,因为太难攻克,不过它们也都遭受过西方的侵略。20世纪上半叶,就连中国也难逃魔掌,遭到西化的日本人的占领,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领土也任由西方军队长驱直入。只有土耳其人这个勇敢坚毅、足智多谋的民族,这个即使使用弓箭这种效力有限的武器也多次打得敌人落花流水的民族一直没有屈服,直到在20世纪中期成为独立的国家。 然而,西方战争方式的胜利其实是假象。在用来对付其他军事文化的时候,它的确战无不胜。但用在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它带来的只有灾难,甚至可能造成浩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几乎全是欧洲国家,它结束了欧洲对世界的统治,通过给交战国人民带来的苦难,腐蚀了欧洲文明中最美好的内容——自由主义和对未来的希望,它还给军国主义者和极权主义者提供了掌握未来的机会。那些人争取他们想要的未来,结果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未竟的破坏。它还促成了原子弹的发明,这是西方战争方式逻辑发展的顶点,也是对宣称“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种论点的终极否定。 政治必须继续,战争却不能继续。这并非说战士的作用已经终了。世界比过去更加需要随时准备为国家服役的技术娴熟、纪律严明的战士。这样的战士必须是文明的保卫者,而不是文明的敌人。他们是为文明而战,他们的敌人是种族主义者、割据一方的军阀、意识形态上的顽固分子、普通劫匪和国际有组织犯罪分子,他们的作战方法不能只采用西方的模式。未来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的人从其他的军事文化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不仅是东方的军事文化,而且也包括原始的军事文化。战争中的自我克制原则,甚至象征性的仪式程序,都是需要不断温习的智慧。把政治和战争区分开来是更大的智慧。除非我们坚持这一区分,否则我们就像复活节岛上最后的居民一样,未来可能被“手上染血的人”所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