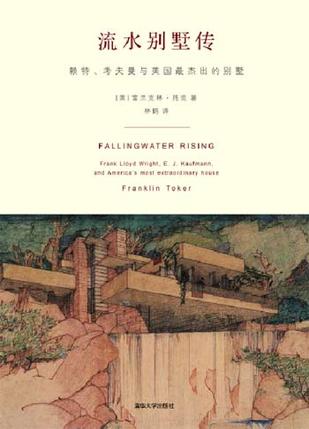这座建筑好好地立着。你的家。由于你为它付出的代价它才属于你。由于我为它付出的代价它才属于我。由于各方面为它的付出它又属于全人类。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致艾琳·巴恩斯达尔信 既然赖特和考夫曼一家全都去世了,流水别墅就留给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有责任去思考流水别墅在历史上的意义,更有责任去思考它在今天的意义。像万事万物一样,流水别墅每一年都会有崭新的意义。1938年布置就绪的那场大肆宣扬是如此夺人耳目,以至于直到如今都还没有完全磨灭。那场大肆宣扬的主要操控手,特别是亨利·卢斯和老考夫曼,他们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顶多充个历史性脚注而已(虽然赖特和艾恩·兰德并不是这种情况),可这座别墅每一年都会更有名气。作为它的新主人,我们需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 就现代建筑而言,事实证明,奥斯卡·王尔德说的那句警句“变得太摩登是最危险的”是对错参半的。在经年累月之后,1932年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博得无限阿谀的现代建筑三位一体奇迹般地保持完好:格罗皮乌斯的包豪斯校舍和勒·柯布西耶的萨伏伊别墅在战争时期遭到损害和废弃之后得到了修复,而密斯在巴塞罗那博览会上设计的临时展馆在老照片上显得极端迷人,于是该市就在它被拆除五十年后重新建起了它。年久有些受损的倒是1932年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成了明星的三位建筑师的声望。格罗皮乌斯的声望遭到的损失是最大的。作为一名严肃的建筑师,他竟然允许自己的名字与纽约中央车站背后的泛美大厦那个笑话联在一起,这相当于是在切腹自杀。勒·柯布西耶终生都保持了他的早期作品中那种纯净和抒情的气质,但是他的建筑沦落成了被人轻率模仿的牺牲品。等你见过从波士顿市政厅到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总部这一连串的模仿之作以后,就很难在他的拉图雷特修道院面前感动得发抖了。有些年里密斯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他设计的西格拉姆大厦的光芒在1958年照耀着整条公园大道,因为它在纽约市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今天,公园大道上盖出了这么多座像雪茄烟盒般的摩天大楼,只有渊博的游客才能从中把西格拉姆大厦认出来。不过,即使是在1958年也应该能预料到这一局面。密斯的荣耀就在于你可以(从表面上)复制他;赖特的荣耀则在于你无法复制他。 这种情况并没有自动宣告赖特在他与格罗皮乌斯、勒·柯布西耶和密斯的痛苦竞争中赢得了胜利。从规模方面来看是欧洲人——首先是密斯——赢了:我们家门外的整个世界看着更像西格拉姆大厦而不是流水别墅。不过从思想方面讲,欧洲人的地位就不太有利了。他们一直在推进着一种与历史决裂的运动:可现在连他们自己也成了历史。 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之后,赖特的声望大体上还是很好,而流水别墅的大受欢迎当然也是与日俱增。这种声望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说它超越时间是因为,与其他的早期著名现代建筑不同,流水别墅这件作品不受时期年代的限制。特别是如果我们看到由格罗皮乌斯和勒·柯布西耶设计的那些住宅,就会愉快地感到自己重回了30年代,可流水别墅就没这种效果。我们热爱流水别墅并不因为它是1930年代的文物,我们为的是它今天对我们造成的刺激。从地理方面看,流水别墅的热门总是全球性的,而且一贯如此。有时候它在国外显得比在本国还更热门:比如在日本,给予流水别墅的尊崇通常只会留给本国的国宝。 从1938年至今曾盖成过上千座杰出的建筑,在这当中比起来,流水别墅也算是维持得很好的。我们在庆祝第三个千年来临的宏大庆典中感受到许多快乐,其中一点就是发现了20世纪是个伟大的建筑时代。其间的优秀建筑不断涌现,首开先河的是赖特以及与他同时代的欧洲人;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重新起步时出现的大师有康、沙里宁、巴拉干(Barrag噉)和丹下健三;最近则是我们的城市点缀着“奇观”(spectacle)式或曰“首席女星”(diva)式的建筑,他们的风格倾向各自不同,被人称为后现代或者第二拨现代派。流水别墅几乎不必担心这些竞争者。毕尔巴鄂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一度赢得了大众的敬意,不过也走起了下坡路。它的大肆宣扬是20世纪的一次巨大成功,与流水别墅的宣传运动不相上下,但是游客们很少有人会说参观这座建筑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而人们至今还在这样说着流水别墅。 近年来牵涉到流水别墅的一个新话题是需要拯救它。这座建筑曾在1990年代岌岌可危地近乎坍塌,此刻它提醒了新一代的人,当年它降生的时候是多么胆大包天。有人说它是“美国的比萨斜塔”,贴切地形容出了流水别墅遭到了何等困顿,为预防它轰然倒塌,所采取的措施正好有个惊人相似的类比,也就是意、英两国工程师的伟大成就,他们挽救了在这个千年的另一端建成的伟大工程文物,让它免于自我毁灭。看到了人们得以利用现代手段解决原始技术遗留的问题,举世皆惊,我们在此过程中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热爱这两座(相对)古旧的建筑。 西宾州环境资源保护部在熊奔溪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挑战,其中,终止悬挑部分的变形是最为紧迫的一项任务。流水别墅里固定住几百扇窗户的窗框也朽坏到了必须重装的程度。熊奔溪的水质遭到了污染,这就要求花费巨资,整修这片领地上纵横交错的下水道系统。(同时借着这批新装在整片地界里的管道,在里面铺设了光纤电缆。)西宾州环境资源保护部的管理者们努力解决着这些高技术问题,同时他们还得为熊奔溪丰富的自然资源制订出一套保护策略来,游客的大量涌入已经造成了威胁。有一项研究结果这么说:“流水别墅由于太受人爱戴而遭了罪。” 由于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不断变化,历史也在不断变化着,因此,当我们穿透从那以后建成的所有建筑组成的滤镜看过去的时候,流水别墅一定也有所变化。不过,赖特的设计有一个决定性的优点,胜过了其他的建筑杰作:举世还没有另外哪座建筑与它相像。如果把后来建成的建筑放在流水别墅的旁边,无论是当真放过去还是只做个比方,就会像是把毕加索的作品放进了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放进了委拉斯凯兹展室。结果,委拉斯凯兹的画《宫女》会显得更加出色,不是因为毕加索的画很差劲,而是因为它们会衬托出那位更早的大师所具备的内在的力量。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美国建筑界一直尊流水别墅为整个美国历史上的最佳建筑,也是全世界近百年来的最佳建筑——但是普通大众又怎么说呢?既然从来没人为热门程度进行过票选,我们可以先来数数是哪座建筑吸引到的游客最多,尽管这样的计数如果不看前因后果的话就几乎没什么意义。在美国境内,美国国会大厦、自由女神像、联合国大厦和白宫每年都会各自吸引到200万名参观者,可人们主要是因为这些地点的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才受到了吸引,目的并不是要看它们的建筑。从全世界来看,地球上最显赫的建筑应该是北京的毛泽东纪念堂,但是它每年的800万名参观者上那儿去也不是为了研究它的建筑。麦加的克尔白天房、金字塔、列宁墓和白金汉宫也属于类似的情况。每年在白金汉宫里打哈欠的游客有上百万,其中有多少人能根据记忆画出一幅粗略的速写呢? 只看参观人数的粗略统计数字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有些地方容易去,有些地方难以到达。参观过西斯廷教堂、爬上过埃菲尔铁塔的人数与参观过流水别墅的人数相比多出好几千人,因为那些文物建筑总在大众的视野里,而且很容易到达。流水别墅一定是世界上最少被人看到的艺术杰作之一。游览过这里的350万人在美国现存人口中占到了大约0.5%。哪怕只不过是坐在第五大街的一辆公共汽车上对着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匆匆一瞥也罢,一天之内如此举动的人数也超过了一年之内参观流水别墅的人数。 由于流水别墅是一座家庭博物馆,我们拿它与其他数千座类似的对手做个比较,或可从中得出一些结论。它每年的参观流量有14万人,所以在此类博物馆里前25位最有吸引力的名单上排到了第20位——这个成绩很出色,因为这一行最大的诱惑之处不是建筑,而是富有和名望的幽灵。乔治·华盛顿的维农山庄在这个名单上拔了头筹,每年参观者超过了100万人(白宫是一座公共建筑,因此被排除在外了)。范德比尔特家在北卡罗莱纳州艾什维尔的比尔特摩排名第二,参观者略少于100万人;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圣西米恩排名第三;排名第四的是猫王在田纳西州孟菲斯的故居“优雅园”,每年能吸引到60万名中年参观者(年轻人就不太感兴趣);再来是托马斯·杰弗逊的蒙蒂切洛排名第五,每年有50万名参观者。家庭博物馆中排名靠前的其他项目主要都是总统的宅邸(安德鲁·杰克逊、林肯,还有弗兰克林·罗斯福的两座宅邸);托马斯·爱迪生、亨利·福特以及其他6名实业家的庄园;然后是各式各样的名人住宅,比如保罗·里维尔(PaulRevere)、贝齐·罗斯(BetsyRoss)、罗伯特·李(RobertE.Lee)的住宅,还有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西塔里埃森,位于亚历桑那州的斯考茨戴尔(在名单上排名第24位)。 在这25座住宅里只有4座——蒙蒂切洛、维农山庄、西塔里埃森和流水别墅——在建筑意义上很重要,然而,这4座建筑中的前3座之所以有人前来参观,主要原因也在于它们是伟人故居,因而产生了神秘感,就连赖特的住宅也是这样。排在前25位的这些住宅中,大多数都确实具有历史意义,然而,熊奔溪却没经历过任何一桩重要事件:那儿既没签署过什么条约也没签署过什么降表,既没遭受过大屠杀也没进行过审判,那儿也没激发过什么发明或是伟大的音乐、文学作品。除了赖特和爱因斯坦以外,也没有哪位世界级的名人曾经到访过流水别墅。在这个名单上的前25位里,考夫曼别墅是唯一一座只因为其建筑的精妙绝伦才有人前往参观的。 “流水别墅今天有什么意义?”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先界定“对谁而言?”因为对匹兹堡、对宾州西南部地区、对美国、对全世界而言,这座别墅的意义既多重,又不太一样。对匹兹堡而言,流水别墅最基本的意义应该是与之南辕北辙的形象。匹兹堡出产了世界上最好的钢材和玻璃,赖特把这些材料安放在一个水润的山坡上,映射出了匹兹堡本身。在理想状态下,流水别墅应该像对母亲一样依偎着匹兹堡,匹兹堡应该像对儿子一样宠爱着流水别墅,可是流水别墅如今却希望和它的母亲一刀两断,尽管它已经打理得极其干净了。不过匹兹堡理当冲着全世界大吼,讲讲它曾如何孕育了流水别墅——但那可不是它的风格。 宾州西南部地区在利用流水别墅的问题上更机变一点儿。在两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这个地区抓紧一切时机征讨自然,而今它却用这座别墅来主导着旅游经济,进而又靠旅游经济推动着本地区新的经济发展,这种局面真是相当讽刺。在经历过半个世纪的衰退以后,俄亥俄派尔重新吸引来的参观者甚至超过了它在20世纪初期的盛况。这要归功于E.J.考夫曼,还有他在半个世纪之前拯救了芬克利夫半岛的那份馈赠。夏日里,住在俄亥俄派尔的人数大增,因为有数以千计的人前来健行、露营、骑自行车、垂钓、玩皮划艇、漂流。每年来自美国各地的大约200万名游客多方利用着这个国家保护区,尽管只有一小部分人走得更远,住进了公路上方5分钟路程处的“漂流”屋。 俄亥俄派尔如今有种微风习习的美好感受。你照样可以走进早在威尔逊总统任期内由考夫曼家出资创办的百货店里,稍做停留,俄亥俄派尔的其他商人们则是生意兴隆,忙着向约克加尼河上玩皮筏的人们推销户外用品。在老考夫曼位于康奈斯维尔的老零售店那儿,商人们给健行、骑车穿越大阿勒格尼通道的人们提供装备,这段健行骑车的路线很快就会不加间断地从匹兹堡一直延伸到华盛顿特区。每年有50万名游客被吸引到大阿勒格尼通道上的不同节段,其中有部分路程属于旧铁道线,就在约克加尼河对着流水别墅的另一侧岸上。西宾州把铁道改成旅行线路的风气在全美国是最盛的,从俄亥俄派尔到匹兹堡之间的70英里路程又是使用者最云集的一段。最终,旅游经济可能会在月桂高地和俄亥俄河口之间铸就新的地势联结和文化联结,不亚于乔治·华盛顿在250年前途经此地时曾造成的联结。 对于整个美国而言,流水别墅的根本意义似乎正像沃尔特·惠特曼在《(费城)博览会之歌》(Songofthe[Philadelphia]Exposition)里勾勒出来的那种意义一样,惠特曼写作此诗的那年,赖特只有9岁。惠特曼说,只要我们愿意这样想,我们大胆创新的新建筑将对美国具备的意义也就相当于金字塔对于埃及的意义: 比埃及的古墓更雄伟, 比希腊罗马的神庙更壮丽, 比米兰雕像遍布、塔尖林立的教堂更壮观, 比莱茵河上的古堡更神奇, 而今我们甚至打算超越所有这些,盖起 伟大的教堂,永远缅怀实用发明 供奉工业而非墓地…… (美国啊,诸如此类,就该是你的金字塔和方尖碑, 你的亚历山大港灯塔,巴比伦花园, 你的奥林匹亚神殿。) 赖特学着他所倾慕的惠特曼,也好像在对着某个特定的美国观众致辞,把流水别墅说成是象征美国民主的建筑。在他看来,它的那些挑台用了水平方向的平板,表现着大地,从而“托举”起这座建筑,让它远离任何伤害。在强调水平动态的时候,赖特也赋予了它一种隐喻的意义。“我认为这类水平伸展的线条是人类生活中真正的大地线条,意味着自由。一贯如此。” 建筑批评家蒙哥马利·斯凯勒(MontgomerySchuyler)提起过出现在赖特年轻时代的另一桩建筑奇迹,也就是布鲁克林大桥,他说那是该时代的建筑中“最伟大、最有特色的作品之一”。伟大的艺术通常都与巨额的财富密不可分,可也并非永远如此。在富裕的1920年代,如果没有西蒙·罗迪亚(SimonRodia)在洛杉矶市亲自动手,美国“最伟大、最有特色的”一座建筑,代表着对立面文化的瓦茨大楼就不会诞生。与此相反,贫困的1930年代让我们拥有了帝国大厦、胡佛大坝、金门大桥,还有流水别墅。我此前推测过,考夫曼别墅可能不会出现在富足而放浪的20年代:它需要严峻的30年代来赋予它梦想乃至于悲哀,这些色彩我们从它的身上都能看得出来。 我在上文里主张,大萧条让美国人明确意识到了他们的本土文化遗产,而大量的本土文化遗产都被结合进流水别墅里去了。除了阿尔托以外,欧洲的现代建筑师只在很罕见的情况下才会在自己设计的建筑里引用地方元素:他们的建筑是勒·柯布西耶的萨伏伊别墅或者密斯的巴塞罗那展馆那样的乌托邦梦想世界。赖特却想将美国本土的民间节律编织在流水别墅里的各个角落,就像德沃夏克、艾夫斯(Ives)、格什温和柯普兰在音乐领域的做法一样。但是流水别墅不仅从通俗文化中汲取养分,它也反馈。刚刚撤销了战时限制,牧场式住宅和错层式住宅的浪潮马上就席卷了全美国,而流水别墅就帮助铸造了战后通行的本土风格。 美国人之所以会觉得流水别墅这么贴心,原因之一是,很多美国人自己长大成人时住着的老家就是流水别墅在牧场式和错层式住宅中的复制版本。战后岁月里出现了莱维镇式的各种各样的小城,比赖特本人更好地推销了流水别墅。赖特设计的美国风住宅历来得到的顾客顶多不超过百位,而莱维特公司和其他开发商们却准确地领会到,流水别墅中的若干元素——岩石表面的石材、绵延不断的水平线条、透过玻璃墙面连接到铺石地板的天井——有可能象征着更加富庶的生活,于是就从中选取了一些元素,推向市场。 一方面,对流水别墅的某些解读是美国特有的;另一方面,它的拥趸遍布全球,这种情况也清楚地说明,流水别墅对于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是意味深长。这可能是缘于它的极端现代主义。如今已经没有多少美国人还会认为流水别墅是个“明日之家”,但它在其他许多国家里依然代表着未来。例如,1951年,为伟大的设计师路易斯·巴拉干打工的一名绘图员,或者干脆就是巴拉干本人,曾在某个墨西哥市住宅开发项目中把流水别墅画成了它的诱惑远景,不是因为开发商确实要依样建起流水别墅,而是因为这座别墅如此完美地体现着中产阶级的居住梦想。 然而,流水别墅受到全世界的欢迎还有另一个根本不同的原因,它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这就是人们在这座别墅里直觉地感受到了深刻的灵性。我把这一点归功于流水别墅对历史建筑的无数指涉。这些指涉中确有一些属于特定的文化,不过大多数人无论来自于哪一种文化背景,都能“解码”流水别墅,因为它的关键指涉是指向大自然的。这座建筑像它身前的瀑布、背后的岩架一样叠落,它的墙面好像是由大自然亲自把它们摞起来的。每个人都懂得这些指涉,因为大自然是地球上唯一普遍通用的元素。每名来宾和参观者似乎都能在流水别墅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的某些回音。 建筑师保罗·鲁道夫(PaulRudolph)很聪明地说过,流水别墅是“一个成真的美梦……(它)深深触动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最后,我们对这些东西全都无可名状。”我们永远别想彻底说清它在我们身上施加的魔力。在建筑体验中,很少有哪个实例能和流水别墅带来的体验相提并论,但是在《圣经》里却有一例。古代有一则注解说,上帝在沙漠里年复一年赐给以色列人的食粮“吗哪”(manna)是让人沉醉的,因为它呈现出的味道永远正好符合了接受者心中想要的那种食物。我们可以说,流水别墅就是建筑中的吗哪:我们迫切地回应着它,因为它提醒我们想起了自己最热爱的那些建筑或者风格。根据我们自己的口味,它吸引我们的理由是理性的或者是浪漫的,是抽象的或者是具象的,是老派的或者是高技术的。这就把流水别墅变成了罕有其匹的真正超越流行风尚的建筑。只要我们每个人还会把自己最心爱的形象或是思想投射在它的身上,它就永远不会热门稍减。 在《序曲》一章里,我许愿要讲述流水别墅真实的诞生年谱,替换下它以往的神话和奇迹。希望我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我承认,流水别墅的诞生是由极多的因缘际会巧合而成的,于是有的时候,它的构想似乎依据的是无意结果的法则。如果约瑟夫·厄本没在1933年去世,本诺·詹森没因为替梅隆家工作而发了财,那么,这两位建筑师中就会有随便哪位动手来设计流水别墅,把它建成一座优美然而不会出人意表的乡间别墅。如果老考夫曼没在1933年的《匹兹堡快报导航》上遭到奚落,他就没必要想着给自己盖出一座建筑奇珍来,以此作为对自己的补偿。如果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没在1932年被现代艺术博物馆羞辱过,他可能就缺乏激情去设计这么激进的一座建筑,好夺回自己在现代建筑领域的隆誉。如果希特勒没在1933年执掌德国,小考夫曼就会继续在欧洲闲荡下去,而他的父亲就会在欧洲研习建筑,而不是在洛杉矶。流水别墅的构成中还需要有一片牧歌般的自然地段,靠在工业力量强大的城市边上,而它要想迅速成名,就需要有亨利·卢斯来玩推广的把戏、有一位摄影新手来拍出今生仅此一现的好照片,还要有艾恩·兰德在旁竭力突破她自己的文思阻滞。流水别墅的大受欢迎同样还靠着由大萧条孕育出来的新的社会情绪和新的文化价值观,以及随着美国走向战争而高涨起来的爱国主义。不过,尽管有上述所有这些巧合,这座建筑的名望最终却是全靠它自己。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像流水别墅这样的一座别墅,将来也永远不会再出现像流水别墅这样的一座别墅了。 流水别墅里挤满了游客。这座别墅如E.J.考夫曼所愿,成了美国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