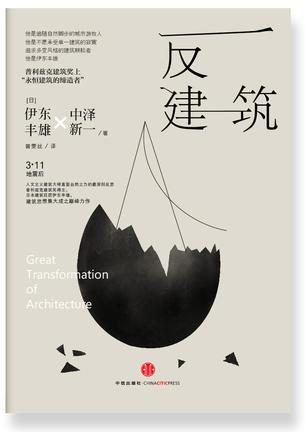就像中泽老师说过的那样,建筑家的工作无非是将客户的想法与现实中可行的实际编织在一起。中泽老师曾经一语道破:“近现代以来,建筑家不知从何时起就带着一种王者的风范,好像建的是自己的王城,或者是在给拥有强大权利的人类或者组织建王城一样,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在工作。于是乎原本应有的作为协调人的作用就被弱化了,这才是现代建筑最大的问题。其实通过3•11一难,海啸灾难也好核泄漏问题也罢,暴露出来的不仅仅是建筑家的问题,而是全体日本人本该具备的作为协调者的机能都弱化了”,我十分赞同中泽老师的观点。建筑家原本应该是建筑中的居民与周围的社会的协调人,同时也还应该是自然与人类所生活的世界的协调者。可以说在当代,建筑家的这一功能被弱化了,而如今在灾区,可以看作我们正在试图找回这一功能。而且对于协调人,也就是与各方交涉的人而言,是不需要有什么王者风范的。 实际上,在我以这种姿态参与重建的过程中,还有人说“伊东老师,盖这么普通的房子不要紧吗?不该展示出更多的伊东式的建筑风格吗”,甚至连事务所的年轻员工也中也有人这么说。然而在3•11过后,如今我确信自己在做的事情就是正确的,并且在带着这种确信开展工作的同时,作为一名建筑家,我感到自己找到了前所未有的真正充满乐趣的工作方法。 作为工作的一环,我将在2012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中担任建筑委员,我准备与三名年轻的建筑家——藤本壮介先生、平田晃久先生和乾久美子小姐一同建造一所群众之家,并且展览结束后我们会将其转移到受灾地。而且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建成后的群众之家,我们还打算将建造的过程本身录制下来一同展示。年轻的建筑家们恐怕又要问“伊东老师,这么普通的东西可以吗?”,或许他们会提出许多意见。我希望通过展示这种争论的过程,来让人们看到我通过地震灾害所感受到的,建筑家能做什么以及建筑家该做什么。或许这也算是让人们看到建筑家作为协调人的工作吧。 文摘 附录:建筑伦理 西藏高原的佛教寺院大多建在背靠荒山的险恶地形上。人们在人迹罕至的荒野上旅行数日,远远地看到寺院的景象,会感到自己终于抵达了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心里不由得松一口气。在这样一片绝无拥抱人类之意,仿佛抽象画一般的风景之中,寺院的确是突兀地割裂了自然,彰显出了人类活动的痕迹。然而在藏族人的建筑思想之中,却并不推崇这种在自然面前表现出自豪的态度。 这其中的理由可以粗略地归结于两点。首先是与“风水思想”(根据地形与方位占卜凶吉的思想)有关。这种自然哲学认为,在建造寺院时,不论是从地理的空间性上,还是从天文学(占星学)的时间性上,必须尽可能地受到自然的祝福,占据天时地利。他们已然了解,将寺院这种建筑作为人造的事物置于自然之中,必然有着无法完全与自然同化的命运,所以不能自认为人类的精神制造出来的事物就比自然进程的创造更为优越,而是要尽可能地去迎合自然,获取自然的祝福。可以说亚洲的“风水思想”已经深深浸透了西藏高原的抽象世界之中。 还有一点理由与佛教思想有关。严格来说,佛教中的密宗始终尤其坚持探索意识的本性,是与这部分的思想有关。不论是怎样的建筑,既然它是由人类的意识活动产生出来的,就具备了无法还原到自然进程中去的特质。然而密宗还认为,仅凭在设计建筑的时候发挥作用的意识,是无法悉数捕捉意识的本性的。如此一来,意识活动的产物不仅带有与风、火、水、土等外部自然相异的部分,与被称为“意识的自然”的状态也是相异的。这么一想,一味地对建筑感到自豪的话,不仅仅是对自然的不礼貌,更会陷入看不清“意识的自然、意识的本性”的陷阱。密宗一直在通过它的建筑思想和实际的画面表现来深化这种思想。 那么,回到具体的话题。关于在建造寺院的时候应该选择怎样的地点,有哪些注意事项,应当遵循什么礼数和规则等等问题,藏族人留下了很多文献记载。宁玛派流传有一本密宗百科全书般的经典全集叫做《大宝伏藏(埋藏经典)》,其中记载道,根据不同地区的传统不同,或者是喇嘛教诲的谱系不同,相应的做法也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其中的一本中是这么记载的: 适于建造寺院(正殿)的土地以具备以下特征为最宜。背靠高山峻岭,前方低丘绵延,左右细流潺潺于前方合流,中部有广阔的岩石与草地可堆放谷物成山,平缓开阔的峡谷地形为最佳。而且最好聚齐被称为“大地的四根支柱”的吉相,即东方为广袤的大地,南部为不高的小山,西方为绵密的圆丘,北部为天幕一样的峻岭。此外还必须要有守护四方的象征。东方要有发白的道路或岩石,象征白虎,且在此方向不得有地形险峻的山谷。南方要有河流和象征青龙的绿地,且若水流有像瀑布般流入洞窟的情况,则最好回避。西方要有象征朱雀的红色土壤或岩石,这个方向上的道路不得有突起的瘤或凹陷的坑。北方则要有嶙峋的岩石,象征龟蛇玄武。这个方向上的水源不应混浊不清澈或咕嘟冒泡。若是一片土地上齐聚了这四方的守护神,便堪称完美了。 (土登嘉措 《打开僧院的大门》 1979年,加德满都) 建造寺院对布施者和生活在当地的人而言都是很重大的时间,所以选地时也需要谨小慎微(毕竟并不是总能找到文献中记载的那么理想的土地,这种时候也需要一些将小丘视为山脉的变通窍门)。在这样选出土地之后,具体将寺院建在哪里,又是由更为自由状态下的必然性也就是“偶然”来决定的。就是说这个场所的决定方式,是让具备神力的喇嘛来摇骰子,以此方式请示吉祥天女的神意来决定的。与此类似地,喇嘛还会通过复杂的占星运算来选出适宜开始动工的日子,然后根据密宗的教诲,举行镇地的仪式。通过以上种种程序,选出大地的形态与磁场、与太阳的位置关系、天体运行的位置等等一切要素都被认定为“适宜”的时间与空间的一点之后,寺院的建造就在自然的祝福之中舒畅地开始了。 不论是怎样的建筑,只要是人为建造出来的,就必然会带有无法完全融入自然的异质属性。然而在贯穿了“风水思想”的亚洲建筑思想中,人们却并不喜欢用建筑物来抑制自然的想法。这种思想认为,在建造建筑时,不应麻木不仁地切分森林和土地,均匀地把地铺平,压抑并压制自然,反而应当借用自然以其精妙的必然性所选择出的天时地利(当然,需要具备特殊能力的人类才能听到自然的声音),集合各种有利的力量与时空的一点,才能建造建筑。这种思想反映出了人类的精神活动也是自然进程的一个部分的观点。建筑是由人类的精神活动而形成的,可是这种精神活动与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繁殖一样,都被囊括在自然的进程之中,是自然进程的一个部分。从这点而言,人类建造的家与鸟兽制作的巢穴没什么分别。所以像建筑这样的行为,人类是不能只凭自己单方面强行推进的。想要完成建筑,必须要在自然的各种力量都对自己有利的状态下进行,必须集齐能够顺利地搭上时空“线路”的种种条件。 然而,也不妨可以这么说,“风水思想”也是人类自身不安的产物。人类虽然赞叹海螺贝壳的美丽、蜜蜂蜂巢的精致,在建造自己的房子、寺院或者教会等建筑的时候,却不会去完全模仿这种“自然的建筑手法”。人类的建筑方式,遵循着与自然进程性质相异的几何学秩序。可以看出,虽然人类的建筑之中反映了欧几里得几何的理想,自然的建筑中的几何学却带有与之不同的感触。也就是说,虽然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也是自然进程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有着无法剔除的不可还原回自然中去的特异属性。所以或许在大地上建造这样的事物,会有损自然的情绪。于是“风水思想”就没能像在小河上建造堤坝的河狸或者将放射状的丝网织成巢的蜘蛛那么大胆,而是神经兮兮地对自然表现出的各种“征兆”加以过分的关注解读。是人类的纤细敏感造就了“风水思想”,这份纤细敏感让安稳的直觉与焦虑的神经在人身上共存。藏族人关于寺院的建筑思想实在是将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之所以这么说,也是因为寺院作为所有建筑的原型,其中浓缩了建筑所包含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