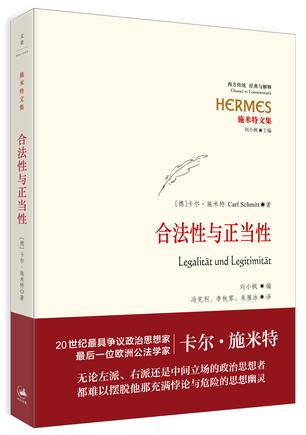《合法性与正当性》一文于 1932 年夏由慕尼黑和莱比锡Duncker & Humblot出版社出版,并且注明,本文于1932年7月10日完稿。 (一)当时的危机已经涉及宪法的概念本身。针对拒绝追问宪法的朋友和敌人的法学,本文是挽救总统制这一魏玛宪法的最后机会的绝望尝试。这使得本文带有其宪法史的强度。本文——尤其是其核心命题——遭遇到顽强抵制:只有在修宪权限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才能够否定一个政党的合法性。正是这个命题,被当时在宪法法上居主导地位的学者们当作非法学的加以拒斥,当作政治上的愿望法一笔勾销。 在本文这里([中译者按]原文第 286 页,参见第一章第 2 节前面部分)已经彻底认识到并牢牢抓住这样一个过程:一个政党进入合法性之门,然后在自己身后将这门关上;这是一场合法革命的典型个案。我从自己 1931 年的著作《宪法的守护者》中摘抄了几乎长达数页的一段,而且涉及与魏玛时代居主导地位的民主派法学学者们(demokratischen Rechtslehrern)的一场争论。通常,无论冗长还是自我抄录,都不是我的风格。但这一次,摘抄是一个抗议、一个咒语。本文的结尾是一声警呼。最后一句“接下来就是真理为自己复仇”,乃真正的呼救。呼救当时无人理睬。但是,撰写魏玛总统制的历史,如果不详细了解本文并评价其命运,是不公正的,也是没有资格的。 为什么呼救毫无结果,无人理睬?“实施修宪的权限,本身并不包含根本上改造宪法结构的权限,这一学说如今在波恩基本法第 79 条和众多州宪法中明确得到了承认。遗憾的是,在魏玛时代,这一在今天对我们来说如此清楚明白的学说却只得到少许赞同。民国宪法的著名诠释者安许茨主张,修宪不可摧毁一部宪法的政治实质,并且断然以如下说明作结:这是一个源于法律的相当重要的政治要求。但是,在魏玛宪法法中,它却得不到任何支持。”其他证明参见前面正文中的第 301—302 页([中译者按]第二章第 1 节中间部分)。 当时流行的法学实定主义基于对立法者的全权的信仰,基于一个有说服力的推论:如果立法者已经是全权的,修宪的立法者的全权必须更为全权。这一非常流行的学说没有再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前提和理论前提。它不知道,合法性原初就是西方理性主义的一个本质性部分,是正当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非其绝对的对立面。普遍的价值中立化属于普遍的功能化,并使民主制成为一种原则上的相对主义世界观。在法哲学上,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颇有影响的《法哲学教程》表述了这一点;该书第 3 版恰恰在 1932 年宣布:“谁有能力实施法,也就由此证明,他有资格创设法……我们蔑视在布道中违背自己的信念的牧师,但我们尊重凭借自己抵制性的法感而在自己对法律的忠诚中不致误入歧途的法官。” (二)在魏玛宪法之下曾任司法部长的拉德布鲁赫这位居主导地位的法学家,就是如此以其全部权威主张如此指导性的法学说。在刊于 1932 年 9 月 11 日《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上的一大篇反对我的作品的评论文章中,一位聪明而又博学的法学家——克瓦博(Georg Quabbe)甚至使用了“捣蛋”这样的字眼。尽管如此,把这种盲目性仅仅理解为一种专业实定主义的偏狭和一种职业性与世隔绝的结果——因为专业实证主义是从一个分工的科学企业的专业化产生出来的,并不公允。毋宁说,不把法律首先看作固定化的手段,而是看作一种和平改革和进步发展的手段和途径,与前一个时代的立法乐观主义若合符节。对于魏玛联盟最强大的伙伴社会民主党来说,还要再加上基尔希海默在其文章“论政治反对派的转变”中称之为“51% 多数的吐火女怪(Chimaere)”的东西:“它在过去时代的社会主义文献中扮演过这样一种角色,有助于像用一根魔棒那样一下子改变社会秩序。” 但是,早在 1932 年,人们就该看清这基尔希海默所说的吐火女怪。“列宁、托洛茨基和拉德克(Radek)迄今为止对考茨基(Kautzki)的作品——《1919年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作的答复,已经足以使人毫不怀疑,与其说存在着反对使用民主形式的原则理由,不如说这一问题与其他任何问题一样,尤其与合法性和非法性问题一样,必须按个别国家的局势给予不同的回答,并且使用民主形式只是共产主义计划的战略性和策略性措施中的一个因素。”尽管如此,那吐火女怪似乎生命力特强。在1946年12月1日的黑森州宪法第41条中,还可以见出她的踪迹。在后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各州宪法中,这吐火女怪才未再露面。 合法性作为韦伯意义上的正当性的三个典型表现形式——魅力型、传统型、理性型形式之一,以一种理性的规范化为前提条件。“如果法律概念被剥夺与理性和正义的任何有内容的联系,同时立法型国家及其特殊的、将国家的所有尊贵和威严集中于法律的合法性概念被保留下来,那么,任意种类的任何法令、命令和措施都能够成为合法的。”(参见本文第278页和第300—301页;[中译者按]第一章第 1 节中间部分)1932 年流行的法学实定主义必然承认这一逻辑,甚至认为这种逻辑是不言而喻的。 (三)当立法型国家过渡为管理型国家时,措施就突出出来了,这就需要阐明法律与措施的关系。与“单纯的合目的性”相反,提出纯粹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仍不过是对真正问题的一种逃避。在 1924 年德国国家法学者协会第一次会议上,笔者所作的关于民国总统按魏玛宪法第 48 条拥有专政权的报告,首次深入讨论了法律与措施的区分。无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状态和围困状态的经验,还是魏玛宪法期间第 48 条的实践,都把措施当法令、把法令当措施来贯彻。正常的法治国家的桥梁在于立法的授权。一旦这种授权因议会的否定多数而失效,第 48 条就表现为在一个不再有能力决议必要的授权,从而容忍第 48 条的法令实践的议会面前挽救宪法的应急桥梁。 1949 年的波恩基本法想重建古典的法律概念:为了限制基本权利,波恩基本法只允许法律作为普遍的规范(第 19 条第 1 项)。波恩基本法还试图限制蕴含在立法授权之中的通向措施的合法桥梁(第 80 条)。瓦克(Gerhard Wacke)甚至把授权采取一项措施解释为违宪。事实上,即便在波恩基本法之下,也无法避免将措施等于法律;关键只能在于正确认识和安排发展。基本法自身甚至允准“借助法律的剥夺”(第 14 条),也就是说,允准措施法律(Massnahmegesetz)的最重要实例,允准措施对法律最强有力、最公开的入侵。 在一篇奠基性的文章《论措施就是法律》中,福斯特霍夫(Ernst Forsthoff)讨论了措施就是法律的特别性,尤其考虑到措施就是法律为行政法庭的监督提供了其他作为正常法律的运用。 巴勒施泰特(Kurt Ballerstedt)甚至达到这样的结论:经济法作为一个自身封闭的学科不可缺少法权法律(Rechtsgesetz)与措施法律之间的区分,但借助这种区分,就可以更清晰地把握随着国家干预经济而产生的法权问题;即便对于基本法第 2 条第 1、9、12 和 14 项来说,这种区分也不可或缺。 这样一来,法律与措施的区分就进入了法律自身,并且导致了法权法律与措施法律之间的区分。这里所表现出的,无非是向关注生存的管理型国家不可抗拒的发展。合法性是官僚体制的一种功能模式,而在社会上必须关注工业大众的共同体的官僚体制,再也不能与基于国家与社会的古典分离的法律概念和睦相处了,只能让司法概念去适应社会国家的发展。 (四)与关于合法性和机会均等的阐述相关(参前面正文第283—284 页;[中译者按]第一章第 2 节开头),笔者阐明了关于对合法占有政权的三种奖赏的学说:合法性的猜测、暂时的可实施性(Vollstreckbarkeit)与服从(obeissance prealable),及总附加条款的执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这三种奖赏都有巨大的意义,以致没有任何宪法学说、法哲学可以忽视它们。笔者在其他地方已经说明,实际评价立法者在宪法上的监督时,必须考虑到这三种奖赏。即便在法学上站得住脚的抵制权学说,也必须从这三种奖赏出发。尽管如此,人们恰恰依然没有注意到关于正常奖赏的学说。 与此相反,只是在国外的著述中,另一类奖赏——选举法的奖赏才已经引起了兴趣:选举法的奖赏赋予一定额度的选票或者席位以附加席位,从而使得在选民中间出现多元主义分裂时产生一种人为多数。主要实例就是1951年5月9日的法国选举法和1953年3月31日的意大利选举法,即所谓的联合方法。阻挡性附加条款或者类似的防护措施,则是涉及少数的一种否定性奖赏,如果我可以模仿次特权(Sub-Privilegien)这个术语使用一个表述的话,可以称之为次奖赏。诸如此类的选举法奖赏,在很大程度上是典型的。但是,它们具有某种人为的东西,因为它们旨在造成一种合法多数,而上述对合法占有政权的正常奖赏则以这种占有政权为前提条件,并且对任何共同体都同样是正常的和基础性的,以致它们需要得到宪法理论上的重视,并且绝不能以对法权保障的一般反思来了结。 除了对合法占有政权的三种正常的奖赏,除了上述这些更多人为的奖赏,还有另外一些相当特别的奖赏。它们理应在这里得到特别强调,因为这些奖赏与一个绝对具有现实意义、但遗憾的是还很少达到宪法理论意识的问题密切相关;这个问题就是宪法内部的区分。宪法一方面是组织性和程序法规定的制度,另一方面又能够包含着实质性法权规定的总和。通过接纳入宪法,相对于大量其他正常的实质性法权来说,程序法规定被赋予了一种更高规范的优势和庄严。我相信,在传统的立法型国家整个迄今为止的制度发生转移之前,是该意识到这一区分的时候了。就这种特别奖赏而言,一个政党或者政党联盟会利用制定宪法(对此简单的多数就足够了),甚至制定宪法法的时刻,使后来的简单多数受制于某些实质法权的规定(参见上面正文中的第 305 页;[中译者按]第二章第 1 节后面部分)。也许,这种倾向就蕴含在多元主义发展的进程中。无论如何,对这些特别奖赏的讨论,将有助于深化在宪法理论上思考法治国家和权力划分的当今状况。自由主义法治国家之父约翰•洛克有一句反对转让授权法和立法权的格言经常被人引用,这句格言恰如其分地说明,立法者的存在不是为了创造立法者,而是为了创造法。与此类似,人们可以说,宪法的制定者还有宪法法的制定者的存在,是为了创造出好的立法者和立法程序,而非为了自己创造法。若不然,即刻就把宪法当作一种法令大全,连同多年的计划一起来发布,就是合乎逻辑的了。不过,就像已经说过的那样,朝着这一方向和各种宪法的倾向(eine Tendenz in diese Richtung und die Verfassungen)已经越走越远。新的印度宪法已经有 315 条和 8 个附录。谁认为这很好、正确,就至少应当知道,这里所涉及的,已经不是在迄今为止欧洲宪法法及其关于法治国家和权力划分的学说基础上形成的那种宪法了。 (五)在“合法性问题”一文中的第 1 条至第 6 条注释里,我为合法性与正当性之间关系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一种总括性概览。高级教士、中央党领袖卡斯(Kaas)教授在 1933 年 1 月 26 日致民国总理施莱歇(von Schleicher)的公开信中表明,在 1933 年 1 月30 日之前的那个决定性的星期,关于合法性和正当性,德国一位权威性的政党领袖和联盟领袖是怎样思考的。卡斯在那里谈到了涉及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和更改选举日期的法学思想,明确警告民国政府注意“施米特及其追随者们将整个国家法相对化的基本倾向”。他所说的这些追随者指谁,指各种学说的一些代表,抑或我当时的朋友波比茨、奥特(Ott)和马克斯(Marcks)或者其他任何人,我已经不得而知了。他如何得知我的宪法法思想,我也不晓得。看我的著作或者简单地当面垂询我,他也没有时间。我也从来没有参与关于国家紧急状态的闲谈,因为我知道,由此只会把一部宪法的合法性交给宪法的敌人;因为我认为,与合法占有政权的奖赏相结合的合法可能性绝没有穷尽。我的国家法观点产生自我的著作,不是产生自传闻或者联想,也不是事后通过倒叙法产生自后来的、结构完全不同的、只是从魏玛合法性的崩溃中形成的处境。 当时,在 1933 年 1 月 23—30 日那个决定性的星期,国会必须被重新解散是肯定了的。国会只不过还是否定性多数的行动和表演的舞台罢了。再次解散国会并不是非法性。问题仅仅是,什么样的民国政府将在即将来临的选举斗争中执掌国家政权,并为自己利用合法占有政权的奖赏:是施莱歇尔政府,抑或如卡斯所要求的那样,从“有承载能力的联合政府”中产生的新任命的民国总理——希特勒。一个与普鲁士帝国代表委员会(Reichskommissariat Preussen)结合的民国政府的权力如此之大,产生对现代国家的权力地位的念头就不难理解了。但是,在 1 月 31 日之前的决定性日子里,民国政府向一种错误的合法性概念投降了,要在宪法法院再打官司的威胁变成了行之有效的合法武器。按照高级教士卡斯1933 年 1 月 26 日的公开信,任命希特勒为民国总理必定表现为走出危机的真正合法出路。 新附加的斗争手段以及在宪法法院打政治官司的威胁,触到了民国总统兴登堡(Hindenburg)的处境甚至其自我意识最内在的神经。因年事已高而离群索居,在群众民主方法的张力中,并且由于一种突变的可能性,这位中立政权的承载者行事就像是一种不合时宜和不合时代的对立。兴登堡忠诚于自己对宪法的誓言,但这一宪法究竟是什么,兴登堡出于自己的本质的一无所知。这样,他教导自己做一个无可指责的人,这教导最终却导致其誓言和忠诚的对象只不过是一个通过的程序、一扇可以向任何敌人敞开的大门,只要这个敌人显得是“有承载能力的联合政府”,并由此使自己成为合法的。
合法性与正当性——重印附言
书名: 合法性与正当性
作者: [德] 卡尔·施米特
出版社: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作名: Legalität und Legitimität
副标题: 经典与解释·施米特文集
译者: 朱雁冰 | 冯克利 | 李秋零
出版年: 2015-1
页数: 264
定价: 39.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施米特文集(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208125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