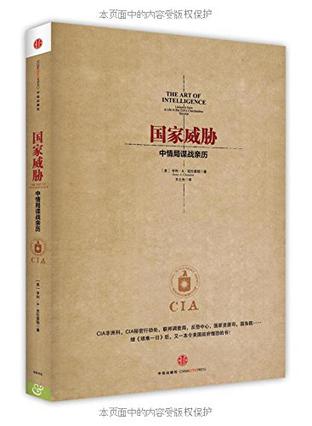2002年夏,我踏上了新的使命。在中情局的秘密行动处服务二十年,最后10个月还领导中情局介入了阿富汗战争之后,是该换花样的时候了。 这个任务就是我的退役。别了,MI-17直升机,无人机“捕食者”,M4突击步枪,格洛克19型手枪,镀陶瓷防弹衣,防疫接种,测谎仪,伪装掩护,连最基本的谍报术也不要了。别了,不用躲避盯梢,不用运作特工,不用消除恐怖分子的影响了。然而,分配的任务却要求我进入一种陌生的文化,调整态度,换换身份。 我又回到了大学,当起了学生。 美国中央情报局给了我学术休假,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访学。新的任务比近期一些经历更沉稳,但令人兴奋。完整的一个学年,可以沉溺于知识之中。我要饱餐一顿涵盖政治思想、军事战略、中国、历史、外交政策、恐怖主义和哲学的课程的盛宴,大肆阅读。这一切令我回味无穷啊。 搜索2003年春季学期的课程目录,我偶然发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情报学。引人入胜的课程名称“谍报艺术与诀窍”,让我去研究开课教授詹妮弗•西姆斯博士的背景。她的简历引人注目,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府里。 作为一个仍在中央情报局领工资的老牌情报专业人士,我觉得有义务选这个课程。我也猜想,该课程内容有趣,容易学。 课程很滑稽的。我们探讨了美国的大间谍头目之一乔治•华盛顿如何以精湛的战术谍报技巧运作特工,然后出色地利用其具有战略价值的情报。我们研究了美国南北战争中谍报能力的进步。我们了解到,林肯总统在白宫电报室度过了许多日子,把它变成他事实上的情报和指挥中心。我们跟踪整个二十世纪无线通信、飞机、雷达、卫星等技术奇迹的来临,是如何改造谍报工作的。 我们观察到,大多数打造国家安全政策和发动战争的政治领导人不像华盛顿和林肯,未能理解或欣赏谍报工作。他们还跟不上地缘政治的变化,部分原因是情报收集、情报分析和政策执行之间的差距。我们认真考虑了政府和更广泛的社会如何看待和对待情报人员,其评论摇摆不定,有深恶痛绝的,也有卡通式幻想的。对于情报人员无知的期望,有时是不合理的期望,或高或低,沉重打击了整个美国历史上的这些人员及其机构。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对于谍报的集体无知,不仅破坏了我们的谍报能力,而且最终伤害了其服务的决策者和公民。 课程虽然过瘾,却并不容易学。西姆斯博士要求投入更多的研究和思考,是我始料未及的。有多少东西我不知道,有多少东西我学到了,想想都令人难堪——即使我有多年的间谍和秘密行动经验,还在几个大洲参与了战争。虽然对自己的无知懊恼不已,我还是痴迷于该学习经历的。 在此学术假期间,我开拓了眼界,远远超出了谍报业务。20年来这是第一次,我不是仅仅关注眼前的情报作战任务。有了研究和思考的机会,我更好地理解到,这个世界正在迅速转变,尤其是在冲突、风险、竞争与合作的性质方面。但有一个共同点:情报的价值增加了。2001-02年度,我们的阿富汗战争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我们这个时代的地缘政治趋势的变革,许多是由技术迅猛进步推动,表明情报会在日益相互依赖的复杂世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我们对于情报的集体理解和赞赏,远远落后于我们国家的需要,整个美国历史上经常如此。 美国及其盟友于1989年11月赢得了冷战,铁幕崩溃之后,许多负责任和受尊敬的领导人,如已故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对于是否需要强大的情报表达了他们的怀疑。有些人质疑秘密行动机构的必要性。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兑现“和平红利”,情报预算削减到伤筋动骨。身为这十年预算崩溃中的现场行动人员,我亲眼目睹了行动的塌陷和特工网络的凋零。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关闭情报站。仿佛我们的领导人预计,地缘政治风险行将消失。 一些中情局领导人大声质疑他们的任务含糊不清。有些人因困惑和厌恶而跳槽。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情局资深人员甚至接受了新世界没有真正敌人的概念。CIA秘密行动处一位科长米尔顿•比尔登宣布,俄罗斯不再构成任何重大间谍威胁。他的观点越来越吃得开,直到一连串俄罗斯渗透活动被曝光,如奥尔德里奇•艾姆斯渗透中情局和罗伯特•汉森渗透联邦调查局。这些叛徒让美国国家安全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们还向俄罗斯管理者提供了情报,导致了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十多名勇敢的俄罗斯特工遭到处决。虽然美国与俄罗斯合作,就像与中国合作一样,好处显然更多,但间谍活动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大国是美国在外交、科学,商业等等上的合作伙伴。他们也是从事间谍活动的敌人。俄罗斯和中国都可能有更多的秘密情报人员在美国境内,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比在冷战高峰时还要多。 然而,在冷战后的繁荣平静期,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享有了妄想中的喘息机会,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没有严重的威胁和致命的敌人。政策的书呆子们奢谈美国无可匹敌的霸主地位,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和自由市场原则普遍盛行、势不可挡,不受阻碍地阔步向前。生活是美好的嘛。 随之,基地组织袭击了美国本土。这是在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和他的19名劫机者杀害了2,977人。罹难者大多是美国人,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公民。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印度教徒等等在那一天殒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被摧毁,在堆积如山的城市废墟中,留着人类遗骸的丝丝缕缕。一些受害人选择跳楼赴死,牵着手,逃避被烧毁和在大楼倒塌时被压死。华盛顿以外,地球上最伟大的军队总部五角大楼遇袭,其一侧轰出了一个深深的黑洞,冒着浓烟。美国的男女军人死伤者不少,散落在整个走廊。 联合航空93号班机的英雄乘客,在这严峻的一天是唯一的有效应敌者,并且制服了劫机者。飞机失控,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附近农田触地爆炸。这支市民队伍,成为一种自发的自组织的非国家行为体团队,他们用手机收集情报,分析他们的处境和风险,策划和执行了一次大胆的反击。飞机上的33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都死了,几乎可以肯定救人数百,其中可能包括我们首都的政治领导人。 美国和全世界感到震惊和愤怒,努力拿捏着这次攻击意味着什么。这个敌人是谁?为什么呢?美国为保护其公民做了什么?可以做什么回应呢? 那个可怕的日子,迎来了一个四周漏洞百出的新感觉。市民想知道,他们的社区会不会被攻击。侵犯我们的家园,引发了一场关于战争与安全的辩论,焦点是情报。国会后来建立了9/11调查委员会,强调情报的作用。该委员会的结论和政策领导人的意见很清楚:9/11是一个巨大的情报失误,而不是政策失败,探索政策不是委员会的许可内容。 委员会和政策制定者们中的许多人曾经投票决定削减情报预算,但现在异口同声:情报出了岔子。现在要紧的是情报。美国需要更多的资源搞情报呢。 自9/11事件以来十年,美国情报部门的预算和官僚机构是没边儿的增长、复制和混乱,简直是群魔乱舞。到2011年,每年的情报预算从数十亿美元激增至750亿美元。一夜之间,美国的政治领袖成为了情报的吆喝者。他们建立了更关键的委员会,花了更多的纳税人的钱,订立了更多的规则和规例,并建成了更多的以华盛顿为中心的组织,如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国家反恐中心(NCTC)和美国国土安全部(DHS)。 与此同时,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与国会一起,选择性地滥用中情局争取政治利益,对中情局提出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乔治•布什总统的一些工作人员试图破坏中央情报局卧底官员瓦莱丽•普莱姆的诚信,甚至人身安全,因其丈夫乔•威尔逊大使曾公开批评布什领导的白宫。不管是为了政治利益,还是其他原因,白宫官员怎么能危害中情局官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掩护身份和生命呢?怎么能危及她的特工网络呢?外国人还冒着生命危险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哪。白宫高级顾问“滑板车”•利比因为对泄漏事件的联邦调查不合作,被判刑入狱了。 除了这可怕的背信,美国总统布什和他的团队全盘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其情报服务,尤其是这些服务符合政府政策期望的时候。中情局长乔治•特尼特与白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也许是太接近了。我在戴维营、白宫战情室,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布什总统汇报2001-02年度情况时,他总是询问有关行动,鼓励我和我部署在阿富汗的人。他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道义上的重要支持。他怎么能允许,或许纵容,对中情局卧底人员的政治攻击呢? 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月上任,他的司法部以入狱收监威胁中情局官员,因为他们执行了前届政府的合法命令。这是试图将先前的政策目为刑事犯罪,作为对中情局的一种惩罚吗?还是仅仅为了政治利益而把情报人员推来推去? 超过两年,司法部的检察官们在追究CIA行动副局长何塞•罗德里格斯,一个可敬而勇敢的领导者,结果发现没有不法行为的证据,而且政治聚光灯也暗下来后,只得作罢了。 尽管当时的中情局长迈克尔•海登反对,每一个健在的前中情局长也反对,奥巴马总统还是公布了已由上届政府批准并指示的强化审讯技术的细节。奥巴马政府试图讨好民主党分子,而牺牲了中央情报局和人员。 奥巴马总统越来越倚重中央情报局。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在南亚发动的对特定目标的攻击,比布什总统整个任期内下达的更多。奥巴马让中情局负责追查和杀死更多的恐怖分子,并在任务胜利完成后,打电话祝贺一个个行动官。他渐渐地信任中情局的评估,而且得到了回报。中央情报局发现了本•拉登,这让奥巴马总统获得了作为总司令捞取非凡的政治信誉的机会。他勇敢地下令中情局和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发动武装行动,在2011年5月1日诛杀本•拉登于巴基斯坦的藏身之处。 在9/11之后的十年间,欧洲盟国加入了政治上的反情报斗嘴,起诉中情局官员,而忽略了自己的情报官员也参与了变味的联合行动共谋。意大利是最好的例子。中情局怀疑外国情报合作伙伴及其政治主人的可靠性。与此同时,外国情报和安全部门盘算着他们能在美国情报界里信任谁。他们自己在辩论,哪个美国机构负有什么责任。谁又能责怪他们呢?所有那些记者泄漏,高级情报官员和各种机构和部门的混乱扩散,角色繁多,扑朔迷离,重叠授权。例如,新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没有规定其限制于协调美国各情报机构,却获得了一个礼宾员的班子,接待来访的外国联络官员。该办公室后来膨胀到三千余名工作人员和承包商,他们大多在找任务来做。 就在后方,美国公众的情绪变化很大。他们钦佩中情局官员,尤其是其对付基地组织渗透到公共领域的主导作用。9/11后为国家而战丧生的第一位美国人,就是中情局准军事人员强尼•迈克•斯潘。对于这位倒下的美国英雄,有广泛的新闻报道,彬彬有礼,这是理所应当的。对于我们中情局的人,损失尤为严重,因为迈克是我们所钦佩的人:无私而无畏。 然而,9/11之后只过了几年,美国和它的某些领导人就对中情局的作用变得模棱两可了。某些部门对情报的怀疑和反感日益增长,特别是审讯技巧和必杀秘密行动。在国内搞谍报也有合理的担心,因为情报缺乏,且挑战公民自由。 大众媒体及娱乐业炒作、歪曲情报活动的方方面面,从描绘超级英雄肖像到炒作可恶情报人员形象,以及谍报任务的不雅形象。 更根本的是,政治领导人和律师们想方设法确定我们是否真的与“基地”组织开战了,如果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敌人。他们是归宿民事法庭的罪犯呢,还是运到关塔那摩阴曹地府的敌方战斗人员?为什么批准中情局操作无人机去杀死指定的敌方首领,也许还包括他不幸的家人,却反对中情局官员在审讯过程中迫使敌俘放弃睡眠,违者可能法办? 为什么中情局处于这一冲突的最前沿?这不只是情报收集,而是全球范围的庞大隐蔽行动。为什么搞这么多的秘密行动?其他的治国工具呢? 我参与了一些这种行动和政治冲突,尤其是在9/11之前和之后的阿富汗,无论是在外勤地效力,还是在首都华盛顿。我经常坐上靠近拳击台的座位,带着敬畏和厌恶观看美国的谍报任务和对外政策一波三折,寻求保家卫国,但有时也添乱。例如,公然入侵伊拉克,接着是软弱而有气无力占领,把9/11恐怖袭击后带给我们的全球的同情破坏了,也把我们最初在阿富汗的成功所带来的钦佩和美誉弄砸了。 这一切的根源,似乎是决策者、民选官员和领导人对情报的欠了解,无论是在政府中,还是在更广泛的社会里。我不知道多少是属于诚实的无知,多少属于政治家、记者、艺人和奸商的玩世不恭和操纵。如果谍报在我们的国家安全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被视为日趋重要,如果市民需要了解这个神秘的艺术,那如何最好地完成呢? 这里是悖论所在。由于间谍中间,尤其是中情局的秘密行动处对于保密具有功能和文化偏向,情报界领导人经常驳回公众宣传或教育的需求。政治领导人普遍会加强这样的态度,不想与自己有分歧的任何专家意见在公共领域露面。事实上,政治家要保护情报为自己所用,甚至对自己内部都保密。这种必要的保密性,特别是涉及谍报来源和方法,往往阻止公众更深地了解情报。 西姆斯博士在她的课程上课期间和之后,和我讨论这个悖论。我们还讨论了情报的伦理。我把她介绍给伯顿•格伯,那是一个很好的朋友,退休的中情局间谍头子,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旁听了西姆斯博士的课,还做了间谍伦理讲座。这引发了重要的辩论。 西姆斯博士和我一致认为,情报研究还不成熟。我们需要更多的参考点,更多的资源,更加突出重点,生动活泼、显示尊重、消息灵通的讨论。我鼓励她整理和编辑情报教材,这是她早就在考虑的东西。她说服伯顿做合作编者。我同意在书中写几个章节,“情报与战争:阿富汗2001-02年度”和“国土情报和安全”,书名《转型中的美国谍报》,由乔治敦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的。 该书对于有志于从事情报学术研究的人是有用的文字,受众很重要,但人数相对较小。我很自豪于自己的微薄贡献。 我的学术休假结束后,于2003年又回到了秘密行动处,当为期两年的国家资源科长(NR),那是中情局最敏感的组成部分之一。国家资源科在美国各地设有办事处,与美国执法机构、美国公民和公私机构合作,推进秘密行动处的任务。我对祖国有了新的认识,加深了对中情局的好感。我也掌握到第一手资料,私营部门在国家安全上的核心地位。作为资源科长,我看到了美国技术的隆重推出,而赢亏则日益全球化了。美国私营部门的高管和专家在五大洲各个角落工作,他们对异国他乡的切入和理解,让我刮目相看。在情报方面公共/私人的相互依存,让我瞠目结舌,还有其丰富的情报资源和我们没有掌握的潜力,也是富可敌国。 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局限性似乎在于,对于情报缺乏负责任的公开研究和对话,特别是情报在性质不断变化的风险上的作用。的确有呼声,但往往是不知情的,另有政治动机,或者愤世嫉俗的间谍老兵在说话,他们面临着一个新的世界,不符合他们的思想观点或职业期望了。 作为一个秘密行动处的官员,我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责任。我被官方禁止从事任何此类的公共宣传。此外,我在学术课本中写了几章,已经打了中情局的文化规范限制的擦边球。 2005年,形势所迫,我进入了公众角色,这我没有预料到。国务卿赖斯让我做反恐协调员,级别是无任所大使。这是总统任命的,需参议院的公开确认。我接受了任命,意识到我的间谍生涯结束了。 我从秘密行动处这个封闭的秘密世界一跃站上全球公开外交的舞台,成为总统和国务卿的反恐政策代表。我又开始了新的生活,从间谍到外交官,从秘密行动到国际电视采访,从一大堆的别名到高贵的称号。最重要的是,我从情报收集者转移到情报的消费者,从行动员到政策顾问、政策制造和实施者。当布什总统第一次在国务院见到我,他问国务卿赖斯,“割喉者做了外交官?行得通吗?” 我曾在许多不同的机构和部门做反恐工作,我了解跨部门工作程序,所以从行动到政策操作的过渡并不难。我多年浸淫在全球反恐行动中,在许多国家的合作关系也有助益。替国务卿赖斯工作的18个月期间,我大部分时间在国外旅行,与我们的大使、军事指挥官和外国合作伙伴协同工作。在这种转变中,可能有一些失误,但我努力学习和提高。但在我的经验和理解方面有一个重大的差距。我大大低估了这一使命的公共部分的深度和重要性。我主持了一百多次世界各地的采访和新闻事件。国内外观众似乎渴望有人来参与,讨论反恐政策和情报的支撑作用。不管怎么样,他们希望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倾听。 在这个任务中,我感到震惊的是教育和负责任公开讨论的重要性。我勤奋工作,在这些开放的论坛代表我的国家,从波哥大飞往柏林,再到贝鲁特,与公众沟通。 我于2007年从美国政府机构退休后,多亏妻子多年的支持,我转移到私营部门工作,来支付孩子们的大学学费。我也想享受更大的灵活性,能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我意识到了,我琢磨敌人的时间超过了思考其他人,这一下击中了要害。为政府服务26年后,退休是正确的选择。 然而,我的心里将永远珍视自己当过中情局行动员的经历。我的服务不仅仅是职业生涯,确乎是一个伟大的使命,一种生活方式。有了那种服务带来的荣誉和特权,那种爱国之心,随之而来的还有责任。由于我独特的经历,遍及反恐、学术界、自然资源、公开外交和私营部门,我觉得对于教育责无旁贷,尤其是考虑到地缘政治冲突方面的巨变对于情报任务和情报人员提出的相关要求。 悖论依然存在。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如何保持静默职业的文化规约,同时寻求晓谕公众,从而促进理解和支持情报界?我寻求在退休间谍的光荣的自由裁量权和积极公民的公共责任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 我退休时,并不打算写书,但拗不过文学经纪人安德鲁•怀利和斯科特•莫耶斯,还有其他人。斯科特在平面媒体第一次读到我的。然后,他做了一些研究,比如给一个共同的朋友,比尔•哈洛打电话,后者担保我成功。哈洛曾经替局长乔治•特尼特当中情局公共事务官,令人敬仰。斯科特和安德鲁邀请我去他们的纽约写字楼,说服我,可以且应该把我的知识作更多的分享。 依托回忆,添加其他参与者的讨论更新资讯,我写下了个人的故事,传达关于情报、战争、政策深层次问题的理解。故事有我直接参与的,也有我当时指挥手下人员的,作为人情故事也值得一看。当然,谍报最终是对人的:那些从事间谍和秘密行动的人,那些分析情报的人,以及那些使用情报的人。谍报也涉及那些招聘目标和外国特工,以及那些从谍报行动和好的坏的情报形成政策的后果中受益或受害的人。 本书的第一部分涉及业务基本面。我曾从事24年的情报收集最受关注,主要是因为这是我最熟悉的。谍报最有争议的方面,即秘密行动,值得大谈特谈。我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秘密行动是2001-02年度的阿富汗战役,作为主要例子有几个原因。首先,我发挥了领导作用,写这些有权威性。其次,这种冲突可以作为谍报融入秘密行动、战争和政策的优秀案例研究。这个战役是未来的窗口,非国家行为体作为敌人和盟友,以及非敌非友的一个复杂的混合。第三,因为鲍勃•伍德沃德等人,此事件有前所未有的开放信息量,可以用来讨论原本禁言的题目。第四,人物扮演了戏剧性的,引人注目的角色。第五,南亚将多年维持美国国家安全关键地域的状态,我们需要总结经验教训。 本书还概述了新的风险世界,情报搜集和隐蔽行动在这样的环境中的作用。这包括勘探战略原则和情报和政策之间复杂的动态过程。本书回顾了冲突、情报、政府和社会的联系。 通过讲述我职业生涯中的经验教训,外加一些他人的经验和意见,我希望对谍报术有所启迪。我试图说明谍报的价值,以及它如何能够保障自由制度,并推进我们日益网络化、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社会。这本书也将汇报情报人员对我们国家的价值。 本书的书名是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已故局长艾伦•杜勒斯的礼赞,他在1961年写了《情报术》,也献给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军事家孙子和《孙子兵法》。杜勒斯的书,第一句话就是引用孙子的。我也感谢指导过我的许多其他的人士。 毕竟,谍报不完全是新玩意儿。 孙子强调,兵法是国之大事,是国家所需要的。他还说,“兵者诡道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指的是情报的价值。 中国古代的道理今天仍然成立。战争和情报不仅对国家越来越至关重要,而且对非国家行为体和公民也不可忽视,因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冲突时代,自有独特的特点和要求。 因为这种划时代的转变,情报的世界处于大变之中。我们的情报界受冲突与合作新势力东拉西扯,为不断变化的政治利益所扭曲,尽量有效地发挥作用。在美国,此综合征尤为严重发作,社会对情报的作用持有不同的期望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意见。我们考虑间谍时,在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夹杂着尊重、浪漫、知识、无知、怀疑、恐惧和厌恶。就像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的,“我们有情报过敏症。”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努力理解和支持情报机构和情报专业人员。 随着战争的性质继续转变,谍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全体公民,而不仅仅是政府官员,需要更好地掌握情报,包括其能力和它的极限。更好的情报可以保护和促进美国和我们的盟国的利益,有利于促进全球自由民主。这就是我为国家服务的理由,是我仍然信守我的 “宪法”誓言的理由。这也是为什么我写这本书的理由。 我希望将毕生所学传授一些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