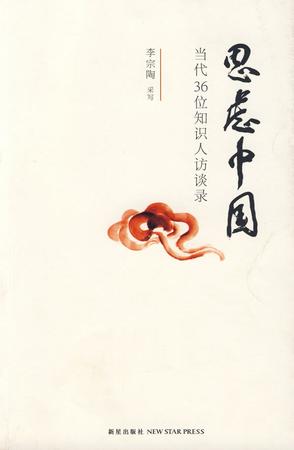许纪霖 第一次认识本书作者,在五年前。那时她还是《新民周刊》记者,为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北大聘任制度改革,上门采访我。在我家小院坐下,递上名片:李宗陶--看这名字,老气横秋的,以为是书斋里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与眼前这位纤细单薄的?南女孩无论如何也对不上。不过,一开始提问,倒是人如其名,问题相当专业,仿佛也是一位学院中人。 经常接受报刊采访,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是否进入状态,与记者的提问直接相关。碰上大而无当、不知所云、人云亦云或早有答案的问题,你只有苦笑的份儿。而那些真正内行的、有内?的提问,会让你精神抖擞,如注射了一针吗啡,慷慨激昂半天。 李宗陶就有这样的本领,会让她的被访者不知不觉,进入她预先设定的情景,有偶遇知音之感。好的记者,各有各的绝招,有的犀利,具有挑战性;有的亲切,让人有一吐为快的冲动。李宗陶的风格,在我看来则是专业。仿佛是你的同行,将你的前世今生、读过的书、写过的文、说过的话,通通琢磨透了。她设定的问题,不是按照自己的想象与逻辑(初出茅庐的记者,往往这样),而是?着对方的自身理路,步步逼入受访者的内心世界。虽然偶有失手,但大多数场合,皆是大有斩获,得胜回朝。 一次成功的采访,与其说取决于被访者的水平和口才,不如说看记者肚子有多少货色。作为《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笔,李宗陶的成功,来自于她的灵感加好学。灵感是先天的,天资愚笨,后天再如何努力,也终究有限。看她采访录中那些知性与感性交错的好问题,就明白这个女孩的灵性。她出身于书香之家,命运的阴差阳错,却让她读了一所工科学校。毕业以后弃工就文,改行当记者。没有受过新闻系的刻板规训,反而让灵性尽情发挥,淋漓尽致。不过,灵气再足,也有挥霍一空的时候。好在她对文学、历史与宗教哲学有近乎膜拜的热忱。买书、读书、写作,成为她最大的癖好。她的每一次采访,都做足了功课。事后将录音全部整理出来,沙里淘金,提炼出最出采的篇章,如同王世襄老人下厨,一斤菜要掐掉七两,只留那一点点嫩尖,炒成美肴。 李宗陶接触的对象,基本在文人圈:学者、作家、艺术家。以我个人之偏见,她做得最好的采访,上等是作家,学者居其次,艺术家压后。个中原因,恐怕与心灵是否契合相关。即令是名牌记者,也并非全能型、全天候,总有自己擅长的领域,也有无法涉入的死角。记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一位史学名教授,曾经对我谈到,当年定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其导师魏斐德教授,建议她研究上海的黑社会。这让她为难。这位晚清名儒严复的后裔,家族里面有的是文人、学者,也有大商人,但从来没有出过强盗!最后她选择了近代中国的大学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后来又研究上海的银行与白领,如今已是继魏斐德之后,伯克利东亚研究的领军人物。 李宗陶身上的文人气息,注定了她最能把握的,不是社会的底层,而是都市的文化精英。有好几年,她不断地去各地采访艾滋病感染者群体,撰写系列报道,还应约写关于他们的小说。大概经验感受与这些对象有隔,我总觉得她写得很累,有点勉为其难。虽然艾滋病的题材是全球热点,也政治正确,但一个人只有对自己的内在志趣有所自觉,才算真正成熟。果然,这一两年,当她回到熟悉的知识人圈子,又重新变得游刃有余。 我在华东师大任教,经常邀请一些海内外著名学人到校演讲。李宗陶对学生生活有天然的兴趣,一接到讲座通知,无论什么主题,几乎必到,成为丽娃河畔的常客。一般采访者,习惯会后私下提问。但她放下记者的矜持,每每如学生一般,抢先在会场上举手发言。因为早早做过功课,问题对上讲者的口味,让那些大学者们顿时兴趣盎然,气氛由此转热。在我的记忆之中,有一两次,仿佛还有打破僵局之功。书中的托马斯·班德、许倬云、冯象、阎云翔、黄克武等人的访谈录,皆是由讲座到采访,形成佳话。 以我孤陋之见,专跑文化人、知识人的国内记者中,写得最好的,当属"二李"。一位是《南方都市报》的李怀宇[现已离职],另一位就是李宗陶。"二李"颇多共通之处,比如有纯正的知识文化趣味,也各有千秋。李怀宇对老派文化人深怀敬意,浸润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情趣之中,对文人逸事如数家珍,仿佛身临其境。李宗陶则有着女性的细腻,对文化人的音容笑貌有敏锐的观察,笔下更富时尚感和学究气。 李怀宇的采访录已先行出版,在读书界口碑不俗。此刻我在海峡彼岸的"中央研究院"访问,刚刚从一位台湾朋友的书桌上,就发现一册打开了的《访问历史》。如今李宗陶的采访录也即将面世,奉命草书小序一篇,以为恭贺。期待双李之作,比翼齐飞,透过优美文笔,为中国知识人的文化传统,留下令人怀恋的精神痕迹。 2008年早春于台北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