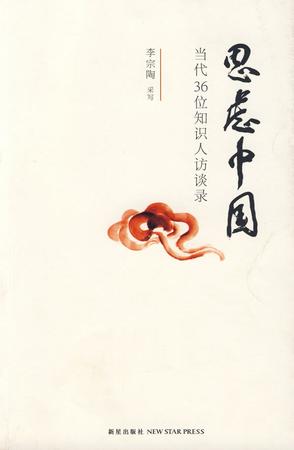--2005年年终小结 这一年,我没有写多少稿件。但那些写过的人和事,还在。 第一件几乎影响了一整年的采访事件是对马骅的追索。其实我要写的,是接马骅班的上海去的8名志愿者,其中医务工作者占了7名。我猜,马骅是他们的暗示,肉麻一点说,是他们心中的一盏灯,宛如《蝴蝶梦》中的丽贝卡。 我去了云南,上到4200米雪线的时候,该有的高原反应都有了。藏族司机农布扎西好心,一路不停讲一点也不荤的荤段子,后来他甚至唱歌了,想让受罪的人分点神。大家停车吃饭的时候,我靠在副驾驶座上吸氧。有同行者回上海后批评我:"给三个人吸的氧,都叫你一个人吸光了。" 那是冬天,手脚冰冰凉。记得路过一个小饭店,农布扎西不见了,一会儿他抱了一个灌了热水的玻璃瓶回来,水只是温热,上面还漂着几朵油花。它触到冰凉的手指,让我温暖。 所到每一处,都有当年那个复旦诗歌少年的影子。从拉着窗帘的缝隙里望见他宿舍桌面上一只打火机和一瓶没有开封的橘子水,我承认,心嘭嘭直跳。 他并不是那一拨诗人里最出色的。但在云南支教时所作的《雪山短歌》组诗被公认是他最优秀的作品,让那些当年跟他一道趿着2块钱的所谓NIKE拖鞋在大家沙龙里晃进晃出的同道们,深深地,深深地怀念他。直到今天。 记得回来后,曾经无意中讲起,如果不是高原反应,我愿意留在那里,当一名随便什么课的老师。这不是矫情,相信有一天,会如愿的。 有人已经先走一步了。前不久听说,那批志愿者中的张医生(原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分院外科医生)在一年志愿期期满后,彻底留在那里了。他跟妻子说,要么你来,要么那什么。妻于是随他去了迪庆。那批医生中,我跟张医生谈得比较深。他说,他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喜欢那个地方:也许是不用再随着气场跟人谈论房子、车子和位子,也许是没事的时候可以跟当地朋友开辆吉普车去大草原上踢球,也许是人与人之间比较"开心",也许是从小饭馆厕所出来的时候,会有陌生人拍拍肩膀:"谢谢你,我老婆那个刀开得真好。"跟马骅一样,他喜欢的,就是这些简单的东西。 2005年春节之前,我去了河南上蔡。那组报道《这个春节有点暖》,算是两年多来15篇关于艾滋病深度报道的最高水平。它没有火气,没想讨伐?,没用大词语,却揭示了表象后面的复杂性。 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一个"艾滋病记者",我关注的东西挺多。我相信,如果写摇滚,我也能写得比较像样。但有段时间,这个主题一直笼罩着我,有限的所见所闻和阅读让我感知到它的重要性。 感觉自己在公共健康领域里的知识不够用,而国内目前又没有特别专业的机构能让记者吸氧时,我决定申请国外的奖学金。 等待面试电话的那些夜晚,手心总在出汗,那些认得的英文单词都飞起来了,然后就不认得它们了。我通过了。到美国之后,项目主任说,你是从60多个国际申请者中挑出来的。 在美国的日子,是平生第一次"独立"的经验。是海绵吸水般的求知和各种原因引发的泪水的打包。在无助的日子里,总想着,会有个奇迹,在街的拐角处等我。 我的英文,远没有期望的那么好。开始听那些专业课时,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总算熬过来了。最后一晚同学聚餐告别时,我能用最简短的语言跟大家幽默来幽默去,这让人有点得意。感谢可爱的美国同学们,教会我那些俚语。 如果哪里失火了,或者飞机掉下来,头100个冲到现场的记者里,一定没有我。我跑不大快的,不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速度型记者。所以,试试从其他方向突破。 信息源几乎是坐在家里等来的,那些采访过的对象似乎都很乐意再向我提供消息。可能是在工作交往中他们感受到我的认真,然后,觉得交出来的作品还不坏。 没有什么谋划的天分,只是在采访过程中用心体会,然后似乎,会被一种力量牵着找到一种最适合的表达方式,包括结构和语感。有些东西,是不能硬来的,否则,端出来的饭菜,姓"僵"。 每次跟高手对话都有点绝望: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书,我还没有看过啊;要看到哪一天,才是个尽头啊。但事实上,看书的过程很美妙,它甚至超过写完一篇自鸣得意的稿件后的愉悦。 记得小学三年级时的一篇作文,我抄了条《少年文艺》上的"好句子":我们呼吸着大自然的新鲜空气。老师在这句下面划的波浪线那么浓重,以至于我再也忘不掉它了。老师是有远见的。不管兵荒马乱还是太平盛世,不管职业生涯处于高峰低谷还是平平淡淡,始终保有一种"呼吸大自然新鲜空气"的能力,多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