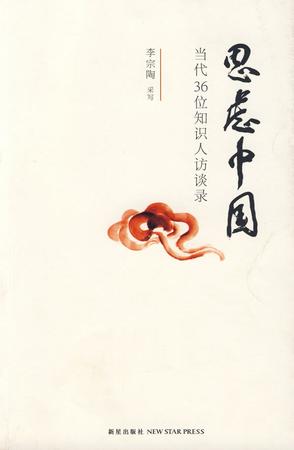记者:您跟王小波那段师生情谊已经很有名了,想听听您对他小说的看法。柏拉图宣扬"哲人王"理论时,自许为哲人王,并把人分为所谓"金、银、铜"几等;王小波著名的黄金、白银、青铜时代三部曲,是不是受此启发? 许倬云:应该有一些吧。小波是用嬉笑怒骂来反映非常严肃的主题。你看他的人,松垮垮的,老穿一件大汗衫,坐无坐相,站无站相,到我办公室里来聊天,我们两个脚都跷在桌子上。但他对事物的感受力非常强,极敏感。他的心非常善良,同情心极高,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我跟他谈得拢,也就是在这方面有很多共鸣。你看他回国以后写的《红拂夜奔》那些,都穿插古代故事,却倒着写,整个儿颠覆了,每个故事每个人物,都影射今天。他把他下乡那段故事放进去了,不像先前的三部曲,虚构为主。我们聊过许多历史故事,以历史故事为背景,可以有更广阔的叙事天地,而不仅仅限于伤痕文学。 他的文才,唔[沉吟],他能跑,他能跳,他不规行矩步,但他不够精到、有力。他跟张承志刚好相反,张承志的文字非常简练,《北方的河》,那个文字真好。我跟他讲,要炼字炼句。我把他的文章改给他看,说这几句是多余的,那几个字是白加的,他开始并不服气,但他也知道文字力量所在。我说,啰嗦不是力量啊,你耍刀舞剑,力量在锋尖而不是在后面的红缨子红穗子啊。 我确实很喜欢他。我推荐他到台湾《联合报》参加小说比赛,送了好几篇,最后中篇得了第一名,拿了20万元台币,差不多相当于5万元人民币。80年代5万元可不是小数目,可有得用哪。[许夫人曼云说,"他就不用上班,回家专心写作去了。"]所以,他很早就用computer写作了。银河我也很喜欢,当时在匹兹堡大学的那么多中国留学生里,她学习最好,别人没有她那么钻,而且一下就抓准了题目,讨论班她表现最好。 记者:小波的噩耗传到您这里时,是什么情形? 许倬云:我是很快就知道了。当时是小波在美国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小波走了。我立刻就问银河,她就解释给我听:小波是半夜里写文章,突然大叫一声,就去了。他的死因结论是心肌梗塞,但实际上他先天心肌很硬,后来愈来愈硬,舒张困难导致呼吸不够,就倒下来了。 记者:说说对知识分子的看法。 许倬云:从法国式的左拉、德国式的荣格尔,到近代美国式的"学得文武才,卖与商贾家",今天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了,这是非常伤心的情形。中国传统读书人参与儒家,都有一个志向,要建设一个完美的人间社会。大浪淘沙,会有人背离,但传统永远在,永远有一批人坚守。 记者:您跟海外新儒家有来往吗? 许倬云:认识他们,但来往不多。新儒家是当年熊十力传出去,今天再传回来的。熊十力取材的灵感当时来自于儒家和佛教。海外新儒家我认为成就最高的是牟宗三,他把康德摆进去了,但太哲学了,难以理解。 记者:对现代社会的人情冷暖有什么感受? 许倬云:农业社会是安土重迁,现代社会是家族离散,不能依靠过去的亲缘组织来解决问题了。今后依靠社区联系的组织架构也会逐渐式微,因为人们迁移的速度在加快。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可以用来解释过去,不能解释现在。西方人与人之间的逃逸、分散非常迅速,中国还会保持一部分人与人之间基于感情的差序格局。比如两个中国人,一个住在纽约,一个住在北京,两人在伦敦碰到了,一看都是中国人,还是会亲一点。如果是两个美国人,未必会有这种感觉。在一个寂寞的人群(Lonelycrowd)里,如果有一丝两丝还可以牵连,就不会太寂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