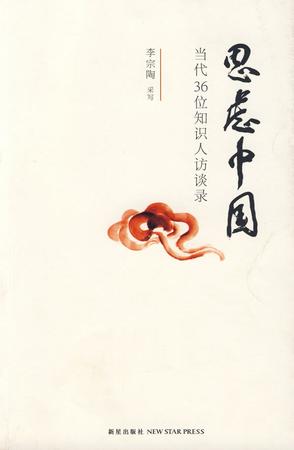记者:您怎么评价陈寅恪、钱穆、吕思勉这些前辈,以及同辈人余英时先生的问学? 许倬云:陈寅恪先生是个了不起的史学家。他用的史料都是最常见的史料,习惯用大量史料归纳出一个现象,那些归纳其实在他脑中早有观察和思考,根源不在历史。他渊博,早年留学德国,后来又到英国游学,得到许多理论背景,再加上家学渊源。他家族经历的,是同光年间的清流浊流之争、满汉之争、中西文化之争,这些人生经验体现在他对中古历史的课题选择上。但他并没有因为个人经验,在选择的课题中有所偏袒。举例来说,他经历同光之争,但在写唐代的牛李党争时,并没有影射同光党争;他面临中西文化交汇和冲突,但他在写唐代佛教文化进入时也没有一点偏袒。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宾四[钱穆]先生也是了不起的史学家。他是真正自学的,从来没上过学,他连好老师都没一个,纯粹是自己摸索出来的,真正聪明绝顶。他的史学研究的特点是另辟蹊径。当时正是今古之争(为改革寻找依据),他没有受正史教育里那些派别的约束,另外找到一条路,打破了今古之争里的一些课题。他后来写《中国通史》,了不起的著作,贯串了民族史观和爱国史观。日本的飞机在头顶上轰炸,他抱着讲义还在树底下讲,他不能不讲民族主义。这个人真是聪明,眼光真好,他一本《国史大纲》里埋着七八十个博士论文题目,大家看不见就是了。但也由于民族史观、爱国史观的限制和西方知识的局限,他对中国历史的评估是有偏差的。钱穆先生是我景仰的前辈,但出于对历史的忠实,我必须指出这一点。 吕老先生所处的时代也是难得。他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当时史学主流是编年史,他跟北大清华那批主流史学家是不大来往的。他的学问是国学基础上出来的,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甚为深厚。因为在上海居住,他感觉到时代在改变,他是当时通达史家里第一位考虑到生活起居、风俗习惯的人,这是了不起的贡献。典籍中能够组织的他都组织起来了,但由于资料来源局限于中国的典籍,相对而言观察的角度有限。他那本书[《中国通史》],用作线索甚好,但我想今天大部分人不会用到他那本书了。 英时跟我是好朋友。英时史学的路子,是钱穆先生给他一些影响,哈佛给他一些影响,此外是他自学。英时是读私塾出来的,国学基础甚好。他没有上过初中,直接就上高中了。他是从研究安徽的思想家戴震开始,治近代思想史,慢慢转入社会背景研究。在最近的一部著作《朱熹的历史世界》里,朱熹的思想退后了,朱熹身处的时代和他代表的那个儒生志业反而被推向前台。他也在改变。他对经济部分不是特别注意,他对文化也不是从比较文化角度看的,而是从中国文化的大环境、大脉络来看的,从这条线上看得很清楚。我们两个做学术的方法,我是从社会、经济开始,走向文化,偶尔走向思想;他是从思想开始,走向社会。我们在中间慢慢碰头,我们是和而不同,角度不一样,但有许多地方是一致的。我们合作过一本书《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他一篇,我一篇,还组织了一大群人一起写的。 记者:对翦伯赞和郭沫若,您有什么看法? 许倬云:翦先生是第一批采用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其实没有列宁)和他所理解的唯物史观进行研究的人之一,写了一部《中国史纲》。采用的分析法是当时苏联的断代分析法,这种分析法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是不适用的。在左派史学里他是第一个成格局的人,他做得很辛苦。我从他文章里看得出来,他自己也觉得这不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他后来跟国家政治不能合调,吃了很大的亏。作为第一个用马、恩思想研究历史的左派史学家,结果被打下去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他有专业的良心和忠诚,他对唯物史观也有一定的信仰,但毛病就出在唯物史观的局限性。 郭先生又是一个绝顶聪明之人。那个时代真是了不起,出了三四代这样的人。所以你要说天地对中国不厚,也不是。原因在于转型之后,无人钻研的空间很大,有空间就能自由飞翔,潜力就释放出来了。后来是愈来愈紧愈来愈密,一方面是政治影响,一方面是经济压力,为稻粱谋的人太多了。老实说,战乱都压不住人,宾四先生那部大作、寅恪先生好些重要文章都是战乱中写出来的。还有一个是民众趋同、走一条路的压力,这三个加在一起,就把可以回旋的余地全部压没了。Anyway,鼎堂[郭沫若]先生也是了不起的聪明人,没有学术训练,自学,将甲骨文研究到那个地步,了不起。甲骨文当时是处女地,谁下去,花功夫耕耘,都会有收获。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还有我老师董彦堂[作宾]都是大家。今天我们说,他[指郭]认的字有错的,但大部分是对的。拓荒之功啊,了不起!他将唯物史观套用到中国历史里,比翦先生更深。他的政治取向是非常清楚的,而且老早就决定了的,所以他跟"右派"一直走得很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里本来有他,但他不肯兼。但1950年以后,我们就没有看到他有独立的意见了,你可以说他跟着革命走,也可以说他跟着权力走,我就不能作断语了。他对学术的维护之功嘛……他可以做得更好,但他没有做。 记者:您在台大历史系的师承很不一般。 许倬云:遇到这些老先生,我是很幸运的。李宗侗[玄伯]先生,世家子弟,法国留学。他是晚清名臣高阳相国李鸿藻的孙子,一出娘胎就是举人。呵呵。他在娘胎里的时候,李鸿藻是宰相,是同治皇帝的老师。慈禧很尊敬他,说如果生个男孩,出生便封为举人。他受的教育是宰相门第的教育,可以接触到多少大学问的人啊,所以他的国学底子是非常深厚的。后来到法国留学,师从社会近化论派古兰氏(Granch),学习古代希腊史,这个对他影响很大。他教我古代社会史,但我后来慢慢离开了他的方向,因为这个学派过于狭窄地停留在单线演化论上,认为在一个地方演化的事情在另一个地方早晚都会出现。我后来不敢苟同老师的观点,但我对他是感恩的,因为他带领我进入古代社会,带我进入人类学。我正在想办法出他的全集,但出版社都想赚钱,他的书大概不会赚到钱,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找到愿意出他书的。考古学是跟李济学的,我现在的兴趣还在商周和新石器时代。当时我在历史系,张光直在考古系,张光直是李先生的嫡传弟子,我是隔了房的徒弟,算是同门师兄弟。我跟光直脾气性格很不一样,他性格拘谨严肃,一头钻进考古学,一钻到底,学问专精,我是跑野马,什么都感兴趣。光直吃亏在一直没有机会到中国来做真正的发掘--他来过,但没有被不允许,所以他考古学是纸上考古学,主要是看别人的报告,这是他终生的遗憾。他对中国考古学最大的贡献是把中国考古学的成就介绍给世界,没有他介绍,外人不理解中国考古学的线索和脉络。 记者:《汉代农业》英文原著有一点令人印象深刻,除了正文154页,后面竟然有大约160页赖以立论的史料和注释,所以我对您读原典的功夫非常感兴趣。 许倬云:史学家必须掌握各种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还必须读懂中国古籍,获得正确的历史感。我读史料和原典就是四个字:来来去去。 我很小的时候就读过大部分的中国原典,我读的第一部书是《史记》,后来慢慢地什么都读。十三经,说老实话,我没有全部读通,《礼记》里有很多我还没读。史书里面《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我是读完了。天文部分我读不懂,音乐部分我读不懂,一般的政治典方制度我是读懂了,所以我还没全读通。来来去去做什么事呢?我不是一次读完就拉倒了,碰到问题、材料,就拿来原典再看再钻,看过去没有看到的夹缝。我也拿别的学科来帮忙,同时我也读别国的历史,看别的文明。这一点我自问是比别的朋友注意得多一点。对中国古代史、古代三大文明--埃及、中国、印度(这个我差一点)和欧洲中古史的熟悉程度都还可以,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丰富的资源和有用的工具。经济学、考古学、人类学,这些学科让我多了许多眼睛,可以看到人家看不到的地方。好处是兴趣广泛,坏处是不能专精。 记者:对剑桥那套《中国通史》怎么看? 许倬云:那套通史不通的,因为出自众人之手,而每个人的见解想法都不一样。另一个极大的先天缺陷是这套书的主编给我们一个框框,你不能写新的意见,只要综述前人迄今已被公认的观点即可。所以让我写剑桥史那章,我是心不甘情不愿,但他们说那段非我写不可。其实我的想法已经有很大变化,但不能加进去。我太老实,别人偷偷加进几句话也是有的,我后来想,我也该"偷关漏税"才对。 记者:您怎么评价日本汉学的成就? 许倬云:日本汉学的成就极高。首先他们把东亚、中国分立为课题,东亚是相对西方的概念。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觉得自己堪比西方了,但地理上又明明在东方,"我要领导东方,打西方",这当然是帝国主义的借口。中国是日本文明的母邦,但它强大以后,不甘心居于中国之下。日本人的勤快是了不起的,一个研究室,三四代人研究同一本书,做同一个课题,延续性极强,累积的成果很高。这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两个学生在一起合作难极难极,这五十年来,师徒相承也不是越传越多,而是越传越少。我们可以用日本的成果,但不应当被它框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