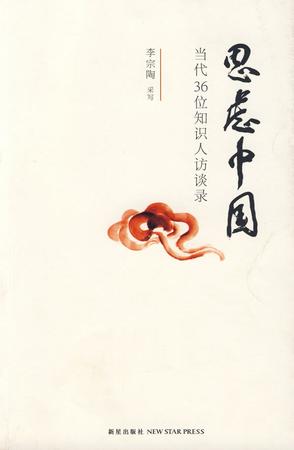记者:在文化"三元色"理论中,您特别指出亲缘组织的作用,您也说过亲缘组织今天依然在发挥作用。从这个角度,您怎么看陈水扁家最近的丑闻? 许倬云:我觉得应当哀悯。陈水扁这个家族是没有什么文化的。他家穷,穷没什么可非议的,但他家穷得没文化。他是个聪明孩子,靠台湾的考试制度考上台大,等于读书不花钱,做到律师,能言善辩,又参加了反对党,一步步有了今天的位置。他那个驸马爷的父母也没什么文化,母亲是小学教员,好一点,但在学校里名声也不太好,贪财、附势。他们的同事说起这两人,都摇头。赵家、陈家家教都不行,这种家庭教出来的孩子,不稀奇。他们现在借着国家力量搜罗大量的财富,这更像是利益集团,用亲缘组织形成利益小集团,谋个人私利。 记者:在跟许医农先生的通信中,您曾经提到过对变了味的"民主"的感伤,许多人寄予厚望的东西为什么会变味呢? 许倬云:民主制度有它的历史渊源。古代是部落民主,尤其是战斗中的部落民主,大家要战斗,一起决定一些事情,这类军事民主在草原部落、树林部落也很多。希腊城邦民主制同样有渊源,它是一些部落迁移到希腊带进去的。条顿民族、日耳曼民族的一些部落民主制度转化为北欧、中欧一些国家的民主制度,它们的渊源并不是从希腊来的。参与决定所属团体的事务,这是常有之事,从法国大革命、英国改革一直到美国建立共和国,这一串演化提升了民主制度的境界,有了理论基础,其根本就是人生来具有权利。 记者:"人生而平等,具有权利",后来写进美国宪法。 许倬云:对了,写进宪法有个依据,就是信赖上帝。今天美国钱币上印的"InGodwetrust",我们信赖上帝或经过神我们信赖彼此。所以人的神圣性是靠上帝的理念来肯定的,人的共同性平等性自由性,也是靠上帝无私地创造了你我他来决定的,这是基本的假定。我们来看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自由是对封建制度提出的;平等是针对法国贵族提出的;博爱,是指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兄弟,不能因为你的血比我更蓝而不爱我。 "自由、平等、博爱"是这么来的,有它产生的特殊的土壤。美国政治制度设计了三权鼎立的人民民主,要依靠法律来防止国家侵权。法国、美国这两个原则合二为一以后产生的民主制度,代表了人类在政治制度创造上极高的原创性,是了不起的事情。 美国的民主制度还有一个泉源,就是印第安的部落民主。部族权力和个人权利都要在部族联盟里出现,参众两院就是这么来的。美国的三权鼎立制,是要靠公有的法律在人和国家发生冲突时保障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国家的权力,三权里,行政权代表日常事务,立法权代表人民意志,司法权是根据共同决定的做事情的原则(宪法和法律)来保障人民的权利,因为人民在国家面前是弱者。 但这中间有一个大缺陷。美国立国十来年时,法国记者到美国去参观,有个叫托克维尔的记者就指出,美国这个制度一定会犯一个毛病,就是庸俗化、平民化之后的品质低下,到最后一定是哗众取宠的人得到权力。这个话,今天应验了。美国参院今天选出来的大多是哗众取宠的人。但是当时托克维尔没有看到的一点是国家的权力大到今天这个地步,这是他无法想象的。权力膨胀到影响到人生每一步的时候,窃取权力的人就会限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记者:丘吉尔说过,民主制度并不是一个好制度,只是至今没有更好的替代品。 许倬云:对了,丘吉尔这句话是说民主制度是个糟糕的制度,但它闯不了大祸。我们今天没有理解的是,国家掌握权力是一面倒的,国家权力太大了。人类社会正走到一个巨大转变的关口,在个人似乎已有自由的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面对超强力的国家机关,面对一些个人以公权的名义操弄权柄以自肥。中国大陆如此,台湾与美国也如此! 以前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这里有句话,革命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记者:"在人和国家发生冲突时保障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国家的权力",想听听您对土地国有制的看法。 许倬云:土地国有,应该有若干限制。荒地应该国有,本来有主的地,不该国有。但我认为土地属于私人应该设一定的年限,此生为限,不传子孙。我比较赞成老百姓享有土地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 台湾以前搞土地改革,口号是"耕者有其田",但随着城市化进程,他把土地卖了,手里土地多的人,都成了土财主,这就跟政府当初的设想完全相悖,而且其他的公共建设也无法推动。台湾现在要修一条路,就因为一幢房子不肯搬,可以折腾十几年。当然,政府如果为了城市建设,强权要求老百姓搬迁,说拆就拆,在安置方面总让老百姓吃亏,这也是不合理的。走到这两端,都是有问题的。我们听说一些城市是这样做的,拆一批,建一批,然后老百姓再回到原来的地方。这应该是国家、开发商、拆迁户达成协议才行。所以,台湾、大陆都走了不对的路。造成暴发户、财富分配两极,环境极度混乱。这方面,可以看看新加坡新城镇的做法。 记者:今天大陆讨论许多问题,最后板子都落在"制度"上。 许倬云:任何制度都像你我的衣服,或他[指摄影记者]的照相机一样会用旧,会与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不协调、不匹配。最重要的是理念,文化理念是个大问题。 现在是知识经济的社会。不仅中国背靠农业社会建立起来的一套秩序要改变,就是西方社会依托工业革命、资本和市场经济的那套秩序也面临冲击。知识是经济、知识是权力、知识也可以形成势力。生命可以创造,可以改变,生命的神圣在哪里,人与其他生命的差别在哪里?这些终极意义都要思考。 要重建一套伦理,建构起一套应对知识经济时代困局的理念,这不是单个儒家可以承担的。这个检讨是学界应该做的事,但没有做。 记者:西方人治史与东方人治史有什么不同? 许倬云:清代以降,中西趋同,现在已经差不多了。传统中国,历史是给上层人看的,治国平天下,以史为鉴,给出的是公识(publicknowledge)。史书相当于治国律己的教科书,都是交代一个事情或一个人物,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处处有教训。过去的中国历史跟人格教育、公共哲学是不可分割的。 西方史学从荷马史诗开始,就是讲个人故事、英雄故事,讲他们的喜怒哀乐、得失成败、优点缺点,所谓StoryTeller。你看History跟Story多接近。等到近代史学发展起来,西方史学欲摆脱教皇统治的阴影,寻根溯源,于是变成一个个国家、一个个民族。此时的历史,转变为国家、民族的历史。所以西方史学从17世纪开始,主要就是专题史,不大有通史。这个传统到20世纪初、大约是1903年伴随西方的大学教育传入中国。从此都是做专题史,写单篇论文,写通史的人很少。 记者:您怎么看待西学更重视的理论框架? 许倬云:西方人在对前人的东西做阐释的时候,做得好,可以建构一套自己的理论框架,也可以直接拿别人的理论来用。台湾是80%模仿美国,20%模仿欧洲,都在依样画葫芦,拿来主义。尤其尴尬的是,对从欧洲发起、美国紧跟其后的对现代性的批判(统称为后现代),台湾没有感受,误认为这是另外一种时尚。但其实,后现代不是时尚,是严肃的批判和检讨。大陆现在跟着后现代的风走,跟台湾犯的是一样的毛病。大陆原有自己一套既定的理论框架,20世纪前面几十年,都在框框里面转,转得很辛苦,结果是削足适履,理论界、史学界都很辛苦。近十五年逐渐在改变。十五年前争论断代争得很厉害,究竟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应该断在哪里,这个讨论令原本硬性的框架松弛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