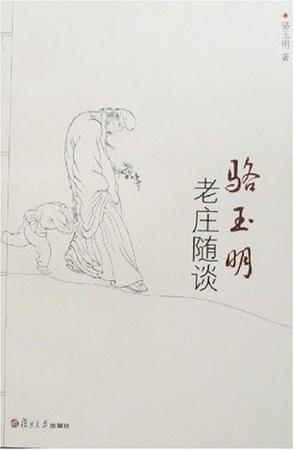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随谈 骆玉明 《老庄随谈》一书最初是由香港中华书局印行的,现在已经不大容易找见。去年杨福家先生曾托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他读了一遍觉得挺有趣,但在国外行途中把书弄丢了,问我这里能不能再找出一本来。我仔细翻了书柜,只有一本涂改得乱糟糟的,结果只能对杨先生说抱歉。复旦大学出版社打算让我修改一下重印,我想杨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也还有兴趣读它,或许其他读者也有愿意翻看的,就答应下来。照例应该专门为新版写一篇引言,但近期直是忙乱不堪,老是拖延着。恰巧前些日子在外面做了一个关于道家思想的讲座,开头一部分是讲道家(主要指老、庄)与儒家(主要指孔、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对立和互补的关系,一位朋友将录音整理成文字,我把这份讲稿清理了一下,觉得作为本书的引言也还合适。下面就是讲稿的内容。 关于道家思想,我想先说一个概述性质的话题,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一种既存在对立又具有互补作用的关系,想能够在一种大的局面上将两者放在一起观察。当然,这难免有粗略的毛病,但相信还是有些用处的。 首先我想绕远一点,就“传统文化”这个概念说几句。现在不少人喜欢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时候听起来很奇怪,好像非要退回到老祖宗那里去才好,有的人你弄不清楚他是要做教主还是要做骗子。我以为谈传统文化,有几个要点是应该注意的:第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很丰富的结构,它不是一种单一的东西。传统文化不能说它只是指儒家文化,它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的;即使讲儒家思想,它也包含着很多成分,儒家思想也不仅仅是那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属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东西。孔夫子自己也就没有做成功过什么官。我觉得这个意识是很重要的。第二,传统文化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它是不断变化的。中国历史几千年,不可能有一种思想从头到尾一成不变,一直就占据着中国人的头脑,一直都很管用。所谓“传统”,固然有沿续的表现,但它同时也是跟随着社会结构、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活动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总是有新的思想文化出现,加入到传统中去。第三呢,就是当我们讲到传统文化的时候,要注意到那里面哪些内容是真正是有活力的。中国文化中有些东西它是非常活跃的,大致说那是一种富于有创造力的东西,一种激发人不断向前走的因素,也有一些东西是比较陈旧和死板的,是对人的思想起到禁锢作用的因素。富于活力和创造性的因素,让人活得开心而不是憋屈,传统中的这种力量最终和中国人走向现代的趋势是一致的,因而它是最值得关注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最大、地位最高的就是老庄思想和孔孟的思想,比较晚一点,又有佛教的思想传进来,那么就是儒、道、释三家,三教九流。要说老庄和孔孟也是各成一个系统,每一家自身的内容也很丰富,我们能不能用一些简明的方法对它们加以阐释呢?魏晋时代有一组对立的概念分别指老庄思想和孔孟思想,就是“有”和“无”的这对概念。儒家的思想用“有”来概括,而道家思想用“无”来概括。玄学家有时会讲得复杂一些,比如王弼认为“圣人” 即孔子虽然只是讲“有”,却以“无”为本;老庄虽是讲“无”,却也并不是不知道“有”的价值。这样说是要把老庄和孔孟混融起来,各取其所长。但这也不妨碍我们将“有”和“无”视为孔孟与老庄思想各自的主要特征。我们以这样一组概念来对比,便于将这两种思想加以简要的区分和对照。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 孔孟思想称之为“有”,是说它是一种为社会确立秩序和价值的学说,它的作用表现在通过明确的秩序和价值使社会进入一种稳定的状态,人的行为有明确的规范可以遵守。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和方圆明明白白,所以它是“有”。老庄思想之所以称为“无”,因为它不相信人所订立的秩序和价值能够稳定地存续,能够使人生活得更好。因为这是人为的从外面强加给人的东西,它不自然,不符合天地的本性,也不符合人的本性。而世界的本质是一个虚无,它是不确定的,富于变化和具有无限可能性的。 进一步,我们以孔子和老子最有名的几句格言来说“有”和“无”,就可以说得更加清楚。还是先说“有”。大家知道孔子有一个很重要思想就是“正名”说,所以儒教又被称为“名教”或者“礼教”。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路,这个子路是个勇士,只比孔子小六岁,为人粗莽,对孔子不是很买账,孔子有时候也对他很恼火。有一次子路问孔子,说是:“你不要老是说人家不用你,如果有人请你执政,你说你首要的方针是什么?”于是孔子就说:“必也,正名乎。”(如果是那样,那就是正名了)子路就说:“你真迂腐啊,管国家怎么就弄到正名去了呢?”孔子就很不高兴,教训他不要不懂装懂,然后说了一番“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大道理。正名思想在孔子那里还有一种更加具体的表达,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的语法结构在古汉语里叫做使动用法:“君君”,第一个君是动词,第二个君是名词,君君就是使君成为君,其余类推。这句话如果大家觉得离我们现在太远的话,可以再举一个现在日常说的例子,比如说做老师的有时候会教训学生:“做学生得要像一个学生。”做老板的有时候也会教训员工:“你做员工就要像一个员工。”当我们在说这种话时,其实和孔子的想法是一样的,可以替换来作分析。“做一个学生要像一个学生”,前面这个“学生”指的是某个具体的人,其身份为学生,后面一个“学生”则是关于学生的理念;“做一个学生要像一个学生”,就是说要使事实符合理念。“君君臣臣”之类,也是如此。 要使事实符合于理念,这个就叫“正名”。往这个方向推开去,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我们给世间万物命名,这不仅仅是用一个声音或文字做符号来代替一个事物,比如用“杯子”这个声音来指代用来喝水的那种实物,不是那么简单;命名的行为意义乃是我们通过给万物命名确立了世界的秩序和价值。比如说,我们使用国家、社会、集体、个人、自由、民主等一系列的名称,这些名称无不体现着理念,体现着秩序即事物的合理关系,体现着价值并由此判断行为的当与不当。说到底,名的世界就是一个理念化的世界,它要求实存事物依照它的规则运行。 那么,谁都可以通过命名行为给出世界的秩序和价值吗?当然不是。就说“父父子子”,当老子的要求“做儿子要像一个儿子”,儿子反驳:“凭什么你说像才算像?”老子当然要教训他:“是我养活你,是我挣钱供你上学,所以我说了才算!”一个门房要给整个公司定规矩,可以吗?我倒是想为国家制定大政方针,并且把它写进宪法,但结果恐怕要被人送进什么医院去,所以宣布放弃。这话回过头去也是一个很深的道理:“有权力为世界命名并阐释这个‘名 ’的人给出了世界的秩序和价值”。 我在举例的时候好像把事情扯得太远了,我当然还要说明历史上的“名教”有其特定的内容,不是一切命名行为都可以叫作“名教”。但在说明“正名”思想其实就是企图依照理念来塑造世界的面貌这一点上,拉开来说也是不违背逻辑的。 但是名教思想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就是说,世界并不是按照理念来变化的,世界不会永远安顿在人给出的秩序与价值体系中不动。尽管自认为发现了真理的人不会承认他的“真理”只是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成立和有效,特别是那种跟现实政治、跟统治力量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学说,总是喜欢宣称自己已经给出了最合理的乃至是永恒的秩序和价值,但世界仍然要变化。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现象呢?名的世界会崩溃,一个理念的世界会崩溃。这种变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汉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时代,而两汉的儒家学说是为这种政治体制服务的。而到了魏晋以后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起来了,那就是历史上称为“士族”的一个贵族阶层。士族的特点就是它的权力不是来自于皇权,而是来自于其自身的力量。士族拥有很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最终造成了士族权力与皇权并存和相互制衡的状态,极端情况下皇帝甚至只是一种象征,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干。那么原来的一套意识形态就显得很不适宜了,它的种种荒诞可笑之处统统暴露无遗。我想说一句听起来很绕的话:荒诞之为荒诞,不是因为它本来就是荒诞的,荒诞是因为它与变化了的现实不相称才显得荒诞。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老庄的“无”,也是用《老子》里面一句话作代表,那是开头的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老庄思想和孔孟思想根本上的不同,在于老庄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一个“无”。这个“无”不是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的意思,而是说作为宇宙本源、同时也代表了根本真理的“道”,是无形无迹的,是不具有任何规定性的,是变化无穷和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老子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切事物都有效法的对象,最后指向“道”,而“道”则无所效法,它以自身为法则。“道可道”,第一个“道”是名词,第二个“道”是动词,言说的意思。世界的本体、根源和根本真理,这个道是可以言说的,但一旦言说,它就“非常道”,不是原来的那个永恒的大道了——它被语言所限制。这话说得有点玄妙,但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总要去言说那个世界的“本质的东西”,人类总是要寻找世界的根本真理,并且依据它来建立自己的价值系统。你不说也不行啊,不说何以知“道”?但是它不能被限定在任何一种状态当中,所以他说“非常道”。这句话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人不可能一次性地穷尽真理,人永远没有能力把真理解说完毕”,所以只能是永远地试图接近它。然后说“名可名”,名称可以用来指称实存的事物,但是“非常名”,名称和事物并不永远结合在一起,就是说被指称的那个事物和你使用的名称以及它所内涵的理念不是可以互替的。我们称作“社会主义”的事物,就不再是开始命名时的那个样子了。邓小平曾提出一个“不争论”的意见,实在是大有意味。你死守那个“名”又有何用?社会是要变化要发展的。那么老子这句话给人的一个最大的启发在哪里呢?就是说你不能用理念的、名称的一套东西来代替世界本身。 庄子和老子是很不一样的,庄子更是站在一个批判的立场上,站在更彻底地否定人所建立的统治秩序和与之联系的价值观的立场上。老子讲“无为而治”,但是“无为而治”也是就一种合理的政治社会秩序而言的。而在庄子那里,他就对治不治没有很大兴趣,他关心的是个人如何能够在昏乱的社会中保全自己,并达到一种超越的精神自由。所以他对社会统治力量虚伪的一面看得更透彻,抨击也更加厉害。比如他提出来世间争论不休的是是非非,其实都是由于人们站在各自不同的利益立场上各执己见造成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站在超越的立场上,根本就没那个是非。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这种话确实很有智慧,读《庄子》常常使人们意识到生命有可能是何等荒谬。 我们这样大概一看,就知道老庄的很多东西是站在孔孟的反面的,老庄思想对孔孟思想有一种瓦解的作用。但是这种瓦解是必要的。如果说中国文化传统里只有孔孟思想没有老庄思想,那么偏执地依着固定的理念去强制变化的世界的情况会更严重。要不然,就是古人说的“死于名下”,现实世界已经变化了,“名”的世界已经崩溃了,你还抱着它不放,以为陈旧的理念比鲜活的人生更重要,那真是滑稽而可悲。 老庄经常说的“自然”,也可以作这样一种理解:在人为秩序和价值观约束下的生活是不自然的,所以任何时候都可以返回自然,返回到命名之前的世界。既然最早的起点是一个“0”,是自然,那么人也可以从自然之中重新出发。 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前面所说的互补关系呢? 老庄思想通常在社会动荡、原有价值观被怀疑而趋于崩溃的时候影响力特别大。东汉末年特别是魏晋时代老庄盛行,它给士人的精神以一种大解脱。我们读魏晋时代的东西,觉得和中国其他时代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用我的老师朱东润先生的话说,那个年头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老子不像老子,儿子不像儿子,人人都想凸显一个不同于他人的自我,乱七八糟,鲜灵活泼。《世说新语》里记载,西晋高等士族王浑和他的同样出身名门的夫人钟氏在庭院里聊天,他们的儿子走过来了,王浑得意地夸儿子出色,可他老婆却说:“要是我和你弟弟生个儿子,会比他还要强呢!”钟氏大约内心里对小叔子有好感,但那样说当然只是开玩笑,并不表明她要做什么,可是清朝人李慈铭读到这个故事惊讶得不得了,觉得一个贵妇人怎么可能说出这样下流无耻的话来。 但老庄思想的毛病在它没有很强的建构作用,庄子尤其如此。它在瓦解之后,不能给出一套有效的秩序和价值。世界的秩序和价值是永远必要的,从社会来说,没有秩序和价值它根本就无法存在,从个人来说,没有价值就意味着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而没有意义的人生是人无力承担的,它没有着落,四望荒凉。魏晋时代曾经出现过一种景象,我把它叫做“名的世界崩溃以后的自由狂欢”。既然世界的本质是虚无,人生可贵的是自然,为何不放任自己呢?也是《世说新语》的故事,说“竹林七贤”里面的阮咸那一帮人在一起喝酒,儒家传统里喝酒是非常讲究礼仪的,他们完全不顾,就把酒缸放在院子里,围着酒缸舀酒喝,有的连衣服裤子也不穿。一群猪闻着酒香过来了,把头伸进缸里喝酒(那是米酒),大家觉得这多么自然啊,也都学了猪的样子。这多么豪迈又多么放诞!但是在放诞过去以后呢?生命背后那彻骨的悲凉! 为什么说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都可以成为主导思想呢?因为它是“有”,正常的社会只可能在“有”的状态下存在。当然,它不能恢复到瓦解之前的老一套,儒家思想也是变化的,在瓦解之后,崩溃之后,它以一种新的面貌来来适应社会的变化,重建价值和秩序。魏晋玄学就已经是努力把“有”和 “无”融汇在一起,把“自然”和“名教”相结合,后来又有新的变化,就不再往下说了。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到晚期越来越缺少活力,这个我一下子说不明白,但是有一点,中国社会至少到宋元时还是很有活力的。就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