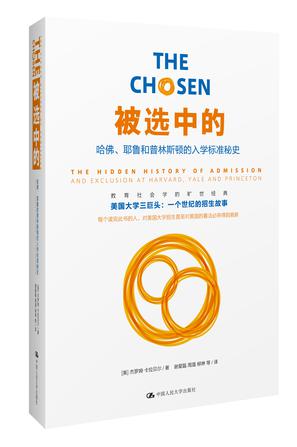1900年9月,是秋,在一个早晨,五百多位新生赶早来到哈佛大学注册。在他们中间,有一位清瘦的年轻人,他看上去有那么点贵族气息,脸上挂着一副夹鼻眼镜。尽管学业并不突出,也并无多少运动才华,不过,这位年轻人身上却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质——他的同学后来描述他说:“他有灰色的眼珠,看上去冷峻、自持、聪慧……又总带几分温暖、友好,脸上还总挂着几分通情达理的笑容。”这位年轻人从他的拉丁文老师那里获得的推荐非常有力。他的老师形容他说“他具有非常出色的能力和非常高贵的品质”,而且“他非常希望能够走进公共生活”。这位年轻人就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933年,他成为美国总统——哈佛历史上第4位成为美国总统的毕业生。 罗斯福被哈佛录取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他毕业于格罗顿,是美国住宿学校中的最上流精英,当然会被哈佛录取。1900年,他23位同学中的18位被哈佛录取。这些毕业于格罗顿的男孩——还有他们那些来自圣保罗(St.?Paul’s)、圣马克(St.?Mark’s)、弥尔顿(Milton)以及其他顶尖私立学校的同伴——主宰了当时的精英大学。 不过,也并非所有的大学新生都来自精英阶层。哈佛一直以自己录取的学生有着多元化的社会背景而自豪。在这点上,它比耶鲁,尤其是普林斯顿要做得更好。在对新生的一次演讲中,哈佛大学的校长埃利奥特驳斥了人们对哈佛的“错误看法”:这些人都认为“我们这所大学里的人都口含金汤匙出生”,实际上——埃利奥特辩解道——情形恰好相反,“大部分人都出身平平,而也正是这种多元化的情形才使得我们在座的各位能够拥有这段宝贵的人生经历”。 实际上,埃利奥特有意淡化了这一事实:哈佛大学的学生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来自优势社会阶层。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哈佛大学的学生组成的确有着相当程度的异质性。罗斯福班级上的新生有超过40%都来自公立学校,并且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移民的孩子。1900年,给哈佛大学输送新生最多的学校,既不是格罗顿也不是圣保罗(该校为哈佛输送了18位新生),而是波士顿文法学校(该校实际为哈佛输送了38名新生)——一所早已失去波士顿名流青睐的公立学校。 但是,公立学校的男孩们所置身其中的哈佛却并非罗斯福和他的朋友们所置身于其中的那个哈佛——这两个群体之间早已产生社会性的分裂。而分裂的物理符号就是两者在哈佛生活环境的差异:后者住在芒特奥本街(Mount Auburn Street)上奢华的“金海岸(Gold Coast)——贵族学生才能住的地方”,而前者则挤在哈佛庭院(Harvard Yard)寒酸的宿舍里——这些宿舍有的甚至没有暖气和自来水。[7]罗斯福出身高贵,理所当然住在芒特奥本。在入学之前,他就和他的未来室友莱思罗普•布朗(Lathrop Brown),先行参观了坎布里奇(哈佛大学所在地),并在金海岸选择了一处合适的住处。他们当初选的是威斯特里堂(Westmorly Court,现在已是亚当斯堂[Adams House]的一部分)。该宿舍顶高堂皇,有两间卧室,一间客厅,还有门廊和浴室。 罗斯福出身显赫,家族中有过好几个哈佛人——他的父亲詹姆斯于185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他的远房堂兄西奥多(当时正竞选美国副总统)也于1880年毕业于哈佛。这样的家庭背景让他很快就融入了金海岸的氛围。尽管他宣称要在哈佛“广结好友”,但事实上,他的圈子依然未能超脱出身的窠臼。他与来自格罗顿的好友一起在私人餐馆用餐,在桑博恩(Sanborn)台球馆与好友夜蒲。在这里,他可以遇到“大部分来自格罗顿、圣马克、圣保罗以及庞弗雷特(Pomfret)的伙伴”。他还是波士顿社交圈的常客,经常与好友们品茗、共餐、聚会。 尽管罗斯福优良的血统已经能让他在哈佛的圈子中立足,但是他尚需在哈佛丰富多彩又高度分层化的课外活动中力争一席之地——对大部分学生而言,这些需要大量精力的活动要远比学习重要。在世纪之交的哈佛,最重要的课外活动要数足球。罗斯福当然也义无反顾地想要一试此项运动。与他一道的还有其他142名同学——这个数目已然超过新生总数的四分之一。他尝试的是后卫。尽管身高六尺一,罗斯福的体重却只有146磅。在1900年的10月13日,罗斯福——这个昔日在格罗顿还算中等、又有激情的球手——被告知,他没被选上球队。 在被刷下数天后,罗斯福就决心另谋出路,试试《哈佛校报》(Crimson)——哈佛的学生报。10月19日,他致信父母,告诉他们自己正在尝试加盟一份报纸,并期望“勤奋地工作两年,成为编辑”[12]。不过,如同玩足球时那样,在《哈佛校报》,他也没能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当时入选的比例是86∶1。第一波新人在当年2月被选中。显然,罗斯福又败下阵来。 但是,罗斯福并未放弃。转机发生在当年4月,其时,他身为副总统的表亲西奥多正造访坎布里奇,并告诉他自己会在第二天早上洛厄尔教授的宪政课上发表演说。罗斯福向《哈佛校报》吹风。结果,第二天桑德斯剧场(Sanders Theatre)来了整整两千名听众。从此刻起,罗斯福这颗新星冉冉升起。1902年秋天,他荣任《哈佛校报》的助理总编。 罗斯福在《哈佛校报》的成功,可归功于其对《哈佛校报》的执着,而非其出色的记者天赋——他的写作并不出色。家族的名头可能是他最大的资产。1901年9月,在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遇刺之后,他的表亲泰迪(Teddy)就任美国总统。1903年2月,在罗斯福竞选总编(若获得这一位置,便可自动升任主席)的海报里,他写道:“总编就是他——表亲富兰克林——罗斯福家族的精英。”他赢了竞选,并在1903年6月至12月间任《哈佛校报》的主席。 是的,《哈佛校报》看重勤奋与天赋(这两者将胜任者与不能胜任者分开),当然,让校园中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有所区别的,远不只是这些。当回忆在《哈佛校报》工作的日子时,罗斯福的同学(Walter?E.?Sachs,高盛的创始人之一,萨克斯家族的后人)感慨地说自己与罗斯福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罗斯福在金海岸与格罗顿的同伴们一同进餐,时不时参加波士顿的上流聚会;而自己却只能与朋友们住在哈佛庭院里,在纪念堂(Memorial Hall)的30号桌边吃便宜的难以下咽的食物,在这里,每周只需付4.25美元,便可吃上21顿饭。 罗斯福与在《哈佛校报》工作的同学处得不错。他不是一位具有改革意识的总编(他花了大量精力关注足球队的弊病以及哈佛庭院是否需要一条更宽阔的人行道这类事情),却是一位颇具天分的领导者。当忆及罗斯福,他的同学和他在《哈佛校报》的继任者都说:罗斯福“喜欢别人……也让别人发自内心地喜欢他”,“他亲切友好,不怒自威”。 在哈佛,《哈佛校报》的主席职位已然尊贵。但是,成功的顶点却不在此,而在坡斯廉(Porcellian)——这个年代最为久远,只吸纳少数人的“最高级俱乐部”。从某些方面看来,罗斯福最有资格成为坡斯廉的会员——他的父亲曾是这里的荣誉会员,表亲西奥多也曾为这里的一份子。他自己还上对了寄宿学校——在坡斯廉俱乐部的16位初级与高级会员中,有5位都来自格罗顿。 坡斯廉是哈佛层次分明的社会结构的顶点。从新生抵达坎布里奇的第一刻起,它就开始物色合适的会员人选。在二年级的时候,备受学生仰视的1770学院(Institute of 1770)会负责将学生做第一次筛选,从学生中挑出100名最适合“社团”的人选。挑选分组进行,每组10人,第一组10个人由上一年级的人选出,“第一组10个人”再负责选出第二组10个人,直至选出第十组亦即最后一组人选。被1770学院选中是件让人感到非常荣耀的事,《波士顿报》和《哈佛校报》会按照选拔顺序刊出被选中者的名字——这一做法一直延续至1904年。 但是,罗斯福一路红灯,第一组10个人里没有他,后面接着四组里也没有他的名字。当11月末,室友莱思罗普•布朗被选中时,罗斯福已经相当焦虑了。不过,最终,在1902年1月9日,他得到消息,自己名列“第六组十人名单的首位”。他的当选——尽管有些迟来——给了他一张进入德耳塔•卡帕•厄普西隆兄弟会(Delta Kappa Epsilon[也叫DKE 或者“the Dickey”])的门票。DKE是个秘密的兄弟会组织,入会之时,会员们都需完成让人倍感折磨的入会仪式。对于这些仪式,我们最好将之描述为“令人好奇的原始的通过仪式”。不过,对此,罗斯福毫无怨言,在他给母亲的邮件中,他写道:“我差点就被宰了,但是觉得非常开心。” 罗斯福的此番态度,非常容易理解。因为数以百计被1770学院选中的学生中,只有前7组或者前8组人能够获邀加入德耳塔•卡帕•厄普西隆兄弟会。而此一组织的成员资格是被选入最高俱乐部的先决条件。尽管如此,情形还是有些微妙——对于这样一个背景无可挑剔的年轻人而言,排在50名开外,实属意外。罗斯福的排名可能反映出他个人性格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常导致他家庭成员的不快。在其宗族的牡蛎湾(Oyster Bay)这一方(西奥多•罗斯福家族的这一侧),人们时常给年幼的罗斯福起一些不太招人喜欢的绰号,例如“南希小姐”(因为他在网球场笨手笨脚),还有“鸡毛掸子”(双关语,说他看起来像当时一款出名的方巾上印的一位“漂亮的男孩”)。罗斯福的谦谦之风——当时《哈佛校报》的一则海报对此有所印证,它说“芳香罗斯福,谷中百合花”——在其时看来,也许并不适合,因为当时看重的是“刚毅”。 尽管罗斯福待人友善、工作勤奋又用心良苦,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有些人,包括他们来自格罗顿的同学,说他两面三刀,“皮笑肉不笑”。另一些人,包括与他有所交往的女子,则认为他肤浅,会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而自鸣得意,说他自负。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罗斯福会在1904届学生中的社会地位稍显弱势,只能肯定地说,在1770学院排名51的位置并不是个好兆头,因为坡斯廉每年只接受8位新成员。 但是,罗斯福依然心存期望。不过,最终这一刻还是来临了——他被拒之门外。对于一位年轻的贵族来说,这样的结果不啻是一种巨大的打击。这些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人,视进入这样高级的圈子为理所应当之事;如若不能,便意味着颜面扫地。尽管最后,他还是被选进了另一个权威的高级俱乐部——飞行俱乐部(Fly)。不过,对他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慰藉。15年之后,已是海军助理部长的罗斯福告诉谢菲尔德•科尔斯(Sheffield Cowls,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的妹妹安娜的儿子),被坡斯廉拒绝的经历是“我生命中最令人绝望的时刻”——更糟糕的是,泰迪•罗斯福的两个儿子——小罗斯福和克米特(Kermit)都先后被选入坡斯廉。很多年之后,艾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就这件事还评论说:她丈夫因为坡斯廉的事,有了一种“自卑情结”——尽管这件事“曾帮助他认识到生活需要克服诸般难处”。